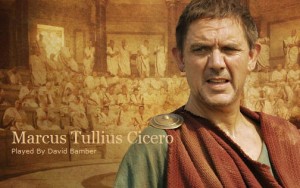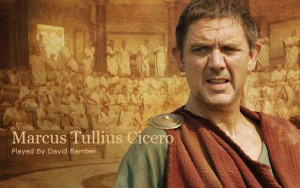
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言辞尖刻,因为他们感觉到被剥夺了那些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无论他们是情绪激昂,还是态度谨慎,都觉得自己所说的话听者寥寥。
——雷蒙·阿隆
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
——钱钟书
一
修辞是个文学概念,但可以广泛出现在与文学无关的各种文字里。阅尽万卷的钱钟书尝言:“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说到文学修辞的力量,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声叹息可为代表:
十二个成年男人和女人的死亡,给我们的感动还不如托尔斯泰作品中一只苍蝇受的苦难多。
说到知识分子的修辞伟力,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杰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有一段针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评论堪为脚注,这些启蒙思想家均是一流文学家:
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我们当然记得,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开场白,也有浓酽的文学味:“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修辞有两大目标:审美和伦理。审美即修辞的文学性,那是诗人、作家的常规胜场,无可非议,千百年来读者一直在快意享受着,兹存而不论。在我们讨论知识分子写作时,服务于人格塑造的伦理功能更重要,古语“修辞立其诚”即强调了它的价值。本来,汉语里的“文”兼有修饰、美化之意,成语“文过饰非”、古语“衣冠可诈,而形器不可诈;言语可文,而声音不可文”等论断,均点明了这层词义。而“修辞立其诚”之所以构成一项重要告诫,正在于“修辞立其伪”乃是文字常态,诗人元好问曾犀利地概括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章不易“见为人”,恰对应于无论文章新手老手都热衷于粉饰自我的现实,这种粉饰常会达到恁般程度,所言与所行,正好相反。
如果我们坚持将知识分子论述限定在“三个公共”框架内——即面对公共大众、谈论公共话题、指向公共正义——我们就不易在以“士”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找到知识分子写作的样本。因为,假如忽略过于悠远绵邈的上古时期,古人著述要么志在向君主进言,要么旨在与别家商榷,要么意在立一家之言,无论他们是否“立诚”,普通公众总在目标读者之外,公共正义多半也在云里雾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既定语境里,不可能觅得奠基于人民福祉的现代正义观;士人忙于为皇上陈计供策,其言词中的“民”,不过是一种用来警示“载舟覆舟”的对象,操心民瘼的本质是牵挂皇权。
此外,仅仅强调写作的诚实,与知识分子面向真理的目标还差得远,沃尔特·李普曼说得明确:“不幸的是,真诚并不代表智慧。”更全面的说法来自一位现代逻辑学家D.Q.麦克伦尼,他说过:“或许你绝对真诚,但同时也绝对错误。真诚不能将谬误变成真相。人要真诚,然而人更要正确。”就此而言,当我们意欲讨论知识分子写作,我们无法从“修辞立其诚”里得到更多启发。
在古希腊及师法古希腊的古罗马,修辞功能得到了更好的研究,修辞的伦理性也得到了更积极的评价。美国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里,曾将亚理士多德的定义,转述如下:“修辞是指针对不可能以逻辑、数学、控制实验或其他精确推理的方式予以解决的问题,说服人们认可问题一方或另一方的一整套策略。”波斯纳同时指出,“亚理士多德的修辞理论强调‘伦理诉求’,即意味着试图说服你的听众,除了你的论辩本身的优点以外,你本人就属于值得信赖之人。”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明确了两点:一,修辞不会增加论证效力。最严密的论证,通常也最不需要乞灵于修辞,比如数学论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需也无法通过引用莎士比亚来增加说服力。二,只要你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公众,你就必须借助修辞,公众对你的信赖是你的观点得以扩散的前提,而除非有效地调动了读者,否则,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信赖你。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实行一种城邦民主制度,其统治者并不自称受命于天,执政官及重要公职人员的当选、施策及述职,往往在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进行,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有权支持或罢免他。因此,说服公众相信自己的主张,就不再局限于中国式的私人道德,还是一个现实成败问题。他若满怀报国之志,就必须将说服公众作为头等大事;像屈原那样只对楚王一人哀哀陈情,必然无济于事。于是,说服公众的雄辩术就发展成一种重要技艺,并得到知识上的培育发展。一位善于调动公众情绪的人,就像今日欧美法庭上擅长说服陪审团的律师那样,他那视诚实如粪土的煽情技艺非但不会遭到指责,还将成为一种职业荣耀。亚理士多德时代确立的另一项修辞学规则是:“要以听众能够接受的主张展开辩论。”换言之,如果你只想姿态高蹈地立一家之言,那就请退守书斋,远离公共讨论的世界。
苏格拉底虽然很谨慎且执意追求真理,他面对由501位雅典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进行最后申诉时,仍“依照惯例以老练的演说家言不由衷的恳求作为开场白——为自己的拙于辞令表示抱歉”。那当然是修辞。固然,他还借助神谕强调自己是最无知的人,但这个说法不难自圆其说,比如,依据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著名比喻,接触了更多知识的人,相当于拥有一个更大的圆,更大的圆既意味着掌握更多的知识,也意味着面对更加广大的无知领域。因此,拥有最多知识的人,的确会产生最大的无知感。但苏格拉底声称自己不善言词,就较难回护,因为他遭到审判不仅缘于他被控渎神,还缘于他谈锋过健,影响力太大——总之,口才太好。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讨论总是没完没了,在这里我们或可大致确定,他并不认为在涉及自身命运的最后陈述里,必须恪守“修辞立其诚”的东方教条(他也没听说过这种教条),相反,他认为让公众以为自己木讷口拙,更符合当下目标,即使他并不怕死。如你所知,苏格拉底的计谋(如果非要说是计谋的话)没有成功,这位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并非死于暴君手下,而是被无知且狂热的民众判处死刑。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写到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他比较了伯里克利的各种功勋(“将雅典修得如此宏伟,……政治军事方面有才能”),最终倾向于优先肯定伯里克利的语言才能,“就像乐器似的,上面时常绷上一根阿那克萨戈拉斯的副弦,使自己的发言染上自然哲学色彩。……他把他的学识用到谈话技巧中,于是他比别人更高明。”他热烈赞颂道:“伯里克利向群众演说时,像‘雷鸣’,像‘闪电’,像是‘舌头上有一根可怕的霹雳棒’。”
罗马人被视为“老到的阴谋家”,与他们迷恋希腊人的说服艺术有关,这尤其体现在罗马雄辩术的集大成者西塞罗身上。西塞罗对演说家的要求是:
雄辩的演说家不仅要赢得赞同,而且要赢得敬佩、欢呼和掌声,要是可能的话,他要在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要是在他前面还有什么东西更伟大,或者有听众说除了听他演讲还有其他更大的快乐,那么他会感到羞耻。
简而言之,荣耀始于“掌声响起来”。西塞罗从柏拉图那里受到的教益是,“在嘲笑演说家的时候,他本人就是一名成熟的演说家。”他认为,“最好的演说家是这样的人,他的讲话教导、振奋、打动听众的心灵。演说家有教导的义务,快乐只是赠给听众的一件小小的礼物,感动他们则是必不可少的。”他还提出如下具体建议:“愤怒最好以高音调的抑扬顿挫的短语来表达,发表演讲时应当伸出右臂就像伸出武器一样。……在有力的段落其开头和结尾处都应当伴随着有力的跺脚。”
来自西塞罗的巨大影响,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居然催生出一门古怪的学科:劣物修饰学(adoxography),并要求中学生学习。“这是一种称赞无价值事物的技巧”,学生必须学会“赞美畸形、丑陋、贫困、失明、放荡、思想贫乏和愚蠢的评论”。学生还被告知,该学科“对律师们特别有用”。索尔仁尼琴提到过一位雅库博维奇,“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他曾在某次会议上“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1917年4月呀!他差点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面对这种巫师型煽动者,人民不够警觉,就可能经由掌声的滑梯滑向地狱。在一个良性社会里,当知识分子或政客磨炼自己赢得掌声的技艺时,成熟公民也应同步养成拒绝随意鼓掌的习惯。
二
波斯纳法官在扼要介绍了乔治·奥威尔的事例后,概括道:
奥威尔的事例表明,成为一名真正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一种魅力型职业(a charismatic calling)。它主要并不是一项智识聪慧、见闻广博以及清晰明澈地创作之事,而是能够通过修辞之力量或某人生活之范例(相关的要点在于——一种模范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伦理诉求特别有效的形式)而撰写出为社会公众或至少为受过教育的社会公众所信任的新颖独特、扣人心弦、边缘异类的思想。
该魅力亦译为“克里斯玛”,喻指一种支配性的超自然人格,当古人称文章为“千古事”时,八成也指向这种魅力。小说家也不失为魅力型职业,但小说家写作时,并不要求展示自身的道德品质,更好的小说家往往更擅长隐匿而不是展示自我人格,是以我们读完《三国演义》,并不清楚罗贯中是何许人也。诗人的情况稍有不同,我们如此喜爱陶渊明,肯定与我们欣赏其人品和生活方式有关。诗人拜伦通过《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堂璜》等长诗塑造了诗性主人公之后,他在生活中随之失去了过平常日子的权利,波斯纳写道:“他已经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选择余地,只有按照他的诗歌生活下去。这种生活一方面很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他乐于扮演登徒子、英雄和解放者的角色。”在意大利扮演情种,去希腊担任解放者,似乎也是向读者兑现自己的诗情诗境,具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必然性。
知识分子的修辞大抵也是在“魅力”的领域纵横腾挪,却未必具有拜伦的言行一致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众所周知晚年时致力于成为一名超级知识分子,“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着手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发出抗议书,发表声明,特别是在诸多文件、信件上签字,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为了维持他人对自己的热切仰望,他还会捏着鼻子做一些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比如“倒便壶”,或尝试给自己和家人做靴子,虽然坚持了没几天,但足以让他向公众发表如下感想:“这让我感到变成了一个劳动者,因为心灵在发育成长。”他还试着干些农活,让记者拍下他的照片满世界转发,照片上,“一把凿刀插在他的宽皮带上,一把锯子悬挂在腰间。”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里通过文本对照,公开了托尔斯泰一桩丑行。屠格涅夫自知不久于人世,希望与托尔斯泰冰释前嫌(本来也无甚芥蒂),就给托尔斯泰写了封信:
我亲爱的朋友,俄罗斯土地上伟大的作家,请听从我的请求吧。请让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并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写下去了。
尽管屠格涅夫又在病榻上缠绵了两个月,但他一直没有收到托尔斯泰的回应。但是,当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必须对屠格涅夫之死发表些公开看法时,他这样说:
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爱他,同情他,读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
保罗·约翰逊评价道:“这是演员的腔调,他扮演着公众对他期望的角色。”据他说,托翁的妻子索尼娅很早就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真正的友情所必需的互不干涉和亲密无间,托尔斯泰都不具有。相反,他之所以信奉博爱精神,是因为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闹,更富戏剧性和轰动效果。”真是这样吗?我不敢说得更多了。但是,素以哲思深湛、理性坚定著称的英伦大哲伯特兰·罗素,在《自传》里写过一句招供语:
我在描述一个不可容忍的事物的时候,就把它描述得令人厌恶,让别人同你一样愤慨。
保罗·约翰逊对此评论道:“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招供,它出自一个以对问题的冷静分析为职业、把自己的旗帜悬挂在理性的旗杆上的人士之口。”并非我恶意联想,当戈培尔们认为犹太人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种族时,大致也是这么干的:“把它描述得令人厌恶,让别人同你一样愤慨”。不过,其中有个重要区别不可不辨:戈培尔们的描述及栽赃,是在一种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里,借助高音喇叭发出的不容异议的歇斯底里大批判,因而本质上不是发表见解,而是肆虐权力;而不依托权贵的知识分子(如罗素)发表公共意见,只是履行公民责任,纵然耍点滑头,也不会对他人构成压迫。再则,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霍姆斯语)里挥洒笔墨,作者还须接受该市场的制约,毕竟,最喜欢批评知识分子的,正是他知识界的同行。就像自由的经济市场会自发调节并限制商人抬高物价那样,思想市场也会生成一种约束,令那些过度自我揄扬者付出代价。这是一种定价禁忌,当知识分子确信周遭环伺着竞争者,他就不得不遵守这份禁忌,与自己的出名欲巧妙周旋。
知识分子难免将自己偏好的观点视为一种精神私产,面临批驳仿佛遭遇强拆,以至作出过激反应。据说,“乔姆斯基从来不承认错误。”知识分子作为魅力型职业的一大不幸,是迫使一些人因过度追逐魅力而变得狡诈和乏味。他们不可救药的自我美化欲,有时会唆使其选择霸王硬上弓的姿势。
当然,即使没有别的想法,知识分子也会设法增进自己的魅力,而且,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良好的修辞也是一种文字礼仪,类似给文字打上领带、戴上礼帽。我相信,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一个奔来笔底、极为凑趣的妙喻隽语,难度约与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相当。毕竟,让文章显出教养,让自己富有人情味并多少展现出诗人的情怀和才能,是一种任何情况下都包赚不赔的美事;更别提还有幽默,只要警惕着别把自己弄成职业逗笑者,那么,适时让读者会心一笑,注定将一举两得:既提升自我形象,又便于读者怡然接受自己的观点。所以,无论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自我约束,他若对修辞之道一窍不通或嗤之以鼻,等待他的只能是出局。
美国的联邦大法官群体是一个突出例子,其地位的崇高性和稳定性,几乎先验排除了美化并表现自我的必要性,他只需全力以赴地展示司法观点和判决依据,即大功告成。何况,案件引人关注的话,不管谁执笔,都会拥有读者并引起反响,执笔者无需顾虑太多。然而,以笔墨节制著称的大法官,仍会追求雄浑的风格,写下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意味隽永的句子,让人叹赏不已——他们只是不会跺脚而已。最近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曾在判决书里引用过莎士比亚《亨利四世》里的句子,即那个著名的“霍茨波的追问”,以说明法律是什么:
欧文·格兰道尔:我可以召唤地下的亡灵。
霍茨波:啊,这个我也会,任何人都会,可是,当您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真会应召而来吗?
与斯卡利亚立场相左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在一本专著里同样引用了这个段落。
另一位不久前去世的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曾经夸口,如果将电话号码簿以他的名义出版,“立马就可以变成一部畅销书”。也许没错,但第二次就没人买账了。因为,埃科若非凭着卓绝的修辞本领征服了读者从而令“埃科”成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品牌,电话簿仍将是电话簿。
总之,修辞的伦理功能服务于一种“承诺”(波斯纳语),该功能不会强化作者的理性,但可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可信度或可爱度。两者品级不同,但品级更高者不见得更有效,正如过于严谨的作者总会在擅长向读者的肾上腺素施加法力的作者面前落败。当知识分子意欲争取读者时,他们的行为及心态,会无限趋近竞争选票的政客。为了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并争取更多选票,“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曾于2007年露着乳沟出现在参议院。为了强化自己的人情味,声称自己正热泪盈眶的知识分子,似乎也不可能绝迹,因为眼泪里掩映着一个温柔的胁迫:你不赞同我的观点,就说明你冷漠。
我们认可某种修辞,实质乃是认可某种立场或价值观。读者有时像当事人,他们将某人捧为“大律师”,将某人贬为“讼棍”,往往取决于自己站在哪一边。在一个修辞策略无所不在的公共世界,也许我们最该抵制的,是呯呯的心跳,从而使自己的判断力保持澄澈。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