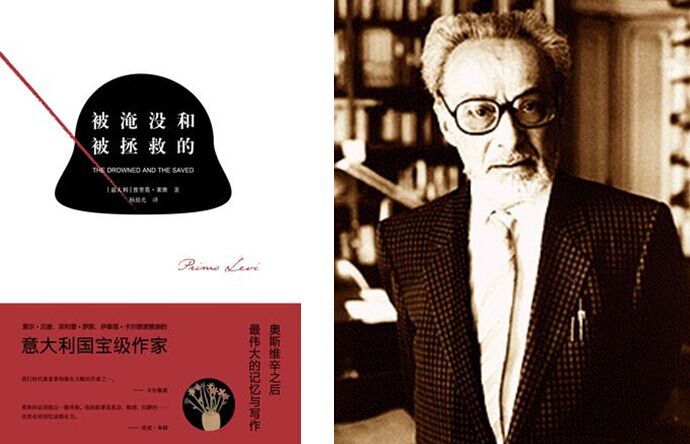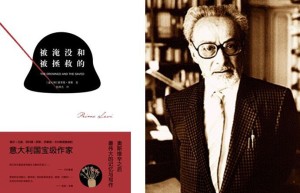
关于二战以及二战犹太人苦难史的书籍可谓卷帙繁浩,就连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洋洋大观,不乏佳作。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普里莫·莱维于1984年写就的《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本书付梓面世后三年,他便自杀身亡。事实上,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着手此书的写作,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作为从炼狱般的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莱维在回忆录中所表现出的克制、冷静与理性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这或许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然科学属性(他是一名化学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天然的“软弱”性格。他在书中说:“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正是因为莱维的这种天然克制与软弱,使得他在对过往经历的思考中,刨除了许多以愤怒、仇恨为基础架构的人类灾难史观。他的“软弱”根性,既不偏激,也不脆弱,他没有在书中声泪控诉非人般的遭遇,也没有以犀利言辞挞伐敌人。他深知无论置身于哪一种极端所发出的声音都将是有失偏颇,且极为有害的,而这本书的价值正是基于这种克制的思考。甚至可以这样说,剔除了激烈言辞和尖锐指责的莱维所传达的思想更具说服力,因为受害者的倾诉在旁观者看来总是带有先天的“本我”冲动,叙述失真、夸张、渲染乃至博取同情都有可能是削弱史学价值的诱因。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责任与判断》等书中对于二战战犯的心理分析、对“平庸之恶”的无情揭露,其条分缕析之精准,用语之冷峻尖锐,让人多少都能嗅出几分愤怒的气息。这种义理分析大有庖丁解牛的轻车熟路,带有学者一贯的思考本能。她虽然也同为犹太人,也同样在二战中遭遇迫害流亡美国,但不可否认,对于二战的分析,她是站在体制外部,站在炼狱外,凭借对地狱废墟的拼凑来对这场灾难进行反思。而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参与者、受害者都是以“人”为单位,当人退化为“零件”,“集体”异化为“粉碎机”时才酿成的一次人为浩劫。缺乏对“地狱”中人性的认知与复杂性的思考,任何一种外部简单粗暴的结论都是极为容易却又极具误导性的。这种结论标榜着对“人性”的充分体悟,却又简化了对人的复杂性的探讨与理解。
十分讽刺且十分矛盾的是,只有那些从“地狱”爬出来的人,才有资格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大规模的“集体犯罪”。莱维,正是这样一个从地狱活着回来的幸存者,在他的叙述下,善恶、敌我、自私与慷慨、人性与兽性都模糊了界限,甚至连生存都可能成为一种罪恶。
一、
在书的开头莱维便兜头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们的记忆也许会越来越不可靠,而人类心里构造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施暴者的记忆会由于对心理创伤的应激反应而逐渐淡化甚至扭曲:“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战后一大波新闻媒体的关注,杂志报章的披露,幸存者的回忆在一遍又一遍的阐述中成为“巴甫洛夫”的狗,完完全全沦为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受到其他幸存者叙事伦理的影响,当头脑中的记忆逐渐模糊时,这种集体的叙事套路就逐渐凝聚成一种“集体性的回忆”,代替了大脑中的独特记忆,成为一种新的“存在事实”。此外,大脑还会自动开启“自欺”功能。就像伤口流血,身体就会分泌促进凝血的血小板一样,当人的内心遭受可怕经历的啮噬时,大脑要么关闭对可怕遭遇的回忆,要么就会想方设法“欺骗”内心,以一套能够说得过去,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论代替“事实”,从而让主体能够在回归平静的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
“保持真伪之间界限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
的确,要想保持记忆的真实性,幸存者们就必须时刻与生理上的痛苦,道德上的内疚做斗争,一刻不得松懈,也因此将会使得他们在此后的生活中依然要背负着沉重的刑架,不断地自我拷问,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些承受不不了良心拷问的人都在战后成批地自杀了。于是回忆,成了集中营的犹太人战后最大的敌人,也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最大阻碍。
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普里莫·莱维)
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嚆矢,“简化模型”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最简单有效的工具之一。宇宙与自然的纷繁复杂与人类的渺小脆弱构成了不成比例的文明发端。人类在不断的实践中,从恐惧与敬仰天地鬼神到破除宗教神秘主义,学会了刀耕火种,构筑了城邦社会,掀起了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简化模型”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对规律和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与掌握。然而,“简化模型”却也因为它的简单粗暴,钝化了我们对于事实的感知,忽视了对“个体”差异性的认知。
就像给图书分门别类贴标签一样,“简化模型”用抽象的笼统概念为我们构建了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社会科学理论和人际行为模式等等。这种分析方式的好处在于,容易理解,容易习得,但在近现代人类的政治进程中,它却发挥出巨大的破坏性。“简化模型”中最基本的一种模型就是“二元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多元论,其本质都是相似的。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党林立,派系云集,相互戮辱攻讦,划地断交,标签加深了误解和分裂,措辞非左即右。集权国家为防止政出多门,概揽大权,令行禁止不容有失。动辄一刀切地集体仿效,或者全盘否定。再譬如网络暴民的“爱国论”,其逻辑之粗暴可笑罕可伦偶。上世纪的文革就是在“简化模型”的荼毒下酿成的一场可怕人祸。在“打倒孔家店”被目为全盘反传统的“常识”时,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文革“打倒走资派”的呼声中,“简化模型”为我们削去了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教我们将刀斧劈向亲人。“简化模型”使政府提高行政效能成为可能,人们麋集在所谓“正义”的阵营中,为“主义”而斗争。
然而,在集中营里,莱维发现他无法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对每一个标本进行分门别类。人性的复杂在这个极端的“实验环境”下被成倍放大,集中营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简单界定为“敌人”与“难友”,“善良”与“邪恶”。这种人性的混沌不明在踏入集中营的那一刻就能感同身受,新来者都会遭遇来自“难友”的拳打脚踢和集体敌视:“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
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在集中营担任管理职务的主要都是集中营里的老资格囚犯,这些人担任着形形色色的职务: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通信员、翻译等等,维持着集中营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对于这样别致而又扭曲的生物链我们既充满了困惑,又分外震惊。在我们既有的认知里,敌人永远是那些压迫者,暴力施行者,受害者永远是脆弱、无力反抗的,那么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人,到底应该被贴上哪一种标签呢?事实上,在集中营极为精密且复杂的体系中,“灭绝”的不单单是生命,甚至包括“人性”。当你了解了整个“灭绝”过程的展开,你甚至会怀疑这是否是第三帝国精心编制,反复推演而制定的一整套“种族灭绝”计划。从犹太人被塞进密不透风的闷罐车开始,这个天衣无缝的“人性”灭绝计划就开始展开了:运送犹太人的闷罐车按照运送路程的长短被塞进不同数量的人,长途运输的车厢内会塞进50人,人们或许可以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挨在一起,而短途运输人数则翻倍至100人甚至120人,几个小时的车程也是极为可怕的折磨,别忘了,被逮捕的犹太人不仅有老人,还有小孩,甚至还有病人、精神病人,逼仄的空间只能容许他们轮流蹲着休息,而最可怕的是,押送队员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和水,以及,最重要的,满足生理需要的容器。于是在长达几日甚至十几日的运输过程中,人们只能在众目睽睽下解决生理需要,并任由液体或固体的排泄物在车内流淌,在密不透风的闷罐车里他们承受的,不单单是生理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由文明世界的人类堕落为原始动物的心理崩溃,那些曾经在欧洲担任医生、教师、商人的犹太人,此刻都无一例外地在别人的目光中脱下裤子解决生理需要。
进入集中营后的日子,党卫军们用饥渴开始慢慢消磨犹太人的意志和身体。从天甫亮一直工作到天黑,中午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用餐和休息时间。每餐只有一个干硬得必须用刀用力切开才能食用的面包,一天的饮水来源只有傍晚的蔬菜汤和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进入集中营后不久,他们就会遭受噬骨的饥饿和比饥饿更为让人冒火的“干渴”。眼球突出,皮肤蜡黄松弛地挂在松散的骨架上,只要一段时间彼此不见面,再次见到对方就会完全认不出彼此。他们在纳粹的“劳动集中营”里被压榨劳动力,为纳粹的企业、军工厂制造商品,搬运重物,挖矿,直至最后一滴血被榨干,那些重病的,老弱的犹太人被定期挑选出来,送进毒气室进行“灭绝”,然后将他们的衣物、金牙、随身物品扒光后再转运到焚尸炉焚毁,纳粹们就连被焚烧尽的骨灰也要充分纳入他们的产业链中——加入建筑材料里,充当添加剂。
你能不惊叹于如此完整的体系运转吗?能不怀疑这是一次事先密谋好的有计划的行动吗?但就连莱维也确信,在党卫军的文件里,一定不会有从上到下的详细到排泄、用水的指示。这完全是一场在集体行为中不断发酵,愈演愈烈的自发暴力行径,却在被高压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里每天上演着。[page]
三、
“They are the typical produ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German Lager: if one offers a position of privilege to a few individuals in a state of slavery, exacting in exchange the betrayal of a natural solidarity with their comrades,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someone who will accept. He will be withdrawn from the common law and will become untouchable; the more power that he is given, the more he will be consequently hateful and hated. When he is given the command of a group of unfortunates, with the right of life or death over them, he will be cruel and tyrannical, because he will understand that if he is not sufficiently so, someone else, judged more suitable, will take over his post. Moreover, his capacity for hatred, unfulfill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oppressors, will double back, beyond all reason, on the oppressed; and he will only be satisfied when he has unloaded onto his underlings the injury received from above.”(Primo Levi《If This is A Man》)
他们(特权囚犯)是德国集中营体制的典型产物:如果一个人有机会跻身为少数特权阶级,代价是背叛与同伴们的天然联盟关系,那么一定会有人点头答应。他将从普遍意义上的人蜕变为一个“灰色地带”的产物。他被授予的权力越大,受到的憎恨也就越多。如果上面要求他虐待下属,由于他掌握着底下人的生杀大权,他将会变得十分残酷暴虐,因为他知道假如不这么做,其他更适合的人将会代替他的位置,把他挤下去。更何况,他的恨还来自于他遭受到的来自上级的虐待,他将这种仇恨无端地,加倍地偿还在他辖下的人身上,唯有如此,他才能在心里找到平衡与满足。(《如果这是一个人/活在奥斯维辛》普里莫·莱维)
集中营的食物配给根本不够正常人维持生命,假如没有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额外食物和水(成为“特权囚犯”或者担任“管理职位”,冒着死亡危险偷窃东西换得食物等等),一个正常人在进入集中营后三个月(刨去生病、受伤的因素)就会因为饥饿而死去,集中营的人性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也同样要完成繁重的工作,甚至要比普通囚犯承担更多的职责,而他们获得的特权也不过是每天多那么半升汤。在集中营里你要时刻提防别人,哪怕是睡觉的时候,也必须看好自己的物品,因为稍不留神,你的衣服、食物就会被偷走或者抢走,而这种错误是致命的,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因此,虽然有许多囚犯担任“特殊职务”,但他们却并没有遭到难友们的敌视或仇恨,因为在集中营里,只要你能获得额外的食物,无论是天赐的“好运”还是凭借智慧,都是令人敬畏的,因为那代表着你有更强的竞争力,有更大的几率在这个地方活下去。
在这个每天都与死亡对抗的地狱里,人伦世界的道德、教化、文明通通都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活下去,以各种方式,以一切方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囚们如果因为表现得好,被嘉奖一个大瓷盆的话,她们会把这个盆拿来当夜间的尿壶(夜里不允许上厕所),早上的洗脸盆和吃饭时的汤盆。在集中营里,任何的物资都是极为匮乏的,刚入营的囚犯没有任何用餐的工具,他必须用仅有的面包来换取工具。
纳粹党卫军们的这些自为的暴力,无意间在整个集中营的试验场里构筑了一套极为扭曲却精密的统治逻辑。统治者们启用了囚犯内部自己人来管理所谓低贱的犹太人,藉以进一步彰显犹太民族道德上的低贱与冷漠,而一旦集中营的丑行公诸于众时,他们也大可佯作不知,毕竟那些鲜血都是沾在犹太人自己手中,更为诡谲的是,他们给予这些特权囚犯生杀予夺的大权,并命令他们折磨辖下的同胞,这和黑手党入门仪式或者恐怖组织的招揽行动一样,是基于相类似的心理逻辑:借你的手犯下血腥罪行,让你不得不与之为伍,并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同时借这种罪行来划清“特权囚犯”与“普通囚犯”的界限,确保管理阶层的“忠心”。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环境下,谁也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但莱维明确表示,他的这番“灰色地带”理论,不是要为谁开脱罪名,更不是模糊纳粹政府的责任,而是以他的智力所及,为我们揭示人性在极端条件下的模糊性与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让每一个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负罪感”,让他们即便在恢复成人以后依然日日煎熬,甚至煎熬更甚。他说,假如集中营最终没有被解放,谁也不知道最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而他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没有犯下罪行。几乎在每一个幸存者的梦里,都不断地萦绕着党卫军们撒旦般的嘲弄:“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得以幸存下来的人,无论是由于一系列的巧合因素,或者智力过人、体能过人、勇气过人,甚或甘于沦为“该隐”,将木斫劈向同伴,他们最终都幸存下来了,他们活过了别人,要么剥夺了别人生存的资源,要么剥夺了别人的生命,要么剥夺了别人生存的机会,甚至于那些死去的人可能比幸存者们更聪明,更有用,只不过因为更敏感,更坚守道德,但无论如何,他们活下来了……
四、
-罗密欧:过来,朋友。我瞧你很穷,这儿是四十块钱,请你给我一点能够迅速致命的毒药,厌倦于生命的人一服下去便会散入全身的血管,立刻停止呼吸而死去,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去一样快。
-卖药人: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多亚的法律严禁售卖,出卖的人是要处死刑的。
-罗密欧:难道你这样穷苦,还怕死吗?饥寒的痕迹刻在你的面颊上,贫乏和迫害在你的眼睛里射出了饿火,轻蔑和卑贱重压在你的背上;这世间不是你的朋友,这世间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没有人为你定下一条法律使你富有;那么你何必苦耐着贫穷呢?违犯了法律,把这些钱收下吧。
无数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甚至艺术作品都将“死”视作一种唯美的,超脱的,甚至英勇的行为,即便是对抗恶势力的行为也被影视剧作品包裹成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些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作品对于现实来说可谓是天大的误会,它们激发了人们内心对抗邪恶的信心和勇气,但却让人们在面对真正致命的灾难时,显得极为幼稚和迷茫。毕竟,作为人类中的大多数,我们都不具备成为英雄的素质,更不具备视死如归的勇气,我们拥有的仅仅是“普通美德”,这种普通美德规范了我们的日常行为,诸如“勿以恶小而为之”,乐于助人,尊老爱幼,凡此种种。而一旦遭遇重大灾难时,“普通美德”便显得碍手碍脚,甚至阻碍人们求生。尤其在“集中营”这种极为复杂且极端的情况下,人被剥夺了所有物质财产以及精神财产,对抗体系严密,荷枪实弹的党卫军,躲过瞭望塔,穿越高压铁丝网林立的外围防护,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不用提在德军连战连捷占领波兰、法国后,欧洲大部几乎都沦入第三帝国铁蹄之下。囚犯们没有体能、没有食物、金钱,没有交通工具逃亡,即便有效逃离,又能去往何处呢?在欧洲所有犹太人都或被绞杀,或被驱离,整个德国与欧洲都陷入一种高压恐怖之中,又有谁敢冒险收留呢?
在所有的历史著作或社科论述中,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误会:“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反观整个集中营的反抗史,几乎都是由“特殊囚犯”组织并领导的,他们由于特殊身份,得以接触党卫军的机密信息以及集中营的机械操控部门,并且有精力有体力筹划并实施反抗运动。那些处于集中营最底层,被残酷压榨的普通囚犯,日日挣扎于生死边缘,是绝无体力、精力甚至欲望去实施暴动。在解放后的集中营幸存者中,绝大部分都是“特权囚犯”,他们是集中营的极少数,却是幸存者中的绝大多数,如此便不证自明了。本书的作者普利莫·莱维也是被甄选为实验室助理而得以幸存下来的“特权囚犯”。
至于自杀,十分吊诡的是,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极少出现自杀现象,反倒是解放后不久,许多幸存者都成批自杀。莱维对此的解释是,自杀是“人”的行为,当一个人处于“非人”状态时,是不会想要自杀的。换句话说,“自杀”是一种经过权衡以后的选择,或是出于自尊受到极度伤害,或出于绝望、罪恶感,或是出于某种“英雄主义”的象征性行为等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集中营里的人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尊严、希望、勇气,他们的身上已经再也嗅不到一丝文明世界的气息,他们遵循的是丛林世界的法则,就像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化用马太福音的一句话:
In history and in life one sometimes seems to glimpse a ferocious law which states: “to he that has, will be given; to he that has not, will be taken away.”
凡有的,还要加給他,叫他有余;凡沒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极端情况下,时间和空间对人来说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人会去谈论明天,“明天”在集中营里就是一个不可能到达的未来,而思考,更是一个阻碍生存的活动,在工作中思考,极有可能使他们分神受伤,而受伤在集中营里几乎是致命的,工作结束后的他们要忙着争抢食物和汤水,防范别人的盗窃,任何文明世界痕迹的冒头都可能影响他们争取生存的努力,直到最后身体的虚弱、疲乏、痛楚,直接让他们放弃了争取机会“思考”的欲望。
只有一次莱维意外受伤在集中营Ka-Be(医院)养伤时,深藏在内心的道德、伦理和情感再次复苏。在Ka-be里,由于伤员和病人不需要做劳力,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消磨在病床上,“人性”的回归让他们有机会审视彼此,反观自我,才有机会哀悼死去的妻儿,怀念在家乡的时光,他们才能意识到集中营的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模样。医院的疗养生活看似惬意、轻松,内心的煎熬却更甚于工作的时光,人性的复苏对“非人性”行为的审判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酷刑。
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还记录了这样一件看似平凡,却十分令人动容的插曲。囚犯们平时的洗漱活动都在公共浴室进行,但浴室经常停水,且水质污秽刺鼻,由于人多资源少,加之纳粹军官规定任何人进行洗漱(无论洗脸还是洗澡)都必须将衣服一件一件脱光,直到洗漱完成再一件一件穿回去,因此洗漱是非常奢侈且十分耗费精力的事情。尤其是在冬天,全身赤裸用污水洗漱是一件充满风险且极需毅力的事情,脱下的衣服必须紧紧地夹在双腿之间,整个洗漱过程都不能有丝毫大意,否则一不留神衣服就会被人偷走。因此,每一次洗漱都伴随着风险。大部分囚犯在冬天都尽可能避免洗漱,但莱维撞见了一个每天洗脸的囚犯,他坦然娴熟的样子,就像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人那样:
“….the Lager was a great machine to reduce us to beasts, we must not become beasts; that even in this place one can survive, and therefore one must want to survive, to tell the story, to bear witness; and that to survive we must force ourselves to save at least the skeleton, the scaffolding, the form of civilization. We are slaves, deprived of every right, exposed to every insult, condemned to certain death, but we will possess one power, and we must defend it with all our strength for it is the last—the power to refuse our consent. So we must certainly wash our faces without soap in dirty water and dry ourselves on our jackets. We must polish our shoes, not because the regulation states it, but for dignity and propriety. We must walk erect, without dragging our feet, not in homage to Prussian discipline but to remain alive, not to begin to die.”
“集中营是一台将人性碾压成兽性的巨大机器,我们必须阻止自己变成禽兽,即便在这种地方我们也要活下去,因为我们必须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别人,因此我们必须忍受痛苦,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尽力保护好这副文明社会的躯体,这副骨架。我们是奴隶,被剥夺了所有权利,任人欺侮,注定死亡,但我们必须坚守不屈从的能力,并尽全力维护这种能力直至最后一口气。所以,我们当然应该在没有肥皂的情况下用污水洗脸,用外套擦干身子。我们当然应该给鞋子抛光,并非因为集中营的规定,而是出于人类的尊严和本性。我们必须昂首挺胸,不能拖着脚走,这并非出于对普鲁士纪律的尊崇,而是为了活得像个人,不至于堕落腐化。”
至于人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惯性。就像一个濒死的人受伤时,他的身体组织也依然会分泌修复物质企图愈合伤口,这是一个机体的本能反应。正如斯维沃在《泽诺的意识》里写到的:“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集中营的生活对他们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他们要经历价值观的冲击,克服并努力抗拒现实对人伦道德的侵蚀,同时也由于他们普遍更加敏感、更富同情心和反思能力,他们的内心遭受更大的煎熬与折磨,直到最后彻底脱下文明社会的盔甲,成为肉搏厮杀的原始动物。他们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间和空间里经历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异化过程,这使得他们在集中营解放,恢复人性的思考能力后,内心承受更大的冲击。而对于那些原本就从事体力劳动的贫苦阶层来说,集中营的生活不过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翻本,只不过更劳累,更残酷而已。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需要为生存寻求意义与出口,更不像他们毫无体力劳动的经验,不懂得如何使用劳动工具。他们无论生活在哪里,追寻的都永远只是纯粹的活下去而已,因此他们的内心负担更为轻盈,而且他们普遍膂力过人,经验丰富,知道如何用最省力的方式使用工具,完成工作,如何避免肌体的损伤,如何停下休息,避免因过劳而致命。
然而,战后的犹太血泪史以及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都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尽管在残酷的丛林竞争中他们显得无能与无用,但对于人类历史进程来说,他们是极为重要的见证者与叙述者。那些在血泪炼狱里沉沦的贫苦大多数只能在历史中默默地承受着,又默默地死去……
五、
莱维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反观历史灾难性事件的另一种视角,他具体而微地叙述着他见证的,经历的,让我们在胶柱鼓瑟的众多二战回忆录看似阡陌分明,经纬有度的宏大叙事之外,从另一个侧面感受到处于灾难核心的人性的混沌与暧昧。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偶然事件,类似的人类灾难是否会以新的方式再次席卷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些交织在集中营里的种种人性异化,以及人性在极端情况下的复杂性,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警惕作用。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察觉到许多类似的人际异位关系,在或大或小的权力与组织结构里能体会到类似的移情心理。
我们总说“历史惊人地相似”,但处于现实旋涡中的我们却也往往因此而忽视了一场异化灾难的重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形态,经济条件与人文水平决定了历史不可能以复制的方式重演,但假如我们不够审慎,或者过分狂妄与冷漠,也许我们下一次迈入的是无人解放的人性灭绝营。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