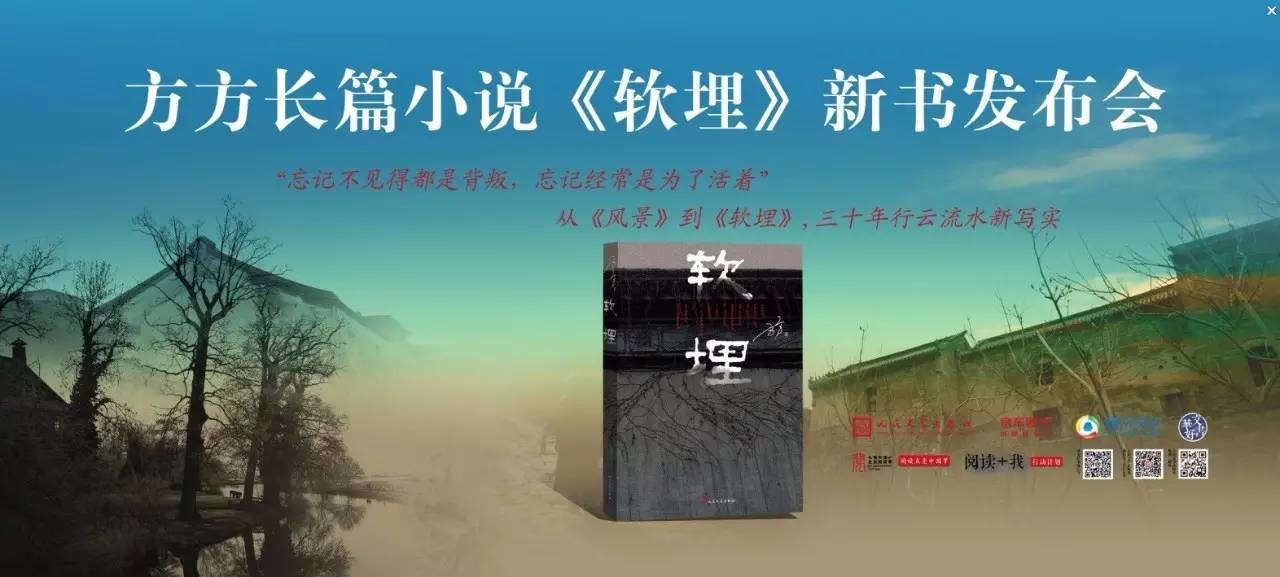第六章
第七章
34. 地狱之第四:西墙的美人蕉下
丁子桃业已筋疲力尽。她清楚地看到,自己已经上了第四层。比起前面,这里似乎隐隐有了几丝微光。
她看清楚了,甚至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西墙。
这是三知堂花园的西墙。这堵又高又长的西墙,她再熟悉不过。整道墙蜿蜒几百米,顺山而下。砌墙的石块大而厚重,里外的石缝都长满青苔。墙半腰的枪孔,也历历在目。西墙角上的碉楼,也进入她的视线。她的公公特意把这座碉楼平台加盖了四角的亭子,亭角飞翘,给人感觉像是吹风赏景的亭台。但她知道,亭子中间放着一门小炮。当年防匪时,这个炮台最为威风。
西墙下正被阴影笼罩。满墙遍布的爬墙虎都已枯萎。墙边那丛美人蕉鲜红如焰的花冠,也已蔫成枯桩,仿佛都是气息奄奄地熬过了寒冷。
她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陆家的三知堂是哪一年。
她仿佛一生下来就知道三知堂。这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三知堂比她家在更深的山里,但是,父亲每年都会去那里。父亲说,隔得很远,就可以望到高高在上的三知堂,西墙仿佛绕了半架山。而三知堂的花园就在那堵高墙后面。
墙角的碉楼也是乡里人喜欢指着说的。说是老早前,山里一个覃姓土匪人多势壮,他想抢劫哪个村,没人能挡住。可是当他抢劫三知堂时,却被碉楼上的火炮,堵在了墙外。土匪非但没法靠近,那姓覃的头领反倒被碉楼上的一炮轰死。三知堂的高墙后,有多少个天井,多少个房间,没人说得清,就算她后来嫁进了陆家,也没有弄清过。
她是父亲带过去的。她的父亲胡如匀和三知堂主人陆子樵曾经一道留学日本。陆子樵回国后,随即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从政,直到告老还乡。而她的父亲,子承父业,回国接下祖父的盐井生意,又代其管理着乡下家族的百十亩地。闲时便呼朋唤友,吟诗作赋,藏书收画,附庸一下风雅。
父亲在路上告诉她,三知堂是陆老爷祖父修建的。这位老爷爷在清朝也做过官。“三知”乃源于杨震所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他想要向子孙及世人表明自己从官一生,做人做事却都十分清白。天知地知我知,他去掉了“子知”。她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掉一知呢?父亲叹说,他的祖上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人言可畏。所以他认为,已有天知,亦有神知;我知即可,你知不必。父亲说完又叹:“而今天下,还有何等人肯守四知呀?”
丁子桃瞬间连父亲长叹时的神情都想了起来。
便是这次,陆家二少爷陆仲文带着她闲逛至他家花园的西墙下。西墙沿山而上,步步修有青石台阶。墙上的枪眼,可见一道道的火药痕迹。凑上前朝下望,山下田园屋舍,尽在眼中。
西墙的边角,一丛美人蕉正开着红艳艳的花。
她说:“我姑婆讲,美人蕉是佛祖脚趾流出的血,所以它红得与众不同。”陆仲文望着她笑,笑罢说:“弱植不自持,芳根为谁好?虽非九秋干,丹心中自保。你想的是血,我想的是诗。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她说:“不知道。”陆仲文说:“南宋大家朱熹哩。‘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是他写的。”她说:“连这句我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念了中学?”陆仲文便又笑了起来。她被他的笑声所打动。
他们相互生情,应该就是那一次。之后,西墙便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墙尽头碉楼上高耸的小亭子,也是他俩小坐之处。小火炮仍然在。他们时而会坐在炮台上,也常常倚在亭栏边,吹风,念诗,听陆仲文吹口琴。
而现在,陆仲文呢?
丁子桃不禁叫了起来:“仲文,你在哪里?”
她的声音似乎被西墙的枪孔吸了进去,四周除了风,却没有一点回响。
而此时的她看到了自己。这个叫黛云的自己,正跪在这一丛美人蕉下。
她正在朝一个坑里填土。
坑里躺着两个人。一个是小茶,这是她从娘家带到陆家来的丫头,另一个是紫平。紫平原是照顾老祖的,她嫁进陆家后,老爷就派给了她。她们俩肩挨着肩躺在一个坑里。坑挖得有点小,两人侧躺着都有点挤。她不忍小茶挤成这样,便拖出小茶,让紫平睡在下面,把小茶摆放在紫平身上。
天黑得厉害。她推着坑边的土,一把一把朝她们身上堆。泥土最先盖住小茶的脚,又盖住她的身体。快要覆盖着她的脸时,她忍不住伸手抚了一下小茶的脸。蓦然间,她觉得小茶还有气息,忍不住叫了起来:“小茶!小茶呀!你要醒了就跟我走。慧嫒她不去了。小茶,我不能丢下你。”
小茶没有回应。小茶十岁就跟她在一起。是她家的丫头,更是她的玩伴。她嫁来陆家,小茶作为陪嫁也随她而来。多少年里,她每喊小茶,都能听到她清脆的回应。此时此刻,小茶却不再搭理她。无论她怎么叫喊,她都无声无息。而她给以的回报,却只是一捧一捧的泥土。她把泥土洒在小茶身上,嘴上抱怨道:“小茶,你应该悄悄地跟着我走。富童在河边等哩。船上还能坐一个人。”
小茶来向她告辞过。那时她刚刚喝过了酒。小茶走到她的身边,说:“小姐,我不能陪你了。你要记得我。哪天你回家,要把我挖出来,放到棺材里,埋我到我妈旁边。”她答应着,抱住小茶哭得无法自制。小茶也哭。直到门口传来紫平的叫喊:“小茶,我们一起走吧。”小茶方掰开她的手,独自走了出去。
她们再见面时,小茶和紫平已然并肩躺在了这丛美人蕉下。
她把最后一捧土,均匀地洒在小茶的脸上。她看不见小茶的表情,也看不清小茶的头发是否凌乱。她没有了眼泪。甚至也没有了悲伤。
这是她在陆家花园埋完的最后一个坑。她知道,她必须走了。
她回到房间,把汀子放进背篓,上面罩上布,再把背篓挎背上。突然间,她看到床边有一只手镯。这是她送给小茶的生日礼物,想来小茶走前又悄悄地还给了她。她匆匆拿起手镯,再次回到花园。
园里到处是土堆。暗夜中,寂静如死。没有虫鸣的声音,连花草树木也都死掉一般。这花园,已经是座死园了。她想。
她走到西墙的美人蕉下,弯下腰,刨开土,她把手镯放在小茶的手上。没有月光,但她却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园新凸的土堆。她回转身,向园里所有的土堆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进碉楼。她想,我怎么可能还会回到这里呢?小茶,对不起了。我要永远忘记三知堂,永远不再回来。
十几分钟后,她从碉楼底层楼梯后的暗道中跑出。洞外是茶园,洞口在密集的几排茶树后,周围长满杂草,极其隐秘。再几分钟,她便见到了老樟树,翻过篱笆,走了十几步,小路即在眼前。然后,她在那路上奔跑了起来。
35. 地狱之第五:花园里的软埋
是的。丁子桃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第五层。
她已然明白,现在她正沿着自己的来路往回走。她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每一件事的细节,每一个场景的气氛,每一个人的神情,还有所有人说话的声音,她仿佛都清清楚楚。
她的公公陆子樵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时,他的魂魄是饱饱满满的。而他在活的过程中,一路失魂。丢完了,他就没魂了。旁人以为他已死,其实没有。他正掉转过身,一点点拾回他洒落的魂魄。能拾得回来,就能得道。再投生时,会到一个好人家。拾不回来的,就难说了,下辈子做猪狗都有可能。
她想,我要把我的魂一点点都拾回来才行。下辈子我要到好人家去。我不想再受活罪。
现在她来到了花园。她看到站在里面号啕的黛云。她沿着黛云面对的方向看去,这场面,令她魂飞魄散。
此时的花园一派死寂。到处是坑,到处的坑边都堆着新土。这是陆家的人自己为自己挖的坑。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堆的土。他们挖完坑,堆好土,相互之间并无言语,不说再见,只是各自一仰脖,喝下了早已备好的砒霜,然后自己躺进了坑里。
枣树下的坑里,躺的是公公和婆婆;离他们不远是玫瑰花坛,花坛中也有坑,里面躺的是三姨太。东墙的竹林中,坑很浅,这是久病的大少爷伯文自己挖的。他没有力气,坑没挖好,人便躺下了。他说,虽然没有棺材,但与竹为伴,也是一种雅死。大姑的坑挨着大少爷。大姑说,我没后人,讲好了伯文当我孝子的。我要挨着伯文。
水池旁的坑挖得最深,是管家老魏的。吴妈距他不远,吴妈是伺候老祖和婆婆的,说是一起走吧,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花园的每个角落都有土坑。每一个土坑里都躺着她熟悉的人。这是一整个家族的人。他们选择了一起去死。公公说,你要抓紧埋土,不要让明早的光线照着我们的脸。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层。屋里的灯全灭了。地色和树的阴影咬合在了一起。花园里没有一丝风吹来。春天已临,但冬季还没走完。园子里所有动物植物都蜷缩着。这是一个无声无息无色无味的花园。
她开始填土。每个坑旁都有工具,根本不用她另外去拿。她疯狂地把土往坑下堆。公公、婆婆还有老祖的坑挖得深,这是老魏帮着挖的。老魏挖的时候,还笑,他说:“陆爷,我能跟您二老一起死,而且死得一模一样,是我的福报哩。我爹妈就没有这个运气。”老魏的妈是在回娘家的路上,被土匪打死的。而老魏的爹从河南送货回来的途中,被日本人抓去,死在了牢里。两个人死得连尸骨都不知道在哪。老魏把老祖的坑挖在自己的附近,他放老祖躺下时说:“您一路别害怕,我隔您不远,我晓得保护您的。”
婆婆一直在哭泣。她不停地说:“我不想软埋。我妈说过,软埋是不得转世的。”
公公喝下砒霜,边躺进坑里,边骂她:“你想活着,就去跟村头的老麻拐睡觉好了。他早说了,他什么都不想要,只要你和家里的红木床。你跟他去吧。转世?你光想转世,你往哪儿转?”婆婆打了个寒噤,把砒霜水一饮而尽。她躺在了公公身边,用头巾遮住了自己的脸。
埋土的事,原本是由她和小姑子慧媛一起来完成的。但她去叫小姑子时,她已经口吐白沫,倒在自己的房间。她惊叫着,拼命摇着她喊叫她,慧媛微睁开眼,说:“爹妈都死了,我也不想活。是我害了大家。我虽然没有告诉金点什么,但金点恨陆家却是因我而起,我不能独活。嫂子,你把我埋到爹妈身边吧。我到地下去侍奉他们二老和大哥。”
她一时无语。想说句话,句子已经碰到牙齿,但还是没有说,只是用口水把那话咽了下去。
她把慧媛扛进花园。离公公婆婆的坑几米远的月亮门是慧媛最喜欢的,她常常带了同学在这里演戏。月亮门是慧媛出场亮相的地方。她挖坑的时候,慧媛还没有断气。慧媛说:“谢谢嫂子代我挖坑。”
她没有回应慧媛,只知道用力地挖土。她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似乎很快她就挖好了土坑。她放慧媛下去时,慧媛的脸已经冰凉。她解下自己的围巾,覆在慧媛的脸上。
这一夜,她不知道埋了多少土。日常屋里曾经从早到晚窸窸窣窣的人声,全都消失。那些曾微笑的、忧伤的、咧嘴的、垮脸的以及阴郁的,在此时全都变成了一样。
经历了这样的夜晚,她想,你们以为我还是活着的吗?
最后,她来到了西墙下。
她要掩埋紫平和小茶了。这是紫平最后的交代。紫平说:“你先埋他们吧,最后埋我。万一时间来不及,就不要管我了。我不怕曝尸。死都死了,曝尸又算得了什么?”紫平的妹子紫燕是山南坡顶村陈老爷母亲的贴身女佣。分完浮财,陈老爷一家被枪毙了。村里人来分抢家中女佣。村组长要了紫燕。他家二儿子是傻子,紫燕当了他的儿媳妇。有一天紫平上山去探望了妹子,回来说:“这样活,不如死。”
她理解紫平。她知道,对于紫平这样的人,死去才是活路。不久前,她的二娘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的二娘说:“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去死,不然会活得比死更难看。”
决定去死并不容易,这个讨论从清早听到全家都将去祠堂接受批斗的讯息时就开始了。但决定了之后,却并不难做。大家默默地、从容地去完成自己的决定。
她感念紫平的义气,也为了小茶,时间纵然紧迫,但无论如何,她也要把她们都葬进土里。本来人死软埋已是天大的委屈,如果连泥土都不覆满,对于她们,活命一场,又该是多大的不公平。
按照公公的要求,她业已完成了所有土坑的掩埋,全身的气力几乎用尽。此时的她,见到躺在土坑里的紫平和小茶侧身挤在一起,不由双腿一软,跪到了地上。
那个同她一起长大的小茶,那个她已习惯身边永远都在的小茶,此时却躺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里,由她亲手用泥土覆盖。从此她的呼唤不再有回应。
36. 地狱之第六:最后的晚餐
丁子桃上到了第六层,她走得有些艰难。现在,她觉得自己落进地狱也是应该。她为什么不在花园里为自己挖个坑呢?她为什么要亲手把他们一个个埋葬呢?
光线更亮了一点,她不知道是距离天堂近了,还是距离人间近了。总之,她的眼睛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多。
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影映入眼帘。她一个一个地数。有九个,或是十个。他们的面庞越来越清晰。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她。然后她也看到了自己。
这是她所熟悉的小饭堂。小饭堂和粮仓相隔不远。隔着一条通道,是灶房。灶房后的一个院落,是下人们住的地方。她嫁来陆家后,多是在这里吃饭。他们经常两桌吃饭,老辈人一桌,小辈人一桌。过年时,家中老少都回来了,小饭堂坐不下,便用大饭厅。大饭厅可以同时放八张大桌,那时候,吃一顿饭就像看一场大戏一样,好不热闹。
现在,是年后。陆家四个儿女,只有老大和女儿在家,老二老三都外出了。此刻的主位坐着老祖,公公和婆婆分坐在她的两边。大姑和三姨太分坐在公公和婆婆身边,病弱的大哥陆伯文则紧挨着大姑身旁。这六个位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因为这六个人永远都在家里。而其他人便可随意了。
现在,小饭堂摆上了大桌。在家的所有人都呆滞着面孔来到了这里。家里发生了大事,是灭顶的事情。
公公的长胡子不停地抖动。公公去官回乡后,胡子就白了。她知道,公公一旦愤怒,他的胡子就会情不自禁抖动。她想,这是他腮帮里的骨头在生气哩。
婆婆哀伤着面孔坐在他的身边,她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一生听从于公公的安排。她总是说:“你嫁了男人,你的命就是他的了。”老祖是公公的继母。她已经很老了,在陆家只是活着而已。她像以往一样,戴着黑色平绒帽,不发一声。三姨太垮着脸。她很想活下去,但她同时也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大姑的表情永远是平淡的。她结婚一个月,丈夫出川抗日,死在前方,她由此回到娘家。多活一天,少活一天,她觉得无所谓。病容满面的大哥依然一副猥琐模样。只有系着长辫的小姑慧媛,头发散开来了,脸上满是疑惑。平常不上桌的管家老魏也坐在那里了。以前家里用人有几十个,一解放,就解散了。留了一些无处可去或是家里必须用的人。眼下在家的只有吴妈、紫平和小茶。她们此刻也没有忙碌,以同样哀伤的面孔.立在一边。
长胡子的公公面色严峻,他低沉地说了一句:“大家也都看到了。坡南坡北的大户人家,被羞辱折磨完,大多都也还是个死。没死的也活得不像样子。还有,黛云家里,我们也都知道。她爹不过继承祖业,开个铺子,喜欢收藏点书,自己也写个字画个画,待人厚道,事事讲忍。黛云她哥还在帮政府做事,他到处征粮,连我家也没少征一粒。结果呢?凌云回来救爹妈,走到半道,就挨了黑枪。爹妈没救成,还搭了自己一条命。黛云,你不要哭。你哭也没用。所以,我们陆家人,在这里光宗耀祖了几辈子,我陆子樵摆不下这身骨头架子,也丢不起这个脸,更是吃不起这份儿打。我不如自己死。”
婆婆首先哭了起来。婆婆说:“我的孙儿汀子怎么办?他还没满两岁,你叫我怎么跟仲文交代?”
公公说:“汀子不能死。黛云带了汀子还有慧嫒今晚就逃。我会告诉你们怎么离开。我已经安排了富童在河边等你们。船太小,只能上两三个人。河水流急,太险,也走不了大船。家里其他人,愿意死的跟我死,不愿死的,各自想办法离开。”
老魏说:“现在外面已经有人看守,谁离开都难。如果没离开,这屋里要是死上几个人,剩下没死的也不会有好下场了。”
三姨太也抹着眼泪,说:“死了就不丢脸了?把我们尸体拖到乱岗上喂狗怎么办?”
公公说:“离开三知堂,没有船,也是逃不出去的。我想过了,想跟我走的,各人自己在花园里找地方挖个坑吧。黛云、慧媛,你们连夜把大家埋了再走。人了土他们是不会挖出来的,这是犯大忌的事。我谅他们谁也不敢。不想跟我走的,自己想办法找活路吧。”
小姑慧嫒说:“爹妈都死了,我活着做什么?”
公公不理她,望着黛云说:“你带着慧媛,先逃到仲文二舅家。他们会送你们到上海。你找到你家表兄,他跟仲文一向关系好,想必会帮你去香港跟仲文会合。叫仲文带你们去英国找他四爸。在那里找份事情做,做什么都行,告诉他,不要回来,这个家已经没了。将来给慧媛找个好人家,也算你替我们陆家做件好事。”
老祖说:“我要入土。”
三姨太说:“棺材都没有备,怎么人土呀?”
公公铁着面孔,低吼了一句:“软埋!”
婆婆的哭泣声变大了。她说:“我不要软埋。软埋了就不会有来世。”公公斥着她说:“你还想来世?你还来这世上做什么?”
婆婆又哭了起来。大哥伯文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他开了口。伯文说:“妈,爸说得是。你看前村后村和我们村,比三知堂势弱钱少的人家,也都是活没一个好活的,死没一个好死的。我们陆家几代人在这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爸更是要脸面也要骨气之人,不能那样被羞辱。我惭愧,一身是病,没有一点能力帮家里。我能帮的,就是陪爸一起走,不叫人耻笑我们陆家。”
公公说:“老大好样的。就这么定了。要走的,各自去穿套像样的衣服吧。”
几个下人都哭了起来。公公朝他们挥挥手,说:“想走的,就走吧。外面的人都等着要你们哩。”
吴妈低泣道:“我在陆家有年头了。跟他们谁也过不来,他们也饶不过我。我跟太太一起走吧。在地下还给你们做饭。”
紫平哭着说:“老祖,我也跟您走。我知道村东头墩子点着要了我,他不聋不傻,有模有样,可我见他在斗争会上揍西村的岳老爷了。下手好毒,我不想跟这样的人。”
三姨太说:“小茶,你被派给二秃了。你要跟他吗?”
小茶摇摇头,哭道:“我不跟他。我讨厌他。”
三姨太说:“你如跟了他,富童这个二愣子回来必定跟他拼命。富童现在能拼得过他吗?他在村里是积极分子。你如不想死,富童就是个死。”
黛云生气道:“姨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小茶是丫头,她凭什么死?”
小茶哭得说话不团圆,小茶说:“姨娘说得是。我如跟了二秃,富童必是不依。他现在哪里斗得过二秃呢?我走好了。我走了,他们都死心了。”
公公的脸板得更加厉害。他说:“既然大家都跟了我,那好,也没什么可以哭的。这是我们的命。有人要命不要脸,但我陆家的人,都是要脸不要命的。”
她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此时抬起头来,对公公说:“爸,我也要跟你们一起走。”
公公说:“你闭嘴!你埋了我们,带着汀子和慧媛逃命吧。我留你,也是要给你胡家留个人。九泉之下,遇着你爹妈,我好交代。你带好我家汀子,算给我陆家也留个根。”
她哆嗦了起来,突然背上疼得厉害。那是批斗她的家人那天,她从家里逃出来时,被人用枪托打的。她说:“爸,我好怕。我不怕死,我怕活。”
公公说:“老魏,拿瓶酒来。”
老魏拿的是一瓶泸州老窖。公公说:“喝了它。喝他三杯你就有胆了。然后带了汀子回你屋里。听到花园没了动静,再出来。把大家埋好,你就算有功德了。”
她不敢违背公公的话,接过酒瓶,拧开盖,咕噜咕噜地灌了一大口。灌猛了,她不禁大咳。小茶过来捶着她的背。她咳了几下,又接着喝。
刚喝一小口,又咳。老魏抢下了瓶子,说:“够了够了。太多会醉。真醉倒,醒不过来就糟了。”
直到这时,公公一指桌子,说:“大家吃饭吧。吃饱了,好上路。”
这是陆家最后的晚餐。吴妈几乎把家里的存菜都做上了桌。仿佛知道彼此将结伴而行,此刻,不分主仆,大家默默地围坐一起。因没有人说话,咀嚼声音立即变得大了起来。
不安和压抑笼罩着饭厅。窸窣之中夹有低泣的声音。泣声大了,公公便瞪眼过去。声音立即被镇压。
37. 地狱之第七:有人送来口信
丁子桃在胆战心惊中爬到了第七层。原本有的揪心之痛,渐渐发散。她已经开始进入麻木。麻木到眼见的一切,既相识,也陌生;既参与其间,却又与己相隔遥远。
送信的是天没亮时出现的。来人急促地拍打着大门。
响声惊醒了汀子。汀子放声哭了起来。她忙爬起身给汀子把尿。这时候,她听到打开大门的嗡嗡声。陆家的大门其实很小,在高墙下,仿佛是个洞,只够两人并肩而人,进门才可见开阔葱茏之庭院。门外行者,不加注意,根本想不到,这小门之后,乃是一豪族大宅。陆家的祖辈,曾经专事贩卖鸦片,从种植、制作到销售,一条龙流水线。山上的茶园早先种的是满山罂粟。因是贩卖鸦片起家,陆家祖辈方才低调行事,小心翼翼。直到陆子樵的祖父做官后,陆续改罂粟园为茶园,及至她的公公陆子樵一辈,陆家已经洗白而为正当望族。
门是单扇,上刷朱漆,无门环,只有凸出一截木头为门把手。木把手被摸的时间久了,油滑生亮。门板很厚,门开时,会发出沉重的嗡嗡声。她的公公陆子樵说,大户人家的门就该是这样响的。门不一定要大,但门声一定要有气势。来客进门,听到声音,就知进到了什么样的人家。
丁子桃想,她家就不是这样。她家且忍庐的门比这个大,与寻常院落一样,是对开门。黑漆,门上有环。她曾经问父亲,为什么我家的门跟陆家的门开法完全不同?父亲说,我们祖辈一直是读书人家,我们不需要遮掩自己。我们不心虚。所以,只要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其实这世上最不被人注意的人,是跟大家一样的人。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想到这些,丁子桃这一刻心里发出冷笑。她想,无论你们用怎样的方式低调,你们都一样没得好死。
开大门的是管家老魏。她将窗子推开一条缝,想看看怎么回事。
老魏说:“哪有这么早来家找人的?”
来者是邻村一个叫陈波三的年轻人。陈波三说:“我妈让我必须赶早来。我叫陈波三。魏大爷您该记得。三年前我妈被山上石头砸着了,是陆老爷救下我妈,送她到县城里治好的。如不是陆老爷,我今天就是个没妈的娃了。”
老魏说:“我记得这事。你赶大早不是来说感谢的吧?”
陈波三说:“是有紧急事,天大的急事。我妈说,必须我亲口告诉陆老爷。”
老魏说:“陆爷没起床,你先跟我说,我看要不要请陆爷起来。”
陈波三急了,说:“真是大事。我妈昨晚就想让我来的。后又说,还是让陆家睡个安稳觉吧,往后就没机会了。”
老魏说:“这是什么话?”
陈波三说:“这是我妈的话。我妈再三交代了,必得亲口跟陆老爷说。她要回报陆家的恩情。”
老魏打量了一下陈波三,然后说:“看你面相也善,你等一下。”
几分钟后,老魏把陈波三带了进去。
她没有跟过去看。她不是好事之徒。同时她也知道陆家的规矩,当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当知道的,你也不必打听。何况,她困得很,一个多月来,她几乎没有睡一个安稳觉,似乎夜夜里能听到爹妈的惨叫和二娘的咒骂,以及打死他哥的枪声。
天没亮透,她被小茶叫了起来。小茶脸色惊慌,说老爷让大家都去他的书房。一大早这么着,必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她草草梳洗,让小茶抱着汀子,一起赶了过去。
书房里气氛很压抑。压抑的缘故,是她的公公陆子樵铁青着脸,胡子抖动得像是有人在刻意摆弄。他来回地踱着步,一言不发。而她的婆婆则挂着一副哭相,满脸悲伤。
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她当即想到的是会不会她的丈夫陆仲文出了事。陆仲文到香港去了几个月,一个多月前来过一封信,此后再无音讯。全家人都在为他担心,不知道他是否平安。
小姑子慧媛最后进来,她嘟着嘴说:“这么早,天又冷,我爸是做啥子嘛?”
她扯了一下慧媛的衣衫,低语道:“不会是你二哥出事了吧?”
慧媛说:“嫂子你放心,我二哥多聪明的一个人呀,他永远不会有事。”
她心安了一点。她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公公终于停了步子,他望了所有人一眼,方低沉着声音说:“大家能猜到,家里出大事了。今天清早有人来送信,说明后天,村里要开始斗争我们家。陆家是远近最大户的人家,我又在国民政府当过官,说是不斗不足以平民愤。要连斗一个礼拜,家眷都要去陪。附近村子的农户也被要求过来参加批斗会。”
屋里立即静下来。静得出奇。静得能听到每一个人的心跳,并且能从这些轻重缓急的心跳中,听出哪颗心属于哪个人。
她立即浑身发软,那样的场面,她是经历过的。站在那样的台上,唯有求死之心。想要活着,不知要下多大的狠心。
时间如同静止,却又于静止中悄然流逝。最后竟是吴妈先出声。她颤抖着声音说:“先吃早饭吧,都凉了。”
讨论便从早餐桌上开始。最先出声的是慧媛。慧媛说:“爸,我不要点天灯。”
她说完这句话,眼睛便望着邻座的黛云。所有的人也都朝黛云望去。黛云立即泪飞如雨。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
公公说:“我不会让你点天灯。但是,如果要你被人斗争,你怎么样?”
慧媛坚定地说:“我宁可死。”
慧媛的话让所有人心头一震。
公公说:“嗯,说得是。现在,我们要商量的就是,我们被斗后,还有没有活出来的机会。如果没有,我们要哪一种死法。是要被斗死,还是……”
他说着,犹豫了。他的眼光投向老魏,似乎示意,请他把话说完。
老魏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说:“老爷的意思……意思是是是……大家是愿意被斗死,还是愿意自己找个法子死?”
公公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得幸有人报信,所以,我们还有时间来弄明白我们活得活不出来。如果能活出来,当然是好。如果活不出来,我们就要清楚自己该选择怎么个死法。”
黛云说:“村里老少不是已经联名写信说爸爸是大善人,推翻清朝时立过功,给山里游击队送过药,剿匪期间还带解放军进山去瓦解大刀会,征粮也出得最多。而且上级不是已经同意不斗陆家吗?”
老魏说:“但是新来的组长不认这个,它没用了。”
慧媛说:“为什么新组长不听大家的意见?”
公公望了她一眼,说:“因为他是王四的儿子。”
一家人都惊哦了一声。然后眼光都投向慧媛。
黛云的心猛然跳动得厉害起来。她和小茶相互望了一望。小茶朝她轻微地摇摇头。她心领神会,轻微地点了一点。
慧媛尖叫了起来:“你们都看我做什么?那是他的事。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三姨太说:“不是你告诉金点,他爸是怎么死的,他会离家出走?这下好了,回家来报仇了。”
老魏说:“这小子忘恩负义,怎么说也是陆家把他养大呀!”公公板下了面孔,厉声道:“不关任何人的事,这就是命!”
原本被这个家庭早已忘记的王四,此时此刻,强硬地在所有人面前浮出他的面孔。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的陆子樵还年轻,管家老魏也还年轻。陆氏家族想要重建祠堂。家族长辈把这件事交给陆子樵和魏管家来办。他们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了一整天,然后告诉他们,附近哪一片地最合适。结果那片地是王四家的。王四的祖父早前曾是陆家老祖的随扈,随陆家在此落户。十八亩良田也是当初老祖以他护卫有功而赠送的。陆子樵认为这是件很好商量的事。但当老魏前去跟王四说,陆家愿增加两亩地予以交换,或以高价买下那片地时,王四却不肯,称爷爷和父亲死前都说过,这地是爷爷的命换来的,是王家的根。现在他的家人也就是靠着这块地在过日子。谈了好几天,没谈下来。陆子樵甚至亲自出了面,王四还是不答应。陆子樵那时还在外面为官,面子挂不住,发了脾气。那王四也是个犟人,居然也发了脾气。于是闹崩了。这事就僵持着。
陆子樵和老魏正在想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时,发生了一件事。
王四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老婆又怀着一个。那天下大雨,山洪随之暴发。结果王四的老婆快生了,接生婆冒着大雨赶来家时,发现是难产,不敢接生,要王四赶紧送到城里找洋医生。进城的几条河沟都淹了水,村里只有陆家的马车过得去,并且陆家的马车有篷,能挡风雨。王四无奈,急跑到三知堂找管家老魏。老魏满口答应,说借马车没问题,但得先把卖地的事办妥。王四依然不肯,掉头而去。回去转了一圈,希望接生婆能把孩子接下来。接生婆再三说不敢,怕出人命。又说,你还晃个啥子,先救人要紧,两条命比天大呀。王四一听也怕了,再次急吼吼跑去陆家,仓促地在契约上签字画押。老潘倒也守信,立马叫了马车夫随王四而去。但料想不到的是,王四老婆一路惨叫着到了医院,孩子平安生了下来,王四的老婆却没有保住命。医生说,早来半个钟点就好了。老婆死了,祖传的地也没了,王四几近疯狂。拿了卖地的钱,领着几个孩子,就不知道去到了哪里。陆家虽然拿到了地,却因王四老婆的死,觉得那块地带有人血,不吉利,也不愿意在那里修祠堂。
两三年后,有人送了一个男孩到陆家,说是一个叫王四的人让他送来的。孩子身上夹着纸条,纸条上写着:“替我把娃儿养大,就扯平了。”老魏忙问王四本人呢,那人说,死了,病死的。老魏吓着了,又问他女儿呢,那人说,没见过,可能早卖掉了吧。这件事对陆家震动好大,老魏也悔死。事已至此,陆子樵决定把这孩子养大,并且说,以后那十八亩地,就是他的。那孩子叫王金点。金点在陆家长大,具体照顾他的人就是老魏和吴妈。老魏心有愧疚,也很善待那孩子。陆家孩子上私塾,金点也跟着一起念书。念完私塾,陆家孩子进城里读中学,金点才开始跟着长工们去干活。本来也相安无事。但两年前,有一天金点没有给任何人留一句话,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三姨太说因为慧媛告诉了金点他们两家发生过的事,理由是太太头一天为警告慧媛不要跟金点走得太近,讲述了陆家与王四家之间发生过的事,结果没几天金点就走了。而慧媛一直不承认。陆子樵没有责怪任何人,也不准大家再议论此事,只是说,十八亩地还给金点留着。
但是,现在金点却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来了。
静默的时间太久。
慧媛有点耐不住,她大声嚷了起来:“我去找王金点。陆家对他怎样,他心里应该有数。”
公公呵斥了慧媛一声:“你闭嘴。坐下!一步也不准出门。我们陆家有什么事需要你去出头?我们陆家又有什么时候求过王家人?”
三姨太嘀咕道:“死到临头还摆什么架子呀。”
公公的声音更大了:“你也闭嘴!”
这几声厉喝,震得人人心里发颤。
这天的早餐吃了很久。吃完饭也没有人离开。整整一天,全家人都在讨论,此一次,有没有活出去的机会。如果没有,应该怎么办。
西村的范家,全家被赶出大宅,住进了牛棚。宅院被充作了仓库。北坡的刘家宅子,呼呼地住进了七八户人家。正房偏房都住的是外人,自己一大家子挤在下人的屋里,进进出出还要受气。当年见着他们点头哈腰的人,全都踩着他们过日子。山南坡顶村的陈家,四代同堂,死得只剩几个老弱,被撵到村头的土地庙里,靠讨饭度日。村里的几个痞子瓜分了他们的屋子和丫头。还有他们的亲家,胡水荡的胡如匀家,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黛云,家里已经没有了其他活人。店铺和屋子自然也改作他姓,家中字画和书烧了好几天,烧完的黑灰也被一担担挑到地里肥田了。
参照了前村后垸、山前山后的诸户人家的经历,大家一致认定,如果被拉出去斗争,就不可能活着出来。即使活着出来了,比死去会更难受。
结束语是公公陆子樵说的:“活不成就死吧。好歹自己选择死,比被人打死斗死要强。”
这个决定一说出,女人们便哭出声来。绷了一天的气氛,倒因了这长长短短的哭声,显得松弛了许多。
已是落日时分了。冬天虽已过完,但春天却来得很慢。夕阳的光仿佛被早春的寒气给冻住,发射不出热量,于是,这天的夜晚就显得格外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