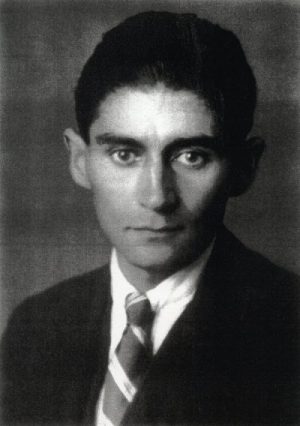普罗米修斯
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种传说。
根据第一种传说的说法,由于他将神出卖给人,因而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神还派出兀鹰,啄食他那时刻在长的肝脏。
根据第二种传说的说法,面对啄食的鹰嘴,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深地避入岩石,最后与它合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的说法,几千年过去后,他的背叛行为已被忘却,神忘了,兀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的说法,对这已是无根无由的事大家已经厌倦,神厌倦了,兀鹰厌倦了,伤口也精疲力尽地长合了。
依旧存在的是那无法解释的石山。传说总想解释这解释不清的事情。就因为传说是出自一种探究真相的动机,所以到头来它只能是解释不清。
(周新建 译)
城徽
修建巴别塔之初,一切还算井然有序。是的,这种井然有序大概太过分了,人们过多地考虑什么路标呀,译员呀,筑塔人的食宿呀,交通道路呀,仿佛眼前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甚至认为,建造的速度大概根本就不慢。人们大可不必十分夸张地表达这种看法,可能是他们特别畏惧打地基。人们是这样论证的:整个事业的精髓即修建一座通天塔的想法。除了这个想法,其它一切均属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将这座塔修到底的强烈愿望。不过由于有将来,人们不必在这方面担忧,而是相反。人类的知识日益高深,建筑技术已大大进步,而且将继续进步,过上一百年,一件现在得费时一年的事大概只要半年就能完成,而且质量更高,更经久耐用。既然如此为何今天要累死累活地使尽力气呢?只有可望在一代人手上建成此塔时,才值得这样尽力。然而这绝对没有希望。更易推想出来的是,知识完善的下一代将认为上一代干得不好,将把已建好的拆毁,以便重新开始。这种想法泄了大家的劲。比起建塔来,人们更热中于营造筑塔人的城市。每个同乡会都想占据最漂亮的营地,因此便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争执,直到升级为流血冲突。这些冲突再无平息之日。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成了一个新论据,因为他们认为,由于缺少必不可少的集中,此塔须造得十分缓慢,或者干脆等到缔结全面和约之后再造。不过人们并未将时间全都用于这些冲突,在间歇中他们也美化城市,但这又引出新的忌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以后数代也没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技巧更为熟练,随之也更加好斗。到了第二或第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愚蠢,但此时他们已经彼此紧紧联在一起,再也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在这座城市里,借助传说和民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渴望,对已有人预言的那一天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拳连击五下,它将被砸得粉碎。因此,这座城市在城徽上有了这只拳头。
(周新建 译)
集体
我们是五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先后走出一所房子,起先出来一个,站到大门一边,随后出来第二个,更确切地说,像水银球似的轻轻滑出大门,站在离第一个不远的地方,然后是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然后是第五个。最后我们站成了一排。人们注意到我们,指着我们说:“那五个人现在从房子里出来了。”自打我们生活在一起,若不是一个第六者常常插足,倒也是一种宁静和睦的生活。他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但却令我们讨厌,这也就够了。为什么他要往别人不喜欢他的地方钻呢?我们不认识他,也不想接纳他。从前我们五个彼此也不认识,只要愿意,我们现在也可能彼此还不认识。但在我们这里是可能的和可以容忍的,在第六个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和不可容忍的。另外我们是五个,我们不想是六个。总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五个也没有意义,可我们既然已经聚在了一起,就不想再分开,不过我们不想来一个新的组合,这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可是该如何将这一切告诉第六个,长长的解释几乎就意味着接纳进我们的圈子,我们宁愿不做任何解释,我们不接纳他。无论他将嘴唇撅得多高,我们都用胳膊肘将他撞开,但无论我们怎样将他撞开,他还是照来不误。
(周新建 译)
夜
夜幕低垂。就像有时低头沉思一样,夜幕紧紧地闭合起来。四周睡的都是人。一个小小的花招,一种毫无道理的自我欺骗:他们睡在屋子里,睡在牢固的床上,睡在坚实的屋顶下,或伸或蜷睡在床垫上,睡在床单上,睡在被窝里。实际上他们是聚在一个荒凉的地区,以前曾有一次,以后将还会这样,一个露天营地,一望无边的人群,一支大军,一个民族,头顶冰冷的天,脚踏冰冷的地,在站立的地方就地卧倒,额头枕在胳膊上,脸冲着地,静静地呼吸着。你醒着,你是哨兵之一,你从身旁的枯枝堆中抽出一根燃烧的木棍,晃动着它找到离你最近的人。你为什么醒着?必须要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回答。必须要有一个人。
(周新建 译)
陀螺
有个哲学家总是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遛达来遛达去。只要看到一个有陀螺的男孩,他便潜伏起来。还没等陀螺转起来,这位哲学家就盯住它准备抓住它。孩子们大叫大嚷,竭力不让他挨着他们的玩具,他可不理这些,只要陀螺还在转,他就抓住它,他十分高兴,但只是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他便将它扔到地上走掉了。他认为,认识每一件小东西,比如说认识了一个旋转的陀螺,就足以达到普遍的认识,所以他从不研究大问题,他觉得那样不经济。如果这最小的小玩意儿被真正认识了,那也就认识了一切,因此他只研究旋转的陀螺。只要有人准备转陀螺,他就有希望,就能成功,陀螺一转起来,他就觉得那希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他,变成了确信无疑,他却将那件无聊的木头玩意儿抓在手里,他觉得厌恶,孩子们的叫声他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听到,此时却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将他赶走了,他就像在一支笨拙的鞭子抽打下的陀螺跌跌撞撞地走了。
(周新建 译)
(选自《卡夫卡短篇小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