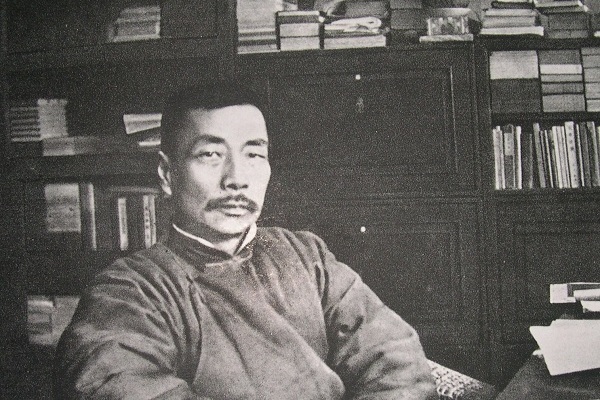最近,我在祝勇先生的一本关于文化人的随笔集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象鲁迅那样破坏易,象胡适那样建设,却难之又难”。从这句话中我体会到一种对中国屡屡遭受人为破坏之灾的悲愤之情,但同时也感到,祝勇先生对鲁迅的”破坏”是存有异议的。他的语气中似乎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在中国,今后最好还是多一点胡适那样的建设者,而少一些鲁迅式的破坏者(或破坏狂)。
看到祝勇先生上面这句明显带有愤慨之情的话,我开始想这样一些问题:鲁迅一生都破坏了一些什么?他的破坏和胡适的建设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观念传统习俗异常严重,恶势力保守势力始终处于上风和强势,专制统治又极端僵化和暴虐,任何一点革新思想和行为都会被当做异端加以剪除的社会,不铲除鲁迅想要”破”的那些东西,胡适想要”立”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能建设起来?而且,鲁迅真的就是一个破坏者吗?他在破的同时有没有建树?
的确,纵观鲁迅的一生,”破”似乎占了主要内容:破旧道德,破旧传统,破宗法观念,破封建礼教, 破一切他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但是做为一个文人,而非职业革命家、政治家,他的破也仅止于写写文章、发发议论而已,不过是用语言文字批一些他深恶痛绝的人,驳一些他认为谬误的言论,揭一些他感觉过于卑劣的谎言,撕一些他厌恶透顶了的假面……,在行为上,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打呀砸呀杀呀之类的“壮举”,因此我想,如果要说鲁迅是一个破坏者,那他也是一个精神文化领域的破坏者,时髦点说就是一个”软件”破坏者、一个”黑客”。
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下判断前,有必要对鲁迅的一生做全面考查和分析,看看他所做的”破坏”,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与别种类型的破坏、都有哪些区别?
我发现,鲁迅一生试图”破”的,基本上属于陈腐的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和对人的精神起桎梏和毒化作用的东西。他并非象一个破坏狂, 见了什么都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看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的人,应能明白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具体做法上,他也是极认真地用心加以甄别,立存废标准,并认为要慎选施行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鲁迅具有超乎寻常的清醒。在1930年,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守,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他并且十分强烈地谴责过他称之为”盗寇式的破坏”行径。从鲁迅大量的译著我们也能看出,他的破坏,是以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为出发点的,他之所以更注重”破”,是因为在他看来,不将一些旧的陈腐的邪恶的东西扫除,新的东西是无从生长的。
我记得十年浩劫结束后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一年的语文作文考题出得很有意味:先讲了一件事,大意是,十个人栽树,一个人毁树,栽树永远也没有毁树来的快,题目就叫”毁树容易栽树难”。这个题的寓意是相当深的。祝勇先生的感慨,我想也是源自类似这样的一些原因。中国的的确确、是被无休无止莫名其妙不负责任的人为破坏行为摧残得太厉害了、太不成样子了,鲁迅也曾经沉痛地说过,我们中国始终是处在“破坏了建设、建设了又破坏”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
可是在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破坏我们必须分清,这就是:毁树行为是一种破坏,对毁树行为进行喝止、声讨,对毁树的人进行揭露、鞭挞,对保护和迁就毁树人的体制施以攻击,也是一种”破坏”,鲁迅所谓的破坏恰恰是后一种,这后一种破坏和前一种破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祝勇先生是不是将这两种破坏弄混了,或者是对破坏行为恨之已极,以至于凡见到”破”便怒发冲冠,分辨不清性质不同的各类破坏之间的差别了?
无庸置疑的一点是,前一种破坏既轻松又畅快,在破的过程中没准还能捞到不少好处;后一种破坏既艰巨又辛苦,并时时都有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而在中国,历来多的是前一种破坏、缺的是后一种破坏。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鲁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前一种破坏行为的揭露和鞭挞上,他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们的国民性里面何以会有这样一股异常强烈的破坏欲,考查了产生这种无休无止的破坏行为的社会历史根源,并试图寻找到制止这一现象继续蔓延下去的办法。这显然是在破中寻立、破中求立,与一味地破,盗寇式的破、奴才式的破、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立的方面,鲁迅更是注重新观念的提倡和新思想的传播,鲁迅不但自己严谨著述,还大量译介了国外的优秀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及著作,为长期在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的中国人输送精神养料,他把此种行为称之为盗”天火”。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大学任职讲学,并办过数种刊物,为培养文学新人和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勤奋工作。鲁迅在自己的《三闲集》的末尾,曾将自己从二一年至三一年十年间的译著开列了一个目录,从那长长的所译、所著、所编、所选、所校订、所印行的篇目来看,他这十年的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谁又能说他这十年的工作都是破坏而不是建设?一个认真研究过鲁迅的人,从鲁迅的大量自著译著中,难道仅看到的是批判,而看不到继承?仅看到的是破坏,而看不到建设?
我没有看过鲁迅全集,仅就我看到过的他写下的那些文字,我认为在他的同时代的文化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鲁迅为最,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绝不单单是一个破坏者,在破的同时,他也在奋力建设。对于这一点,是有他的全部文字在那里永远作证的。我甚至这样想,中国要是没有鲁迅,整个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不知要苍白多少?
那么鲁迅的破坏,和胡适的建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以为,鲁迅的破是一种建设前的”清障”工作。但是由于文化是一种”软件”,因此在破的同时、包括未及彻底清除掉旧物的情况下,仍可以进行某些建设性工作,不必象物质世界一样,必须铲除了地面上的所有遗留物后,才可以施行新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破坏和胡适的建设是有同等价值和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鲁迅要扫除的,也即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影响发展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思想文化上的旧货和污秽,而是包括物质的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东西在内的有机体,正是这些有生命的旧东西,构成了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不扫除这些障碍,许多建设是无法可想无从实施的,即使勉强为之,也只能是沙上建塔,长久不了的。这恰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的过人之处。鲁迅对胡适的一些嘲讽,我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但是完全否定胡适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建树,显然是偏颇和不当的。做为一个文化人,只要是用良知和真诚在思考,他的劳动就应该被尊重。文化上的多重选择和争鸣,无论如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于”难”和”易”的问题。众所周知的是,植树难、毁树易;盖楼难、拆楼易;建设难、破坏易。但是如果我们要破的是一种千年陋习和制度呢?谁还会认为它容易?我们面对的要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利,这股势利根本容不得半点违拗,我们却必须抗拒它,这是难、还是易?今天我们知道,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时代;鲁迅所要进行的破坏,也绝不是随大众往自己家里搬几块雷峰塔的砖。他是要到法场去拆除那斩了无数人头的断头台,他是在试图着去砸碎那所有束缚奴隶身心的枷锁,他是在统治者为自己及其走狗安排好吃人的筵宴、准备在“长治久安”的美梦中宴饮的时候、吼出了“他们在吃人”的呐喊——对于这样的破坏,祝勇先生真的以为”容易”么?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已经表明,中国人为铲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付出了太多太大的牺牲;而鲁迅当年竭尽全力破除的东西、也并未真正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消除,有些反而变本加厉、以出人意外的、百倍千倍的凶残和疯狂在中国肆虐开来。胡适(包括一切善良的人们)想建立、确立的东西,也由于缺少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每每飘摇无着、如影子一般在人们面前晃那么一晃便烟消云散。这一切无不说明,”破”在中国是多么艰巨和不易;而没有彻底的破做先导,我们要么无从建设、要么建设起来的也是一些空中楼阁。
鲁迅在杂感《忽然想到(五)》中曾有一段与“破坏”与“建设”相关的论述: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很显然的,生存、温饱、发展是建设范畴的事,而古今人鬼《三坟》《五典》等阻碍发展前途者,则是要破除的对象。
就拿现实来说,我们从事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哪一步离开了清扫和破除?”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思想解放运动,难道不是在”破”?丢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风,难道不是在”破而后立”?我们实在可以这样说,没有大刀阔斧的对一些僵化陈腐的旧造陈习、束缚人手脚的典章陋规的破坏,就没有改革开放在今天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历史和现实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建设事业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破坏为其清障、开道,只会沦为理论家书斋中的空想和宣传家街头动听的口号。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破”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埋头搞建设的事了。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会遇上新的问题,都会给自己进一步的发展积累下新的矛盾和障碍。我们今天在建设中遇上的羁绊、前进中遇上的障碍,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危害要大得多、也严重得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仍然不仅仅是建设的重任,而且也包括为建设清障的工作。这后一种工作,现在看来越来越无法回避或绕过(有人曾经十分天真地这样想过)。更令人忧虑的是,所谓的”阻力”、”障碍”、”羁绊”等等,并不是一些死的、躺在那里仅仅等待我们去搬运和清扫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的、庞大得无法比拟的有机体。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些微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多少知道一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在中国有多么强大的势力和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我想一个人便不会再轻飘飘地说什么”破坏比建设容易”这样的大话了。
我之所以对祝勇先生的一句话发这样多的议论,是因为我们今天又走到了不破坏无以前进、不破坏无以继续顺利地进行建设的地步了。而且,直白地说,我们今天所要破的东西、远比鲁迅所要破的东西强大得多、也狡猾得多。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无数专家学者、志士仁人,不约而同地从心里发出了”改革会不会夭折”的忧虑和担心。建设者是可敬的,但是当建设者无法正常从事建设、而且他们的劳动成果多被无端剥夺和挥霍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首发2001年《鲁迅研究月刊》
附记:
1998年的时候,谢泳先生发表了一篇《鲁迅研究之谜》,该文提出一个看似深刻、重大,实则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看了谢泳先生的文章,我按捺不住写了一点与之商榷的文字,大致意思是:专制利用鲁迅,是因为鲁迅具有利用价值,就像江湖骗子穿上警察服装招摇撞骗,是因为警服可以迷惑人,给人信任感安全感。不能因为利用者一方选取了一个被利用对象,就认为被利用一方与利用者一方是一类货色了。谢泳先生收到我的商榷文字,即刻给了一个回复:你讲的是有理有据的。同时建议我把文章寄给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我就把自己的辨析文字作了进一步加工润色,投给了《鲁迅研究月刊》。很快,就收到月刊副主编王世家先生的回信,老先生用的是毛笔和旧时文人常用的红格笺写的回信,信纸铺开有8K大小,当时展读时很是激动。信的内容现在记不清了,大意是文章写的不错,拟在第几期发表云云。这样就与王世家先生认识了。后来与王先生有过多次通信。
在2001年写完《“破坏”与“建设”》初稿后,我就直接寄给了王世家先生。记得初稿的文字在2800字上下。王世家先生回信说拟用,但需要我把文字再压缩一下。我就铺展开稿纸对文章进行修改、压缩。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修改的过程是一个重新梳理和再思考的过程,等一切就绪誊抄完备,我清点字数,发现把原本2800字的文章“压缩”到了3500字。这可如何是好?考虑再三,我想,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言之不空泛不拖泥带水,长就长吧——寄。
结果,王世家老先生收到我的3500字“压缩稿”后,一字未删全文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