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9 湖南散文
“你从哪里来的?”
“我……大概是别的地方。”
“你从哪里来的?”
他的面目模糊,长着白瘢点的黑眼珠突然空翻,走到我身边时这么问道。他第二次陡然在“来”字上加重语气,我像是来历不明的人,无端地心惊肉跳起来。
我醒来时,才发现天色还在黑暗之中。我长久失眠,偶然撞入的梦乡,是一片荒野,一条灰头扑脸的公路,一间灰头扑脸的土屋,我孤独地站在土屋的前方,瞻望公路上的空阒。他不再问我的话,而是转身钻进黑洞般的屋里,再没有出来。在明艳的清新天空下,仿佛有叛军杀入,是沤溲的异味,从他身上和土屋里跑过来的。
很熟悉的场景,那必定是我去过的地方,我拼命地从大脑记忆库中搜寻。但它显然已经在时空上离我远去。沮丧连日来跟随这个梦,把我推向“土屋”摇摇欲坠的墙壁。当再一次被推向斑驳的土壁时,我依托惯性孩子气地撞上去,土砖瞬间坍裂,砸在地上,棵棵青草弯折匐地。我的心感到了剜了个缺缝般的疼,我想起来了,那是真实的疼。
十多年前,我去往家乡的东山镇看望一位农村诗人。当地的朋友在饭桌上说起被称作老包的他,说起他那些不可理喻的奇谈轶事,我们几个刚闹着酒的外来者就嚷嚷着要去看看。从松木桥左拐上的那条公路,直插进向山谷绵延的绿意泛滥的田野,就变得格外狭窄和破旧。公路羼杂着一段段的平坦和颠簸,酒精在我们的胃里加速燃烧。车轮下扑腾起灰尘和细石,掠过路旁的沟堑,把野地里的蚂蚱和麻雀惊飞。车就这么一路奔驰,像是开进一片无边无际的荒芜里。
叫老包的农村诗人并不知道我们何时到来,但我在朋友的提醒下,一眼就看到了坐落在那条公路旁的土屋前的他。我看到他从一个一动不动的小黑点,变成身材矮小的瘦弱男子,肤色蜡黄,皱纹折叠,衣领袖口浓墨重彩。我望了一眼同行的省城来的衣冠楚楚的胖诗人,皮肤白净,戴着眼镜,嘴角油光浮泛。老包就是一只逃离饥荒刚钻出地面的土鼹鼠。
有熟络的人跟老包打招呼,一一介绍跳下车的我们,他无动于衷,目光在陌生者的脸上跳动,表情跟土屋的颜色是一个调色板上的,板结,凝固。我们这群外来者,也不见外,自己张罗着自己,然后像掂量着这块地皮生意,绕着屋子转圈。胖诗人转了好几个圈,走姿像跳舞。老包突然撞向前,跟他说了几句话,胖诗人讪笑的声音越来越小,然后机巧地转身躲到我身边。老包跟过来,像根细木桩般杵到我面前,长着白瘢点的黑眼珠突然空翻,问道:“你从哪里来的?”我承认,那一刻,我是真的慌乱了,双手无措地折叠着刚从野地里拔起的一根狗尾巴草茎,回答:“我……大概是别的地方。”这样的答案当然是不会令人满意的。老包咄咄逼人地再次问:“你从哪里来的?”这时,当地的朋友把他连拖带抱地推进了土屋里。
再次走出来的瘦小的老包,腿有残疾的老包,把订阅多年已经纸页发黄的《诗刊》杂志、他写在一张张脏兮兮纸上的诗歌,从漆黑脏破的土屋里搬出来。这些纸页一见到阳光,页脚就瑟缩着发抖,页面上更加黯淡。它们喜欢跟老包在黑暗中密谋者般对话,太阳照着,它们已不习惯睁开眼睛。当地朋友说,老包常常困在家中不出来,跟纸和笔说话,跟一行行所谓的诗歌说话,却不跟登门的人说话,四周八围的人都认定他已经疯了。
土屋的门实在是矮,登门的人没有谁不是要把头低下才能进去。我们轮流进去参观,屋里很黑,也很逼仄,我眯缝着眼,等待视线适应后才看清,经年累月堆积的油烟和尘垢,多久不曾换洗的被褥衣物,散发出沤溲发臭的气味。老包无所谓不在乎的样子,让对气味敏感的我无法对在此般屋檐下生活的他怀有好感。胖诗人吐了吐舌头说,他也许不需要任何人的好感。我说,是啊,有诗歌和远方的人,都是自恋狂。
屋的西墙破了个洞,一张旧挂历纸糊着,风不时把印在上面的美女的衣裙吹起。一根照明线在头顶摇荡,屋外的人说,这电灯线只是摆设,老包没钱,怕缴电费,自己把线剪断了。怎么不干脆把和世界的联系一齐剪断,诗人是可以这么做的,我心里蹿起一个声音作答。
有人在一旁调侃,老包啊你这么脏,老包啊你这么穷。
又有人绕到他身旁,你背一首诗我喊你老包,背不出来你就是草包。
他像没听见,进进出出,照料着他的那些旧杂志破书籍“宝贝”,还有也许永远不会被发表、被朗诵的诗作。这个家徒四壁的人疯了,这个疯了人在写诗。他是疯了才写诗,也是写诗后变疯的。我突然觉得朋友的笑谈很滑稽。滑稽者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取笑那些沉默的滑稽者呢?
土屋前突然安静下来,沉默的老包让人觉得无趣。同行的人纷纷散开,滑去有段距离的村子,帮老包讨取些用物。老包像只刚刚熟悉环境的鼹鼠,身处安静之中,紧张感慢慢拂散。当地朋友拈出一页纸,指给我看老包因为孤寂写的一首《没有鸟的林子》。
“一座空山/我走进没有鸟的林子/树叶上 喧闹着阳光/时间是一座停下的钟/柴草满山 山在枯黄/木屋旁竖着两只耳朵/尾随在主人左右/砍倒的木料堆积着财富/对面坡上一只小兔/倒在猎人的枪口/我相信它们会玩一场死亡的游戏”
我说,写得很好,真是老包写的吗?不知何时站身旁看我读完的老包将那页纸抽回去夹进手稿中,砸点着脑袋,头发在空气中摩擦出窸窸的声响。朋友说,那些村民讲老包胡说八道,写的不是现实,哪里有没鸟的林子,哪里有没鸟的山?
我的目光挪向老包,不要和不懂诗的人计较。老包,你为什么要这么写?
老包斜我一眼,我写的就是我的现实。
老包的现实是什么?我想,他孤身独居,一个人上山去砍柴,感觉那是一座空山。即使那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树叶托着流动的阳光,光沉甸甸地落在树叶上,但山里还是很寂寞的。
一个中年村民脖红耳赤地挑着担水,放进了土屋的黑暗处,然后拍打起阳光下的尘灰。他是村里唯一把老包认作诗人的人,也只有他会闲下来就串串老包的门。他说,大家笑他是过得太空虚,想找个老伴一起上山砍柴。人家的调侃,老包当没听见。别人的闲言,像风把落叶扫拢那样传到老包的耳朵里。他从不去当面反驳,却会跟来串门的村民针尖对麦芒般地掰那些错话。
没有人说错话,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又穷又老的疯诗人。
老包从来没在众人面前絮叨他的陈年旧事。他的过去,从认识他的人、与他交谈过的人的嘴里传来传去,就像一条条小溪流,从山谷里蜿蜒流出,编织出一块发光的水面,而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拍击起水面的浪花。三十年前,老包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但怕穷的老婆突然就带着一双儿女远离僻壤,再也没有回来。这场失败的婚姻,缘起和毁灭都是他的不可治愈的腿病。更早之前,他生了场怪病,辍学归家,四处求治,几年下来好不容易找了个山里的中医治好了,还被人点拨去上门学了裁缝,手脚灵巧头脑聪慧的他很快获得师傅的垂爱,让他做了上门女婿。几年后病情复发,且越治越糟越治越穷。这是一个乡村诗人的前半生。独身的他突然在某一天开始从脑子里蹦出一些句子,他认为那是诗,他的乡亲们却是当作荒谬的笑话。开始写诗的老包,把好心人给的米和油卖到乡村小餐馆里,把儿子偷偷寄回来的钱,都拿去买了纸和笔、邮票和远方。他梦想着诗歌发表诗集出版,乡亲们茶余饭后在心里嘲笑,这是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荒谬梦想。
荒谬把老包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某个编辑发现他,而是一个路过的当地记者把老包的“荒谬”从土屋搬到了太阳底下。老包的荒谬生活引来门庭车马,这些车马离去之后,老包像水面浪纹一圈圈地往外漾开:
“前不久,我决定绕道东山镇去看那间熟悉的土屋,只见门敞开着,大门外喊了几声,谁知诗人脆弱的声音送不出房门。跨进里屋,终于见到活着的他。还是那张又瘦又黄的脸庞和一头乱糟糟的灰白发,也许身上的破棉袄早已挡不住袭人的寒风,扶在椅子上的手在明显地颤抖。环视土屋,紧靠床边的后墙还是3年前连牛也能钻进来的大窟窿,伸手抄进米缸,米粒少得能够数出来。”
“60多的老人,身边一直没有亲人,身子又因风湿几乎瘫了一条腿,手也不方便,没人保证衣食。且身无分文,患了病怎么着……”
“嗜诗如命的诗人还能在诗国的疆界跋涉么,我在布满蛛网的土屋中搜索着,显然,诗人没有因病、因穷停止吟唱,一本《诗刊》合订本底下又发现了他的《增补“土屋手记”》手稿,是用一个作废的备课本装订的。”
那天老包一瘸一瘸地走来走去,他的小腿肌肉萎缩缠身多年,这个疾病让他几乎失去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学业、家庭、亲情,却在陷入困顿中爱上诗歌。除了老包,谁会选择这样的爱。挑水的村民讲起一则旧闻,有人残忍地笑了,我却似乎听到老包的血管爆裂的声音。一天,老包走到东山镇的街市上,迎面一个女人指着他对别人说:“这个人还在!”
他们,是不是都早以为他死了,或者是这样一个荒谬的人应该死了。我无从猜度老包当时的心情,但他用文字记录了:我是活着,但谁曾有过一番评述我活着的内情呢?算了,就让诗来为我发言吧!他这样在粗糙的纸的洁白处写下一首《我死了,但我还活着》:
“我吃的饭没有/盐呢?/油呢?/还有烧柴!/也就是没有一个“饱”字/只有“饥”//我穿的衣没有/被呢?/鞋呢?/还有袜子啊!/也就是没有一个“温”字/只有“寒” // “温”“饱”二字/是作为人最起码的要素/而我没有具备/这么说我已经死了/但我还活着/啊,死了的原来是我的肉体/我诗的生命还活着/我看见人们正在搬运我的尸骨/在我六十个春天还没到来的时候/就为我挖掘好了坟墓。”
荒谬的老包只是感到他无可挽回的无辜。
前不久在北京搭乘13号线地铁,我和一位编辑朋友聊到老包,他说见过很多像老包这样的人,有着文学禀赋或热情却无法正常写作与生活的人。他告诉我,有位叫迈克尔·费茨杰拉德的教授曾把一小类人群划归为艾斯伯格症候群,这个群体里的人拥有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超的数学天赋。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等音乐家、作家和哲学家都属于艾斯伯格症候群,而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工程学天才也被认为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费茨杰拉德说,导致这种病症的某些遗传因子同样也是他们非凡的创造性才智的来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是一步之遥。那老包是疯子,还是天才?当时地铁途经回龙观站,朋友说出站不远的回龙观医院就是北京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我苦笑一声,地铁再次疾驶刮起的风,把我的笑吹到黑暗的隧道里,被下一趟地铁碾成碎屑。
我从那个既怪异又真实的梦中醒来,回忆起了我去看老包的那年,有人说他刚过六十四岁生日。大家都向他表示了生日的祝福。他说,你们都记错了,他没有生日。这一晃又过了十几个春秋了。
我拨开家乡朋友的微信,问:“写诗的老包,还在吗?”朋友隔了很久才回答:“死了好些年了。”他又帮我问了几个人,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老包到底是怎样死的、死去的具体日期。我们都把写诗的老包忘记了,也许那些去看过他的人,一转身离开就被他忘记。我费力从成堆的旧书中翻捡出那本地方文学内刊,是做的一期老包诗歌专辑,遴选了他自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写下的120首诗。我翻开其中一页,写的是老包家住在大山脚下一个叫探弯子的地方,村庄隐身在两座矮山背后,只住户姓包的人家。老包这样讲述他的来处:
“春风一吹,弯子里满是李花、梨花、桃花/花中掩映着一座青砖瓦屋/还春雪一样藏在我的记忆里//目寻探弯子,就在我的前面不远/想走进探弯子里,/可一生啊,要走过多少坎坷 方能抵达/再想那儿时的旧梦/时光的迷雾啊重重叠叠/想走近那山坡的小路上/可我又更加靠近了黑暗。”
那是种怎样的黑暗,让老包更加靠近。他看见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燃烧的又是冰冷的,透明的又是遮蔽的,一切是可能的又是无能的。他在那个世界里独自生活,从中掘取赖以存活的力量,以此去拿到一个毫无慰藉的人执着生活的证明。我还在后来诸多夜晚接踵而来的失眠中纠结扭打,他是否还难以释怀他离开的这个世界,是他曾用他的全部意识和对无拘无束生活的要求来对抗的世界,抑或只是通向日常生活的一条道路。他,他们;我,我们,都要从这条道路上走过。
“你从哪里来的?”我看着镜子里的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欠老包一个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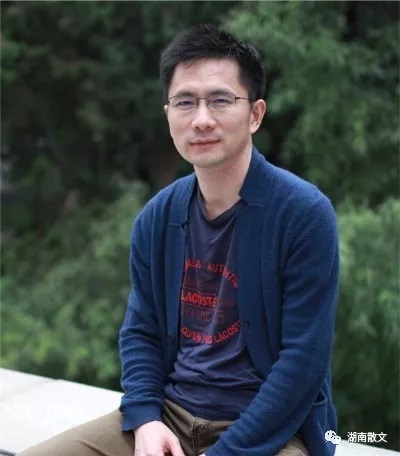
沈念,1979年出生,湖南岳阳人,文创一级,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在《十月》《大家》《钟山》《山花》《天涯》《芙蓉》《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入选多种文集选刊;出版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出离心》,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