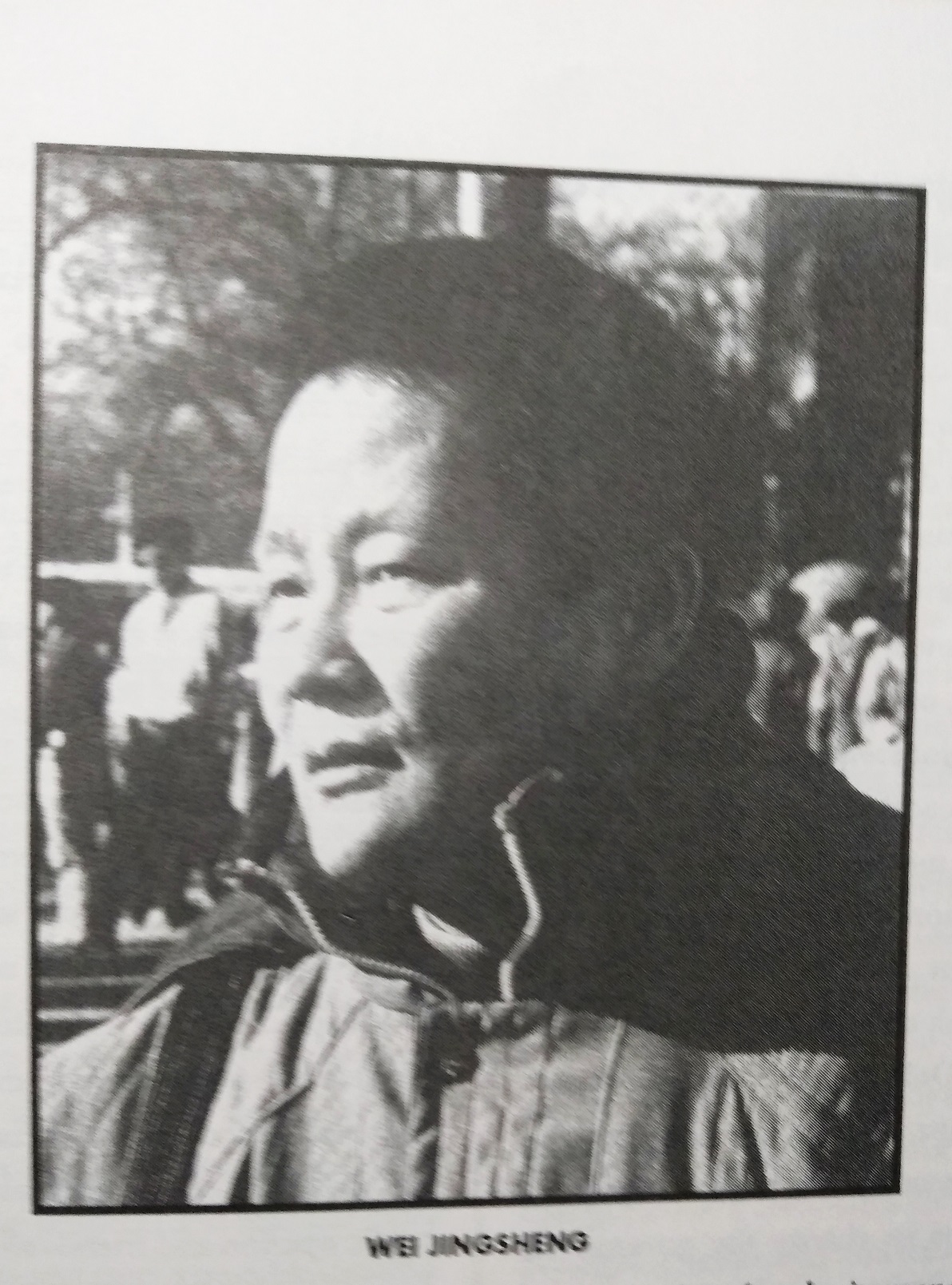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1979年7月17日,审判闹剧轮到傅月华了。同魏京生一样,对她的指控也是两条罪状:一条是刑事上的,说她6年前捏造强奸罪名诬告她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另一条是政治上的,指控她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扰乱公共秩序。但是这次审判真成了闹剧,中途坍台了。先是在听众中有一位高级干部,他认出原告的一个证人是他在几年前曾经打过交道的人。他站起来斥责那个人是“小流氓”。而后,另一位旁听者是一位地方上的司法工作人员,竟然指责审判员带有偏见。傅月华的辩护很有说服力,获得了听众的喝彩。在这些喝彩者中,甚至有一位是经过挑选的政治上可靠的人。结果,在傅月华描述了党支书身上隐私处一种特别的标记以证明自己的控告属实之后,审判只好中途停止。
这期间,国际大赦组织向中国政府发来一封抗议电报。美国国务院把对魏京生的审判说成是“出人意外的和令人失望的”。但是,邓小平在10月18日的一次会见外宾中,仍然坚持说魏京生和傅月华是骗子,是工人中的败类,破坏了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国并没有因惩罚他们就侵犯了人权,因为“如果给予他们自由,那就意味剥夺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自由”。
可以不客气地说,邓小平上面的讲话完全是信口开河,没有依据。魏、傅二人发表的言论并没有诲淫诲盗、暴力煽动的内容,怎么成了犯罪呢?至于游行示威更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正常现象,怎么在中国就成了破坏秩序的大逆不道之举呢?至于“如果给予他们自由,那就意味剥夺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自由”,更是无稽之谈!有谁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客观公正的调查吗?就是官方也不敢!否则是自找没趣,自找难堪。
推迟对傅月华的审判最终证明是没有用的,因为出于政治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理由,裁决是事先就决定了的。当12月恢复审判时,法官说傅月华“道德败坏”,犯有诬告罪,不过,由于某种他并未解释的原因,对起诉中的这一问题“将不再追究”。这次她被指控犯有盗窃罪,虽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但是她仍然因为这一罪状和扰乱社会秩序而被判处两年徒刑。
在这些审判进行的同时,官方报刊上刊登了一系列的评论和警告性的文章。整个基调是在魏京生定罪判决之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定下的: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人企图为魏京生之类的反革命罪犯进行辩护,甚至把他称为“人权先驱”和“民主战士”。其中有些人可能是上当受骗,不了解魏京生的真实面目。但还有极少数人的人,他们怀着同魏京生一样的目的,企图用同样的罪恶手段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奉劝这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你们应该抛弃你们的幻想。“
官方媒体立即随声附和:《北京日报》警告“一切反革命分子”,“不管你们的旗号何等‘时髦’,不管你们的手段何等狡猾,最终你们将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中国青年报》则指出:“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如果你们不转变思想、悔过自新,你们将身败名裂。难道魏京生的教训还不值得引起注意吗?”《光明日报》甚至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议论那种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或者侵犯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解放’。”
这些论调的意思就是让人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牢狱侍候。但是就在三个多月前的6月20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草案时,《人民日报》就“反革命罪”发表意见:“即使有明显的反动思想,那仅仅是思想问题,不能构成犯罪。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应当有思想犯。”
言论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如果不用言论表达出来,何以成为思想?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全都赖以具体言论的表述。例如,毛泽东思想具体地说,就是他的许多言论的汇总。既然说了“言者无罪”,“不应当有思想犯”,现在却明目张胆地以言治罪,言而无信,天日昭昭!凭什么以血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和平表达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魏京生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
但是,无论是对魏京生的审判,还是官方媒体的警告,都没有使“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就范。与三月的那次打击不一样,当时只是引起了小规模的反抗,这次审判却引起了大声的抗议。在给魏京生定罪的那一天,民主墙上有一份大字报指责领导集团“践踏宪法”。另一份大字报问道:“如果人们把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构成犯罪行为了吗?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人们怎么知道什么话才不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呢?”10月21日,《四五论坛》采取了一个公开的大胆行为,把审判魏京生的记录的一部分张贴在民主墙上一一那是从法庭上偷偷带出来的。旁边还贴出一份大字报,题目是《不公正的判决》。这天,一些人在民主墙前面举行了集会,魏京生的一个支持者发表了演说。他把他的姓名、住址交给了人群中的便衣警察,说:“假如我被通缉了,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去哪儿找我。”
青年积极分子的这种勇气并不是当局面临的唯一问题,更为棘手而意想不到的问题是来自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的抗争。
1979年10月,那些在“北京之春”运动开始时几乎沉默不语的知识分子,此时却站了出来,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在审判后的一星期,《光明日报》的一篇头条文章居然是用魏京生的那句名言来开头的:“没有政治民主化,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文章还宣称:“我们必须进行独立的理论探索”一一复制了其有魏京生所办的民刊《探索》为特征的术语。这份报纸的另一份评论用的竖行标题是:“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文章说: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书生”。他们随时有可能……被关进监狱,哪里谈得上“专”别人的“政”?然而他们以真理的呐喊划破了夜空,震撼了大地。……如果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真理的传播也不靠暴力,那么,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反而用暴力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看来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并不完全同意魏京生的观点,但是他们对以专政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感到不满并为之恼怒。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告诫,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受到了公开的批评。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指出:“某些人有一种偏见,一提‘自由’,就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把自由都奉送给资产阶级呢?”这篇文章还明确指出:不能够以制造反革命言论为理由来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思想”。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竟然对魏京生的审判刊登出如此直接的批评文章,这显示了上层意见分歧的激烈程度。
但是,提出最强烈挑战的是作家。
10月30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他答应停止从外部干预文艺,但是他也极力说服代表们反对“左和右”两个“错误倾向”,同时提醒他们必须严肃地衡量他们作品的“社会效果”。在随后的大会发言中,诗人白桦表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极不寻常的态度。他称赞了青年作家的勇气和独立思考,不过他发言的主要内容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大胆批评,这比以往他所发表的任何作品都走得更远。白桦在发言中激动地说:
我们应该掩饰谁也无法掩饰的社会矛盾吗?我们应该去歌颂使我们付出重大民族牺牲的愚昧状态吗?我们应该对已经绊住了我们手脚的官僚主义保持沉默吗?我们应该去照顾与共产党毫无共同之点的“一言堂”的威望吗?人民群众不许可!……
很多好心的同志和读者经常来信提醒我:“你很不安全!”我很感谢这些同志的关心。同志们这样想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前些年生活中说谎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虚伪者安全,诚恳者危险。我常听一些有儿女的同志们忧心忡忡地说:“我的儿子将来准坐牢,因为他不会说谎。”也有些同志乐滋滋地说:“我的儿子准有出息,因为他是个小两面派!”多么可悲!……
(三中全会以来,)因言而获罪者渐渐少了,但不是说已经完全解除警报了。……但是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不敢说真话,父子、兄弟、姐妹、朋友之间不能知心,作家不敢记笔记,公民不敢记日记,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呢?
现在仍然不能说文艺家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时候了,不是还有人着文、投书、讲话,要把某人关起来,给某人重新戴上帽子吗。
我呼吁民主!……我呼吁团结!……我呼吁给作家、艺术家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我呼吁关心青年作家的培养!……我呼吁保护、支持和奖励勤奋的劳动者!最后我呼吁:拿出勇气来吧!没有勇气就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不仅白桦有勇气说出这一切,而且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也有勇气把它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除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外,这是唯一受到这种对待的大会发言。
但是,外国媒体已经注意到,甚至在文代会召开之前,“收”的信号就已经显示了。邓小平的目的就是想恢复党的纪律和权威。毫无疑问,从一开始他就准备着承受一切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对青年积极分子的挑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必须打压下去。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关闭西单民主墙。这个决定在11月初就准备采取的。在审判魏京生期间,邓小平对民主墙有了另外的认识,他告诉外国客人“它不能体现我们人民的真实感情”。六个星期以后,他又说尽管有一些人贴大字报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让民主墙维持了这么久的时间。”
对这个决定的公开暗示第一次出现在11月3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里。它说有什么意见应该“在会议上或通过其他正常渠道提出”,因为问题不可能通过贴在街上的大字报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它又说,“事实已经证明”,大字报“容易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在生产、工作和社会上制造混乱。”
还有火上浇油的喧嚷。11月9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危言耸听地报道:
本市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蛊惑人心,煽动闹事,窃取刺探情报,向敌特机关挂钩,策划建立反革命组织……还有一些流氓分子在公共场合聚众斗殴,寻衅闹事……(我们对这些人)就是要严厉打击,毫不留情,就是要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杀,绝不能心慈手软。
这些虽然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套话,但比起三月份的论调,有一点重大的增加,即“该杀的杀”。公安部门受到敦促,要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11月18日的《北京日报》说,魏京生“杀气腾腾地妄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把他描述成一个从不干好事的为非作歹的贼人。在傅月华被判决之后,新华社搞了一个有关她男女关系的报道,内容十分下流,以致《人民日报》不愿刊登。
对请愿告状者的腔调也变了。9月份的时候,一些官员曾因为没有解决上访者的问题受到指责。现在,上访请愿者却被告知:“即使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也不要闹事。”12月初,被说成是“闹事者”和“害群之马”的那些人在许多城市纷纷被捕。12月中旬左右,在北京的上访请愿者全部被遣送回各地。
这年冬天,“北京之春”在西单民主墙演完了这场戏的最后几幕。
11月11日,星期日下午,一些警察来到西单民主墙,他们逮捕了三名正在推销魏京生审判记录油印本的青年,把他们推进一辆等在路边的吉普车里。在下一个周末,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一次。虽然这些被拘留的人大多数很快被释放,但是,《四五论坛》的一位编辑却被送进劳教所,理由是他公布了那个被官方称为“公审”的审判记录。
11月21日,《北京之春》公然对抗官方禁止出版非正式刊物的指示,它再次出版,向高层领导作最后的呼吁,以期改变他们的态度。呼吁中说,许多人都在注视着,要看到民主墙会有什么结局。镇压会马上奏效,但以后长期的后果又会如何呢?
一个星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广州市政府处理民主墙问题。北京市政府站在它的立场上,说民主墙“只起坏作而没有好的作用,挑起群众好斗的心理,引起交通堵塞……并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向外国人传递情报的重要接触场所”。同外国人有联系现在似乎成为一条罪状。官方有人声称,“外国人已干预此事”,于是要求严肃处理那些“与外国人相勾结,向外国人要钱、要材料以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人”。在全国范围内,煽起了一种对“敌特和奸细”的仇恨和恐惧。还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声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支持民主运动。
12月7日午夜,西单民主墙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下关闭了。取代它的是设在月坛公园的一堵墙,这堵墙以后被大家看作是“官僚主义墙”一一写大字报的人必须登记姓名和通讯地址。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其中有两个警告,第一个是对知识分子的:
我们对所谓“民主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基本倾向和其目的决不能抱天真的想法……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联系……我们必须告诉支持他们活动的共产党员,你们的立场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你们不立即彻底改正错误,你们将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有些人可能说,这又是一次“收”吗?我们从来就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放”过……坦率地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严而不是宽。
(这下人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党员干部犯贪腐错误多而犯政治错误少的原因了吧。因为这些党员干部都信奉“唯物主义”,在物质方面大捞特捞,有谁会犯什么没有实惠的政治错误呢。而且犯贪腐错误有可能漏网或轻罚轻判,犯政治错误则肯定会被严惩不贷。)
第二个警告是针对作家的。邓小平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作家是主要的受害者。在当时,向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发起进攻是必要的,它唯一的错误是扩大化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镇压已经纠正了,但是镇压的手段有可能再次使用。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说,“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从来就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应该从宪法条文中删去。
1980年1月以后,没有一本非官方的杂志还能公开出版。只有少数民刊,如《今天》和广东的《人民之路》还坚持到了夏天。但方,官方一直不允许它们获得合法地位。当新的出版法在7月颁布时,它们也被关闭了。8月底,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四大”如邓小平所愿被从宪法中勾销。大字报的时代结束了,“北京之春”也随之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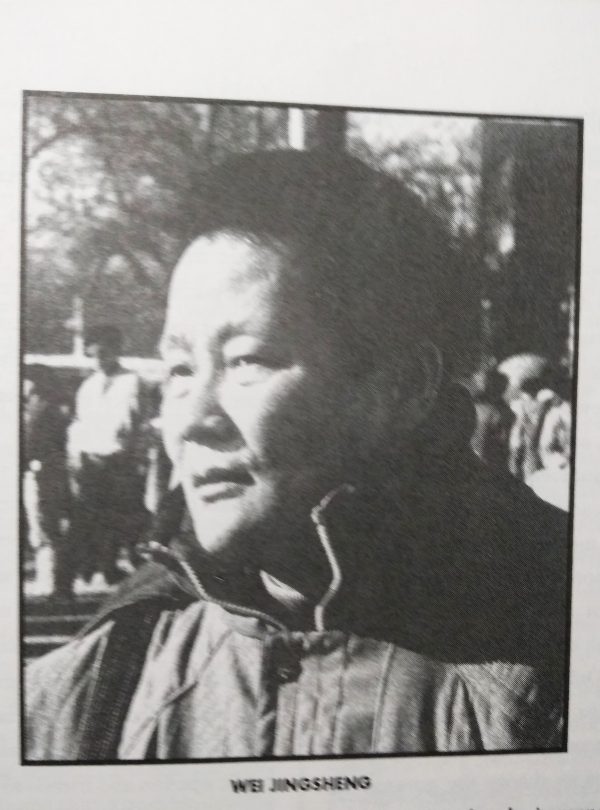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201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