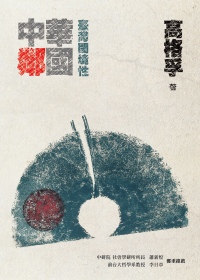古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海峡两岸的政、经、学各界人士,正因为身在局中、缺乏距离感,对两岸问题的看法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相比之下,反倒是冷静的旁观者看得真切、评得到位,比如《中华邻国》一书的作者、法国学者高格孚。高格孚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台湾认同政治、台湾史以及两岸地缘政治,以“历史性比较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在仔细比较十七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海峡两岸的状况之后,得出如下之结论:“(今天中国的)怀柔政策很像清廷与施琅一直到攻击台湾前夕所进行的政策。”
三百多年前,满清王朝的实力在康熙一朝臻于顶峰,其扩张能力在东亚大陆所向无敌;统治台湾的郑氏政权则因内部分裂而陷入风雨飘摇。最终,郑氏第三代统治者郑克爽投降清朝,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而今,中共以驱使数亿奴隶劳工的代价,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坐二望一;而台湾受全球经济危机和岛内产业外移的影响,经济不振,民众忧心忡忡,民主国家公民的自信心随之滑落。在此困境之下,台湾该以何种方式应对彼岸咄咄逼人的压力?高格孚在书中对执政的国民党发出一系列追问:台湾怎么可以面对中国崛起或复兴的事实?国民党怎么样可以结合保护台湾主权以及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带给台湾各行各业的机会?另一有关的问题是:国民党怎么面对台湾政体的民主准则?
是卑躬屈膝,还是前行引导?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施琅率军在澎湖列岛大败郑氏舰队后,给台湾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是,郑克爽向施琅派出和谈代表,表示愿意投降,但希望“三不伤”,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在得到施琅的允诺后,郑克爽正式向清廷呈送降表,表示以往的对抗是“稚鲁无知”,愿意顺从天意,“颜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后诚”。在表章中,郑克爽只提出请求允许继续居住在福建的条件,因为福建是其家乡——然而,清廷在受降后拒绝了这一要求。郑克爽降清后,与家人被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条胡同里,这里正是当年清廷软禁其曾祖父郑芝龙的地方。郑克爽年仅三十七岁便在软禁中郁郁而终,比其父亲郑经和祖父郑成功还要短寿。
物换星移,二零零八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发生重大逆转。马政府将中国当作拯救台湾经济的救星,对中共节节退让:陆客自由行实现,陆客蜂拥而入,让台湾业界难以承受重荷;陈云林等中共高官访台,台湾当局殷勤备至,戒备森严,宛如接待上国使节,警察不惜使用暴力打压抗议者;已经大陆化的旺旺集团以大手笔并购诸多岛内媒体,台湾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拒谈“六四”问题,并声称这是维护台湾的利益……那么,这样一个无比尖锐的问题便油然而生:马英九会不会成为当代郑克爽呢?
高格孚以郑克爽当年的降表为解读对象,饶有趣味地分析读者和作者“心有灵犀”共鸣,这也恰恰正是如今两岸会谈时双方内心活动的写照——“双方皆假装此突然的转变是基于共有的信念:不仅是台湾海峡两岸的权力失衡;不仅是对个人的根之难以名状的渴求,无论那有多么理想化;也是了解到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已非昨日的共产党,如今它作为永恒的中国的明确的领导者,正引导着一个迈向全球强权的国家的命运。”这样,强者一方不吝给出丰厚的奖赏,而弱者一方得以保存几分颜面,尽管“各怀鬼胎”,却也“皆大欢喜”。
但是,在高格孚看来,这不是台湾的正确选择。在政治上,台湾已经实现了总统直选、完成了第二轮政党轮替、拥有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人权也有了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台湾高度的国际化程度和位于太平洋与亚洲大陆交接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枢纽地位。因而,台湾不必向中国卑躬屈膝,反而可以充当中国的前行先导。
台湾是“后国家”时代身份认同的“实验室”
主权问题是两岸对谈中一个无解的死结。由于主权被神圣化,使得两岸的政府和民众都难以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药中自拔。其实,国家主权真有那么重要吗?对于中国和台湾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二十世纪才逐渐被建构出来的。
此前,清廷在甲午战败之后,未经台湾民众的授权和公决,就悍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的士绅和民众奋起抗争,不是忠于清廷,而是打出“台湾民主国”的旗号——虽然这个“台湾民主国”迅速被日本军队所扑灭,却堪称是亚洲第一个以民主为号的国家,比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整整早了十七年。
再次之,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太后下诏“对万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南方各省却实行“东南互保”的政策。可见,南方的督抚们并不认为国家主权是最高价值,而认为保护治下民众的生命财产是首要职责。这种观念,不见得就比举国玉碎的爱国主义要“落后”和“低级”。
在欧美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国家主义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一种普世信仰,国家也确实成为“符合人类基本群体认同需求的重要工具”。但是,国家的定义与地位,并非定于一尊、凝固不动,它必然随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迈进“后国家时代”。作为法国人和欧洲人的高格孚,对欧盟的成立与扩展,以及各成员国将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这一超国家的区域共同体,自然有切身之体验。所以,他指出:“在后国家的世界里,由于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将小于或大于国家的实体或群体视为潜在的认同选项,挑战着国家作为当代认同核心出处的优越位置。”换言之,至少国家不再是惟一的、共同体成员必须皈依的“最高价值”。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台湾国家地位的不确定性和主权的暧昧性,过去也许是劣势和弱势,如今则成为优势和强势。台湾学者吴介民指出:“台湾是一个‘主权受挑战的民主国家’,这里的‘受挑战’指的是台湾在国际列强夹缝中的处境;这是外部的意义。但是,对内而言,台湾的国家主权是没有争议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中华民国或其它称谓,它的统治权都是自主而完整的。”内外之张力让台湾更具活力。而高格孚则如此分析台湾的特点:“它倾向于自前国家阶段(即在其近代历史后殖民阶段,一个‘台湾国’从未正式出现),直接转移至后国家阶段(台湾极度全球化,主权政体甚至是国家地位并未被承认,但却完全独立于任何其他国家),而没有经历国家阶段。”所以,台湾的经验突出显示,假若国家仍是必要的,那么对国家的认同是可以灵活与易变的。
如是,台湾的特殊性也带来了它的珍贵性和先驱性,它或许为人类的群体认同带来新的启发和触动,正如高格孚指出的那样:“由于台湾的多元文化、历史经验与对世界的关系,台湾也成为认同的实验室:在文化、国家认同、市民身份、地方认同或学习如何作一个世界公民等方面,台湾均探索了很多新认同的可能方向。”
两岸关系需要“新思维”
两岸关系不能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下去。马政府以来获得的缓和局面,其实只是沙滩上的城堡而已。高格孚点出了“房间里的大象”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技术上还处于内战的状态。一九九一年,李登辉总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等于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权;也是从台湾法律的角度终止内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没这么做,而且还在二零零五年通过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所以,虽然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在表面上舒缓了,但从中国在军事方面并没有撤除导弹以及其他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在外交方面也没有停止对台湾之施压。除非两国或两府签署和平和约,或北京废除《反分裂国家法》与放弃使用武力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两国之间还是会在技术上处于一个内战状态。
这种状况,不是靠台湾单方面的善意或“非武化”就可以改变。但是,台湾却可以诚实而自信地对彼岸实行“启蒙教育”。近年来,诸多大陆游客和大陆学生包括韩寒等名人在台湾的观感,说明台湾完全有资格向中国输出“软实力”。对此,高格孚语重心长地对中国的统治者说:“一个独立的台湾不一定会对中国造成威胁。与其继续延续康熙时期以来的作为,试图紧密控制台湾的政治以及影响其对于国家认同的辩论,中国不妨尝试该改变其想法,将台湾视为一个可以帮助其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多元文化盟友国,同时设法藉着在国外扩展华人文化来改变全球化世界里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观。”这就是处理两岸关系时亟需的“新思维”之一。
不过,高格孚也认识到:“中国政府目前最不支持的模型是联邦国家,尽管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不追求一个由中国与几个邻近的华人国家共同组成的国协。”毫无疑问,“这两个想法在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里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也正是中国当局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关在监狱中,并对倡导联邦制的《零八宪章》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即便如此,高格孚已然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群体的身上发现“一些勇敢且高瞻远瞩的中国有识之士们早已拥有类似的想法”。真理固然会让先知承受苦难,但真理之光终将穿透黑暗的大地。
在高格孚眼中,台湾并不是官员或罪犯的流放之地,而是一个会产生价值观的地区。他指出:“台湾的多元文化母体的重要部分的确来自于中华文化,同时中华文化并不是其文化的惟一来源。在台湾保存中华文化的同时,台湾政府与社会各界,包括民间团体、企业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等参与者,不但会另外发明中华文化的新想法与概念,也会开拓新文化的方向,更会在缺乏国际承认的情况下仍旧探索如何成为全球公民。”倘若是,马英九不必步郑克爽之后尘,台湾民众也不会充当中国的二等公民。有一天,“全球公民”就将是台湾人头上荣耀的冠冕。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