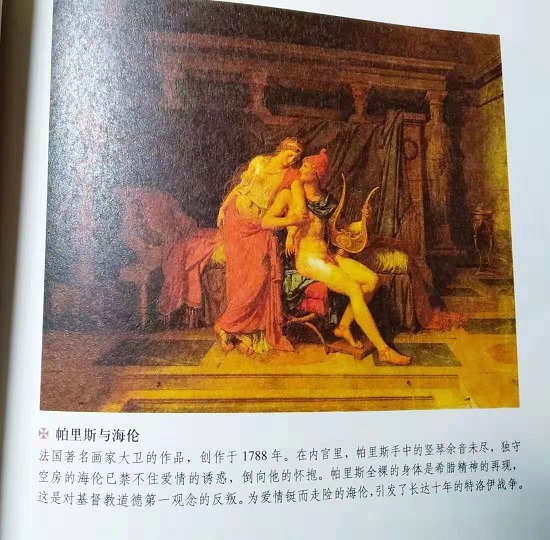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列举许多事例,宣扬宽容精神。他在“向书籍开战”一节中,以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自居,向那些禁锢思想自由的势力开战。他首先拿来开刀的是沙俄帝国和后继者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他这样写道:
就说俄国的问题吧。大约20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外国报纸有整个四分之一的版面被称为″鱼子酱“的黑东西涂抹了,据说是为了擦去那些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看到的内容。
这种监督被整个世界看作是“黑暗时代”的残余物,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然后就是俄国革命时期。
俄国的革命者在过去的75年里大声疾呼,说自己是受贫穷、遭迫害的生灵,没有一点“自由”可言。他们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被严格检查来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可是到了1918年,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又有什么变化呢?这些高呼热爱自由的胜利者,废除书报检查制了吗?绝对没有。他们查封了对现在的新主人的行为不进行正面报道的所有的报纸和杂志,许多不幸的编辑被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选择)。总的来说,沙皇那些遭人唾弃的被称为″白衣小教父“的大臣和警察都比他们宽容一百倍。
房龙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列宁刚刚去世,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不宽容已为西方文明世界所垢病。房龙想必对此有所知晓,上面的文字就是他对这些红色革命者出尔反尔的鞭挞。
宽容应该是一项永恒的原则,而不应该是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人类历史上不乏一些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处于劣势、少数派的时候,以受害者的身份鼓吹宽容,从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一旦这种虚情假意得逞,便嘴脸一变,就视与其相左的思想是异端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事例。房龙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宗教不宽容的现象,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类似不宽容现象虽然着墨不多,但让人们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感受。时至今日,人们从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看到,一些所谓的革命党是怎样从争取民主的政党沦落为反民主的政党:“当其未得势时,痛心疾首于他人之妨害其应享之自由,必须奋力反抗;一旦反抗得势,又忘却当日自家感觉的痛苦,而一样施之于别人,施之于政治”。
如今,中世纪宗教的不宽容已成为历史,而革命的、政治的不宽容还在世界一些地方大行其道。所以,房龙在九十多年前的教诲对我们现在认识宽容精神大有裨益:
我有幸成长在一个比较开明的社会环境里,这个社会真心相信弥尔顿的名言:“遵循自己的良心来认识、发言、辩论的自由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我决心坚持下去,尽量记住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阐明、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他不影响别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不违反当地警察局的条例就可以了。
当然,这让我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查制度的敌人,已被记录在案。在我看来,警方应该追查的是那些利用色情来谋私利的报纸和杂志,而其它的,谁想发表什么就由他去发表好了。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浪费精力。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我也很熟悉,从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制从未有一点好处。
废话就像炸药一样,只有放在密封的狭小容器里,加上外力猛烈的打击,才会发生危险。如果任由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半吊子的经济观顶多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而他的苦心只会成为众人的笑柄。
同样是这个人,如果被不识字而又粗暴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拖进监狱,再判处35年单独囚禁,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死后还会被尊为烈士。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了解;如不然,他们说的就会被很快忘记。……
言论自由作为个人权利,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作为天赋人权,它并不需要谁审查你的言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它只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依据,那就是,只因为你是一个人,有头脑,能思维,因而应该享有言论自由。绝不能认为只有口含天宪金口玉言或真理在胸哲言睿语才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也绝不能以言论正确与否为尺度来制定意识形态领域的紧身衣。
也许有人对此会不以为然:既然你认为受压制的思想也可能是正确的,主张不能用不宽容的态度打击异己之见,这岂不是说错误思想可以肆意妄为,贻害天下,而我们就不能加以批评压制吗?
我并没有让人们对“错误思想”熟视无睹,而不去用证据去反对它、批判它,而只是主张,争鸣应该在有理有据、心平气和的平等状态下进行。如果用强权去压制自己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论,那就是对真理女神的侵害行为。因为这就是蛮不讲理,不相信真理具有战胜谬误的伟大力量。况且这样一来,信仰就是迫于强权压力的曲意奉迎,而不是基于理解的真心服膺。谁能同意用强力去宣传真理,用暴力去反对谬误,应该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项准则?幻想强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剑能割除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实在是匪夷所思!
所以,言论自由所保护的绝不只是所谓的“正确思想”。如果言论自由只保护有表达“正确思想”的权利,而不保护有表达“不正确思想”的权利,言论自由就会沦为极权专制者把玩的玩具。因为如果言论自由等于言论正确,人们只有表达正确思想的自由和权利,每个人的言论都必须符合真理的金科玉律。这不仅使作为芸芸众生的凡夫俗子丧失了话语权,同时也使当权者有了扼杀异见的借口和依据,认为真理只在我手中,凡是不合我心意的观点,便可动辄斥之为异端邪说而强力压制。可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不说错话?要求每个人言论正确,无异于取消言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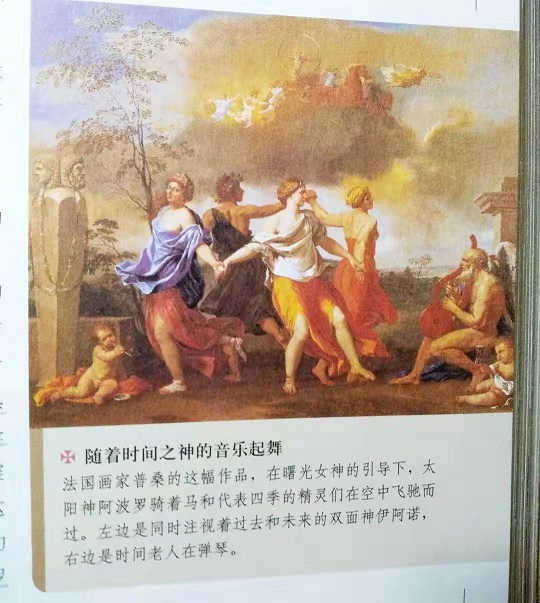
房龙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人类在探索宽容的道路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历程。他对代表着古代世界精神本质的“兼容并包”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讴歌,对文艺复兴时期几位杰出的人文学者备加赞赏。他特别指出:“也就在这个时候,大胆地把所有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思想的某些忠实追随者,开始反抗古老的经院哲学的狭隘限制,并离开了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语法的兴趣当成是一种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那些教会信徒的羊群。”他首先称赞的人物之一,“就是那个有着温顺灵魂的人:伊拉斯谟。”
对于这位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的荷兰人文学者,房龙是这样评价的:
“他给自己选定的,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探照灯的角色。无论什么事情出现在时事的地平线上,伊拉斯谟马上用他的智慧之光把它照亮,尽自己所能除去它的伪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极其憎恨的无知,让周围的人看清它的真面目。”
“暴力不是他的本性,他也从未把自己当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完全缺乏那些想法一一告诉全世界如何达成黄金时代的人所具有的坚信自己正确的信念。”
“他也和所有真正伟大的人一样不喜欢制度。他相信,拯救这个世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改造了每个人,也就改造了世界。”
“伊拉斯谟的‘愚人′与幽默文学中那些庸俗的玩偶相比,是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物。在这本小书(《愚人颂》)中,就像他写的所有文字一样,伊拉斯谟都在宣扬他自己的一种理论,我们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他认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他坚称,最重要的是神圣律法中蕴涵的精神,而不是神圣律法最初版本中的逗号和分号。他以真正的人的态度,不是把宗教看成一种统治方法,而是当成一套伦理体系。这一切,使伊拉斯谟被冥顽不化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为一个‘不信神的无赖’,是所有真正信仰的敌人。他们说他‘污蔑了基督’,但对隐藏在这本巧妙的小书的趣味词句后面的思想,他们却只字不提。”
“就这样,他像一个巨大的海狸一样,夜以继日地筑造那条著名的理智和常识的堤坝。他只是希望,这道堤坝可以挡住滚滚而来的无知和不宽容的滔滔洪水。”
房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拉伯雷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拉伯雷在增加民族欢乐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都说是他给人类带来了笑声,一个作家还能得到什么比这更大的荣誉呢?但同时,他的书又不同于那种可怕的、搞笑的书,它也有严肃的一面。在16世纪前半叶,宗教恐怖政策造成了无法统计的悲剧,而书中通过对这些政策实施者漫画式的描述,为宽容事业打出了一记漂亮的重拳。″
房龙指出:“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之一,就是多种宗教教派建立并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处在这种险恶境况下的人文学者,又能做什么呢?房龙写道:
拉伯雷是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巧妙地避开了能使他陷入麻烦的直接批评。“监狱外面一个快乐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一打愁眉苦脸的宗教改革家”是他的行动准则。因此,他避免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非正统的观点。
但他的敌人仍完全清楚他的真正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对他的书进行明确的谴责。巴黎议会把他的书列入了黑名单,并把管辖范围内找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没收、烧毁。但是,尽管有刽子手疯狂的活动(当时,刽子手也被官方派出去毀掉书籍),他的《巨人传》仍是大众欢迎的经典著作。四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教育那些能从善意的玩笑和嘲谑的智慧这种巧妙结合中获得快乐的人们。同时,对另外一些坚持“真理女神嘴角若挂着微笑,她就不可能是个好女人”论调的人而言,这本书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让他们烦恼不安。
他具有破坏性。但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正迫切需要一些能对社会进行“旧屋拆除”工作的人,而为首的正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面对不宽容的强权,宽容事业的追求者应该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房龙在“索兹尼叔侄”一节中用不太长的篇幅写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小人物。房龙首先向人们介绍说:“他们都是说话斯文的绅士,做事体面而又令人愉快。
“但是,最终,他们在推翻使世界长期饱受苦难的教义暴政时,作出了比一个军的吵吵嚷嚷的宗教改革家更大的贡献。……”
房龙对早逝的叔叔雷利欧一笔带过,重点向人们讲述了侄子福斯图斯的事迹。房龙认为,福斯图斯。索兹尼“生命中的最后20年是他整个人生中最有趣的阶段。因为,就是在这20年里,他具体表达了他关于宽容的思想”。房龙接着写道:
这些思想可以在那本所谓的《教义问答手册》中找到。这本书是索兹尼给那些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结束教派纷争的人们撰写的某种共同的宪章。
16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教理问答、自白、信念、信条的时代。德国、瑞士、法国、荷兰、丹麦,到处都有人在写这些东西。但各地随意出版的这些小册子表达了一个可怕的信念:它们(而且只有它们)包含着真正的真理,用刀剑、绞刑架、火刑柱惩罚那些固执地忠诚于另一种“真理”(小写的真理,以表示其恶劣)的人是所有经过庄重宣誓的当权者的职责。索兹尼的信仰自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表明,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人,无意与任何人争吵。他继续写道:“许多虔诚的人都在煞有其事地抱怨,迄今为止所发表的,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发表的各种各样的教义和教理问题手册,都是造成基督徒之间分歧的祸根,因为它们都想把某些原则强加于人的良知之上,都把反对自己的人视为异端分子。”
这样,索兹尼就以最正式的方式表明,索兹尼派并不主张因宗教信仰问题而放逐或压迫任何人。他诉诸广义的人性,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让每个人都自由地判断他的信仰吧,因为这是《新约》根据最早教会的先例确立的准则。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有什么权力压制、扑灭上帝在其他人心中点燃的圣火呢?又有谁能够垄断《圣经》的知识呢?我们的某个兄弟或许比别人更博学一点,但就自由和跟基督的关系而言,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些话说得好极了,精彩极了,不过据说说早了三百年。……
房龙接着在讲述了蒙田、阿米尼斯、布鲁诺、斯宾诺莎四位人类宽容事业的先驱者后,对洛克的人文思想作了重点介绍。在“新的天国”一节中,房龙在评价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后对洛克的思想大加赞扬:
洛克和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直到死都留在教会中,但是,他真心赞成对于生活、信仰用特别宽容的方式去解释。他和他的朋友问道,除掉一个戴金色王冠的暴君,只是为了另一个戴黑色耷拉帽的暴君实行新一轮的权力滥用,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今天要唾弃这一类教士,第二天又接受了另一帮同样专横跋扈的教士的统治呢?……
……在流亡的四年中,他撰写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使他成了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一个主角。在这封信中(在他的对手的批评下,信扩展成了三封),他坚决认为国家没有权力干预宗教。洛克认为,国家只是一些人为了相互利益和安全创造并维持的保护性组织。洛克和他的门徒们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命令公民个人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国家并没有命令个人该吃什么、喝什么,那么,凭什么强迫公民去这个教堂,而不去那个教堂?
随着新教主义取得了不彻底的胜利,17世纪成了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据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能够终止一切宗教战争。和约规定了这样的原则:“所有臣民都必须皈依统治者信仰的宗教。”因此,一个大公是路德派的公国里的臣民全是路德派教徒,而在另一个当地的男爵碰巧是天主教徒的公国中,所有的公民都是天主教徒。
洛克推理说:“如果国家有权规定臣民灵魂的归宿,那么,一半的人就注定要下地狱。因为两个宗教不可能都正确(按照他们各自的教义问答第一条的说法),那么出生在国界线一边的人肯定会进天堂,出生在另一边的人注定要下地狱。这样,一个人碰巧出生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他将来是否灵魂获救。”
房龙对洛克没有把天主教纳入自己的宽容体系表示遗憾,但可以理解。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对17世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天主教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形式,而是一个政党。这个政党一直在谋划颠覆英国的安全,还建立了‘无敌舰队’,弄来大桶大桶的火药,想要炸毁英国这个友好国家的议会。”
“因此,洛克宁愿把权利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他还支持继续把天主教徒从英国国王陛下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但他只是针对天主教徒危险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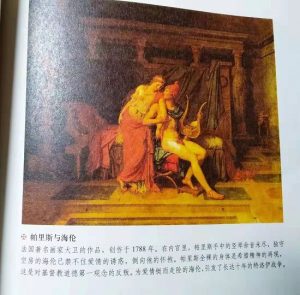
18世纪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封建专制的年代。在如今这样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不管是怎么开明的专制君主,都不会被人们认为是理想的统治者。房龙却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对18世纪(德国)普鲁士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一些开明举措大加褒扬。在《宽容》一书中,“腓特烈大帝”是文字最短的一节,只有一千多字,但房龙对腓特烈大帝的美言占了一多半。他说:
……腓特烈大帝不但对基督教感兴趣,更对基督本人感兴趣。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因此,至少在宗教问题上,他是个特别宽宏大量的人。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
这个英明言论为他将来在宽容的道路上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比如,他颁布法令,规定:只要信仰宗教的人是正直的人,过着正派而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教派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的教派都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国家不许介入宗教问题,只应该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各教派之间的和平。他自己笃信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终审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了解人的心灵”。他从不冒险对上帝发表意见,从不相信神需要人的帮助,要运用暴力和凶残的手段推行神的旨意。
腓特烈大帝所有的这些思想,都比他的时代超前了几百年。当国王给天主教臣民一块土地,使他们可以在首都中心建一座自己的教堂时,当时的人们不住地摇头。当国王成为刚被大多数天主教国家驱逐出来的耶稣会的保护人时,人们开始嘟哝一些不祥的警告。当国王宣布伦理和宗教毫不相干,每个人只要依法纳税,服兵役,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宗教时,人们已经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基督徒了。
当时,这些批评者恰好生活在普鲁士境内,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国王陛下是警句大师,他只要在律法页边写一句机智的话,就可以让那些在某些方面惹他不高兴的人烦心一辈子了。
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一个掌权40年的独裁者,却让欧洲人第一次尝到了几乎是完全宗教自由的滋味。
在欧洲这偏远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没法在喜欢穿綠衣服的人面前称王称霸,反过来也是一样。
不容易啊,腓特烈大帝!28岁继位的你身经百战,与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德国其他邦国几次兵戎相见,多次侥幸脱险。1759年8月库涅尔斯道夫战役之后,你在家书中说:“全完了。我军崩溃之后,我是不会幸存的。”你的两匹战马都中弹倒下了,你的部下把你从战场上拉了下来。虽然普鲁士在你的统率下没有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但是已经获得了“天下无敌”的美名。
在内政方面,腓特烈大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他独搅朝政,内阁大臣不过只是他的秘书而已。在普鲁士,从上到下,人人都直接对君主负责。但大帝并不是专制暴君,1740年他上台后,首先禁止在司法审讯中进行拷打,取消新闻检查,废除宗教歧视。此外,这位新国王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反对权术主义》,其中充满启蒙运动的伦理观点。为了充实柏林学院,他召回流亡的德国学者,并聘请一些外国科学家前来任教。这位大帝还喜欢同艺术家和作家们交往,伏尔泰曾经在他的宫廷里呆过一段时间。
房龙在这一节的最后不无感慨地写道:“腓特烈是否对他努力的成果完全满意,我很怀疑。”但是,“与他伟大的前辈一样,他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份过于丰厚的遗产。”
我的感慨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没有一位像腓特烈大帝一样给我们留下类似的遗产。悲夫!
(未完待续)
荀路20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