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6-14
新帕扎尔市区内店铺密集,穿城而过的拉什卡河全部经过衬砌渠化,与两岸的新楼群构成不错的景致。老城的穆斯林古街狭窄幽深,连片红房夹着点点白(清真)寺,充满沧桑感。
新区的建筑则很时髦,尤其是那座现已成为地标的乌尔巴克大酒店很是抢眼,它那伊斯兰风格的大楼有一部分就跨建在河上,拉什卡河连同滨河路都从楼中穿过,形成“水上酒店,楼下过河”的独特景观。我们开车往返两次穿楼而过,心想下次如果再来,一定要在这里住上一晚。
乌尔巴克大酒店
由于没有重化工业污染,这条河看上去河水很清澈。河边与大酒店隔岸相对的,就是那座伊萨科维奇总督建的奥斯曼城堡。不像乌日策、多博伊和老拉斯那些山头要塞,这个城堡建在平地上,看上去无险可守,但却人来人往很热闹,城墙内现在已经不见建筑,只有一片绿地,成了带围墙的市中心公园,也是免费出入。这里的前后两座古城,山顶的老拉斯和平地的新市场(“新巴扎”)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当年的奥斯曼帝国确实比古塞尔维亚强大得多,所以不那么需要据险而守吧。
车窗外的新帕扎尔
前南时代的新帕扎尔和整个桑扎克地区都没有大学。新世纪在欧洲与土耳其的资助下,新帕扎尔办起了两座大学:公立的新帕扎尔大学和非盈利机构办的新帕扎尔国际大学,还有一所伊斯兰研究院。它们都没有围墙,漂亮的楼房就在市区街道上。我们驱车路过了所有这三个地方。
我曾读到一些怀旧人士说:前南时期的高校水平很高,毕业生专业、英文都很好,在欧洲很容易找工作。现在的高校水平就差了,学生也不好就业。其实中国不也这样吗?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欧美,如今都出现高教普及化导致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大学由精英教育逐渐变成公共教育,除了少数名牌大学还被视为精英摇篮,一般大学也就是人生必经的驿站,平均水准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还是因此提高了。对于原来没有大学的桑扎克地区尤其如此。
新帕扎尔国际大学
由于桑扎克民族主义兴起,这些新建筑都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格调。但我注意到街上的妇女戴头巾的并不多,近来在许多欧洲国家蔓延的伊斯兰化担忧,至少在这个穆斯林城市还看不太出来。
说到“伊斯兰化”,我们在前南地区的感觉与西欧很不一样。前南解体以来,这里的穆斯林不仅在政治上显得比塞尔维亚人更亲欧,而且在世俗化方面也没有比其他民族更加抵制。极端宗教现象当然有,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类现象在前南两个穆斯林族群中要比在塞族东正教徒乃至克族天主教徒中更多见。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面临强大的东正教民族,这里的穆斯林需要欧洲的保护。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世俗主义土耳其的影响。
前南两大穆斯林族群波斯尼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当年都是从土耳其接受伊斯兰教的。但凯末尔革命后,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化的先锋,反过来又向前南地区传播世俗主义。这个现象也其来已久。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时并没有西方从塞族压制下“拯救前南穆斯林”的背景,尽管王国时期的南斯拉夫也有东正教势力压制穆斯林的问题,但一战后的协约国列强总的来说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王室是支持的。那时在国际上为奥斯曼故土遗民说话的主要就是土耳其。所以当时的波斯尼亚人与其说是亲欧,不如说是明显亲土。他们往往向土耳其人展示宗教倾向以示亲近。
殊不知,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那时的土耳其当局对世俗化与政教分离看得甚至比西欧都重,一些伊斯兰习俗在欧洲尽管很边缘化,但完全可以存在,在土耳其却是被严禁的。
反映二战前南斯拉夫的著名游记《黑羊灰鹰》作者丽贝卡. 韦斯特曾记载当时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访问萨拉热窝,穆斯林市长与大批波斯尼亚民众涌上来热情欢迎,现场到处是绿色新月旗、毡帽、面纱——这些当时在南斯拉夫虽不受国王政府待见、但并不违禁,而在土耳其,这些东西却都是“反(凯末尔)革命”的象征,是犯大忌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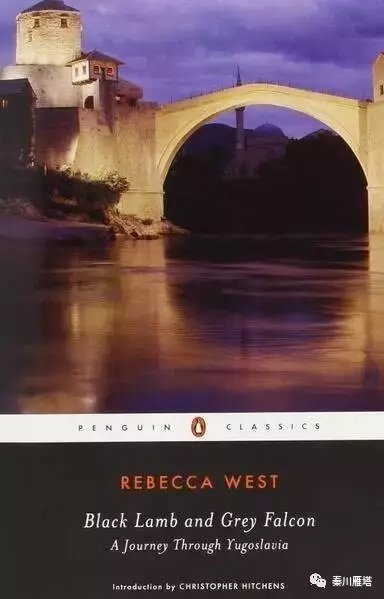
《黑羊灰鹰》
结果自然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一色西装革履高礼帽、比欧洲人还要“欧化”的土耳其来宾当场拉下脸,把热情的市长和欢迎民众好一顿训斥。这个场景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土耳其对前南穆斯林的影响其实恰恰是一场世俗主义的启蒙。
现场看到这一幕的韦斯特感慨地写道:“波斯尼亚的斯拉夫人就像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女人,但最终还是为时间所征服,于是她向旧情人求救了。但回应她的人,虽然打着旧情人的名号,但其实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情人的儿子,那儿子冷冷地看着她,只当她是家史里丢人现眼的一幕;想到这里,我们都不禁要同情心大起了。”
丽贝卡. 韦斯特
直到21世纪初,在整个前南联邦解体危机期间,土耳其对前南穆斯林的影响其实都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动力。当时面对前南乱局,伊斯兰世界向弱势的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表示同情和援助的不乏其人,但是他们的影响不仅无法与西方相比,而且在穆斯林声援中的影响也远远无法与地理接近、历史语言文化联系密切的土耳其相比。
当时的土耳其经过凯末尔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世俗化、工业化、市场化直到宪政民主化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而且无论早先的世俗主义威权政府还是后来的世俗民主政府,都非常热衷于西化、入欧。土耳其二战后就加入北约,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
战后从欧洲委员会、欧共体到欧盟,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每一阶段土耳其都积极争取加入,而且为此做过不少重要妥协。例如2002年土耳其当局应欧洲的要求,放弃对土称为“数十年来头号恐怖分子”的奥贾兰执行死刑判决,并借此正式宣布废除死刑以示与欧洲接轨。
土耳其自1920年代实行凯末尔以宪政为导向的世俗共和“训政”,自1946年实行多党竞选民主,这比今天欧盟成员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都要早。这一进程虽有几次波折,呈现一种“威权推进世俗主义却有碍民主,民主导致宗教复兴而有碍世俗”的周期性困局,但总的来看每次“轮回”都有进步:军人威权一次比一次柔软,多党民主也一回比一回世俗。即便像埃尔多安这样如今被视为反世俗伊斯兰势力的人,在2010年前的执政前期也还是极力“欧化”的。
但土耳其向欧洲“求爱”长达大半个世纪,欧洲对接纳土耳其却一直表现消极,明显地苛求多、帮助少。终于使土耳其从沮丧、生怨到反弹。在近年来的欧洲危机和全球化困境中,土耳其出现世俗化倒退和伊斯兰化卷土重来的“埃尔多安现象”。而且不光是埃尔多安一个人或一党的问题,这种现象已经从政治层面深入到了社会心理层面——不仅各国游客都看到的土耳其城市中妇女戴头巾的比例开始增加。
土耳其街头的妇女儿童
就以近年来在欧洲引发热议的人口增长率差距为例,在并不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情况下,穆斯林旧传统特有的高生育率过去几十年一直稳步降低,导致土耳其人口增长率1960年还高达2.83%,半个世纪来一路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值1.29%,但是此后却明显反弹,如今已达1.78%。这可以视为非世俗化反弹的一个象征指标。
这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恐怕不能仅仅用“穆斯林旧传统的特殊顽固性”来解释。我在其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欧洲这些年来对土耳其(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有双重失误:
一方面,欧洲对土耳其几代人的长期示好无动于衷。就像韦斯特描绘的当年波斯尼亚人以伊斯兰宗教热情追求土耳其,却遭到世俗主义土耳其的拒绝——现在轮到土耳其了。借用韦斯特的话说,当代的土耳其以几十年世俗化热情追求欧洲,“但回应她(土耳其)的人,虽然打着旧情人的名号,但其实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情人的儿子,那儿子(欧盟)冷冷地看着她,只当她是家史里丢人现眼的一幕”。
2016年,安卡拉街头的妇女示威,支持艾尔多安总统发表对西方的强硬讲话
如果说,当年土耳其拒绝波斯尼亚伊斯兰式的追求,有助于巴尔干穆斯林民族的世俗化,那么,当代欧洲拒绝世俗主义土耳其的追求,就成了导致土耳其宗教传统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来在后冷战时代那个欧洲凝聚力最强、土耳其世俗主义进步也最大的时期,欧洲如果能够帮助土耳其融入——就像帮助不少前东欧-“新欧洲”国家一样,那该是人类多伟大的成功啊!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曾经执伊斯兰世界之牛耳长达很多个世纪,欧亚间基督徒与穆斯林一千四百年对立,其间土耳其充当穆斯林冲击基督教欧洲的主力就达700多年。欧土若能结合,将使人们津津乐道的德法两强“化干戈为玉帛”变仇为友的奇迹显得不值一提!
如今回顾起来,这样的成功曾经并非不可能。而欧盟虽然仍是“类邦联”,并未根本改变成员国主权体制,但内政关联程度已经很大,土耳其一旦入欧,将获得巩固世俗主义和宪政体制的强大助力,倒退就会难多了。可惜,机会错过了。但也应该庆幸:前南解体的动荡发生在土耳其世俗主义进步最突出的时期,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如果是发生在现在欧局前景迷茫。土耳其倒退明显的情况下,那就麻烦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