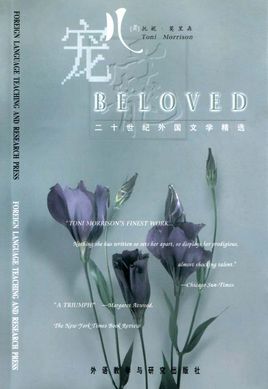第10章
第11章
保罗·D向自己扣起的双手中呵着热气。风疾速穿过胡同,梳亮了四只等待残羹剩饭的厨房狗的皮毛。他看着狗。狗看着他。
后门终于开了,塞丝用臂弯夹着剩饭锅,迈了出来。她一看见他,马上”哦”了一声,微笑里有喜悦也有惊讶。
保罗·D觉得自己回了一笑,可是他的脸冷得厉害,他自己也拿不准。
“伙计,你让我觉得像个小姑娘,下班后还过来接我。从前可没有人这么待过我。你最好留神,我要盼起来可没个够啊。”她麻利地把那些最大块的骨头扔在地上,这样狗就会知道骨头够吃,用不着争来抢去了。然后她倒出来一些东西的肉皮、一些东西的头和另一些东西的下水—餐馆不能用、她也不愿要的—在狗的脚边堆了一大摊,冒着热气。
“得回去把这个刷净了,”她说道,”马上就来。”
他点点头,她又回到厨房。
狗默不作声地吃着。保罗·D心想,它们至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要是她有足够的东西给它们—
她头上的棕色围巾是羊毛的,她把它压到发际挡风。
“你早收工了还是怎么的?”
“我提前走了。”
“有事儿吗?”
“可以这么说。”他说着,抹了一下嘴唇。
“不是裁人了吧?”
“不,不是。他们有的是活儿。只是我—”
“嗯?”
“塞丝,我说的话你不会爱听的。”
她停下来,把脸转向可恶的风。换一个女人,准会眯起眼睛,至少要流眼泪,如果风像抽打塞丝一样抽打她的脸。换一个女人,准会向他投去一种不安、恳求甚至愤怒的目光,因为他说的话听起来绝对像”再见,我走了”的开头。
塞丝镇定、平静地看着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释放或者原谅一个处在需要或困难中的男人。事先就同意,说,好吧,没关系,因为她根本不相信它们—没完没了的死拉硬拽—会达到目的。无论原因是什么,都没关系。没错。谁都没错。
他知道她在想什么,而且尽管她误会了—他不是在离开她,永远不会—但他想告诉她的事情仍然会更糟糕。所以,当他看到期待从她的眼里消失,看到那种毫无责备的忧郁,他说不出口。他不能对这个在风中不眯眼睛的女人说:”我不是个男子汉。”
“得啦,说吧,保罗·D,甭管我爱不爱听。”
本来打算好要说的他说不出来,就说了脑子里面一些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想法。”我想让你怀孕,塞丝。你愿意为我干那个吗?”
这时,她放声大笑起来,他也笑了。
“你到这儿来就为了问我这个?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疯子。你说对了,我不爱听。你不觉得我从头再来一遍太老了点儿吗?”她把手指插进他的手里,情形跟路边携手的影子简直一模一样。
“考虑一下吧。”他说。突然间柳暗花明了:有法子抓住她不放、证明他的男子气概并且摆脱那个姑娘的魔力—一箭三雕。他把塞丝的指尖放在自己脸上。她大笑着抽回手,以免给过路人看见他们行为不端,在公共场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刺骨寒风中。
现在,他仍然拥有一点时间,其实是买的,但愿那价钱不至于毁了他。就仿佛买来一个下午,预支的却是将来的生活费。
他们停止了嬉闹,放开手,耸着肩出了巷子,走上大街。那里的风小一些,不过风留下的干冷使得那些缩在外套里发僵的过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靠在门框上或者商店橱窗前。送食品或木料的大车的轱辘好像怕冷似的,吱吱嘎嘎的。酒店门前套住的马闭上眼睛打着哆嗦。四个女人两两并肩走了过来,她们的鞋踩在木板人行道上嗒嗒作响。保罗·D拉着塞丝的胳膊肘,带她从木板路走下土路,给女人们让道。
半小时之后,他们到了城郊,塞丝和保罗·D又得以相互把手指头抓来拽去,不时趁机摸摸屁股。这么大了还这么孩子气,他们又兴奋又难为情。
决定了,他想。就这么定了,哪个没娘的丫头都不能搞破坏。哪个懒惰的丧家狗女人都不能摆布他,让他顾虑重重、不知所措、摇尾乞怜或者忏悔表白。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就搂住塞丝的肩膀,紧紧箍着。她把脑袋靠上他的胸脯。这个时刻对于他们两个都很珍贵,于是他们停下来,就那样站着—屏住呼吸,甚至不在乎有没有人路过。冬日的光线是黯淡的。塞丝闭上眼睛。保罗·D看着路边成行的黑树,它们自卫的手臂高举着抵御寒冷的袭击。悄悄地,忽然开始下雪了,宛如从天而降的一件礼物。塞丝睁开两眼看着,说道:”恩惠啊。”而在保罗·D看来,那确实是—一点恩惠—专门赐给他们,为他们此刻的感情标上记号,以便日后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记起。
干燥的雪花落下来,又厚又重,简直可以像五分硬币一样砸在石头上。雪总是让他惊讶,雪是多么恬静啊。不像雨,而像是一个秘密。
“快跑!”他说。
“你跑吧,”塞丝道,”我立了一整天了。”
“我在哪儿呢?坐着吗?”他一路拽着她。
“站住!站住!”她说,”我的腿可干不了这个。”
“那就交给我吧。”他说道。还没等她回过味来,他已经退到她身下,用后背驮起她,在大路上跑起来,跑过开始变得洁白的褐色田野。
他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了,她滑下来站稳,都笑瘫了。
“你的确需要些娃娃,跟你一块儿在雪里玩。”塞丝整理好头巾。
保罗·D边笑边呵着气暖和双手。”我当然想试他一家伙。只是还需要个自愿的合作者。”
“我会说,”塞丝回答道,”非常、非常愿意。”
快四点了,离124号还有半英里路。一个人影向他们飘来,在纷扬的雪花里隐约可见;尽管这同一个形象四个月来一直每天迎接塞丝,可是她和保罗·D正在如此忘情地专注于彼此,看见她在近前出现,都不禁心中一凛。
宠儿不理睬保罗·D;她的端详是给塞丝的。她没穿外套,没戴围巾,头上什么都没有,可是手里捧着一条长披肩。她伸出胳膊,想给塞丝围上。
“傻丫头,”塞丝说道,”在外面什么都没戴的是你呀。”然后她离开保罗·D,在他面前接过披肩,围在宠儿的头和肩膀上。她说着,”你得学会懂点事”,然后用左臂搂住宠儿。这时候雪花不飞了。保罗·D觉得,宠儿来之前自己身上被塞丝靠过的部位变得冰冷冰冷的。他跟在两个女人身后一码左右,一路克制着满腔怒火。等到看见窗户上丹芙在灯光下的剪影,他忍不住想:”你又是哪拨儿的呢?”
是塞丝解决的。出乎意料,她安全妥当地一举解决了所有问题。
“这回我可知道你今儿晚上不睡在外边了,对吗,保罗·D?”她朝他笑道;烟囱像个帮腔的患难之交似的冲着从天上射进来的寒流直咳嗽。窗框在一阵严冬的寒风里战栗着。
保罗·D从盘子中的炖肉上抬起眼睛。
“你上楼来睡吧。到你该待的地方,”她说,”……而且待下去吧。”
从桌子一头宠儿那边向他爬过来的缕缕恶意,在塞丝温暖的微笑里变得无关痛痒。
曾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保罗·D感激过一个女人。那次,他爬出树林,被饥饿和孤独折磨得直对眼儿,就去敲他在威尔明顿的黑人区见到的第一扇后门。他告诉开门的女人,他愿意给她劈柴,只要她肯施舍给他一点东西吃。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等一小会儿。”她说着,把门开得大一点。她喂了他猪肉香肠,对一个快饿死的人来说那是最糟糕的东西,可是他和他的肚子都没意见。然后,他见到了她卧室里的白棉布床单和两只枕头,忍不住飞快地抹了抹眼睛,以免让她看到一个男人平生头一回感激的眼泪。土地、草地、泥地、谷壳、树叶、干草、蜘蛛网、贝壳—所有这些东西他都睡过。从来没想象过白棉布床单。他呻吟着倒上去,多亏那个女人帮忙,他才有借口是跟她而不是跟她的床单做爱。那天晚上,吃饱了肉,耽于奢侈,他发誓永不离开她。要想把他赶下那张床,她非得杀了他不行。十八个月后,当他被”北极银行和铁路公司”买去时,他依然感激那次与床单的结识。
如今他第二次心怀感激。他觉得自己仿佛被人从一面悬崖峭壁上摘下来,放到坚实的地面上。在塞丝的床上,他知道自己对付得了那两个傻丫头—只要塞丝将她的意愿公开。他尽量抻开身体,望着雪花在他脚上方流过窗户,现在,那把他带到餐馆后面巷子里的疑虑,很容易解除了: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太高了。他所说的怯懦,别人叫做人之常情。
塞丝钻进保罗·D的臂弯,回想起他在街上求她为他怀个孩子时的那副面孔。虽然她当时大笑着拉起他的手,可还是着实吓了一跳。她很快想到,如果那真是他想要的,性交会有多么愉快,然而她主要是被再次要个孩子的想法吓坏了。需要足够过硬、足够麻利、足够强壮,还得那样操心—重来一遍。必须再多活那么久。噢主啊,她暗道,救救我吧。除非无忧无虑,否则母爱可是要命的。他要她怀孕干什么?为了抓住她?为了给这段路留个记号?反正他没准到处都有孩子呢。流浪了十八年,他肯定跟人下了几个。不对。他反感她已经有的孩子们,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孩子,她纠正了自己。一个孩子,再加上她视如己出的宠儿,那就是他反感的。他反感与姑娘们共享她。听她们三个笑着他不理解的东西。破不开她们之间使用的暗号。甚至恐怕还有花在她们而不是他身上的时间。他们怎么说也算个家庭,可他不是一家之主。
你能帮我把这个缝上么,宝贝?
当然。等我弄完这件衬裙再说。她还穿着来的时候穿的那件,谁都需要变个花样。
还剩下一点馅饼么?
我记得丹芙吃了最后一张。
没有怨言,甚至不介意他现在在房子周围四处乱睡,直到今天晚上,她才大发善心制止了这种夜不归宿的行为。
塞丝叹了口气,把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她知道,为了避免怀孕,自己一直在不让他尽兴,这使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她自己的孩子足够了。假如她的儿子们有朝一日回家来,丹芙和宠儿又一直住下去—嗯,这正好是朝思暮想的情景,不是吗?就在她看到路边携手的影子之后,生活面貌有了多大的变化啊!还有那一刻,一看见那裙子和鞋子坐在前院,她就失禁了。甚至不用看那在阳光中燃烧的脸。她已经梦想多年了。
保罗·D的胸脯在她的手底下一起一伏,一起一伏。
丹芙洗完碗,在桌旁坐下。宠儿自打塞丝和保罗·D离开屋子就没挪过地方,坐在那儿吮着自己的食指。丹芙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她喜欢他住在这儿。”
宠儿继续用手指抠着嘴。”让他滚蛋。”她说。
“他走了她会跟你发火的。”
宠儿把大拇指也伸进嘴里,拔出一颗后槽牙。几乎没有血,可是丹芙还是叫道:”噢—你不疼吗?”
宠儿看着牙,心想:终于来了。下一回该是她的一只胳膊、一只手、一个脚指头了。她身上的零件也许会一点一点地,也许一股脑全掉下去。或者哪一天早晨,在丹芙醒来之前、塞丝上班之后,她会四分五裂。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很难让脑袋待在脖子上,腿安在屁股上。在她记不得的事情中有这么一件:她第一次得知她会在哪天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堆碎片。她做过两个梦:一次是自己爆炸,一次是被吞噬。当她的牙脱落的时候—一块多余的碎片,一排中最后的那颗—她认为毁灭已经开始了。
“肯定是颗智齿,”丹芙道,”不疼么?”
“疼。”
“那你怎么不哭?”
“什么?”
“疼的话,你怎么不哭?”
于是她哭了。坐在那里,用非常非常光洁的手掌攥着一颗小白牙,哭了起来。就像那回,她看见血红的小鸟消失在树叶间,然后乌龟一个跟着一个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想做的那样。就像那回,她看见他站在楼梯下的澡盆里,而塞丝走向他的时候想做的那样。她用舌头舔了舔滑到嘴角的咸泪,希望丹芙搂住她双肩的胳膊能避免它们四分五裂。
楼上的那一对结合着,什么也没听见,然而在他们下面、外面,124号的四周,雪下了又下,下了又下。堆积着自己,埋葬着自己。越来越高。越来越深。
在贝比·萨格斯的思想深处可能一直存着这个想法:要是上帝发恩,黑尔能够虎口逃生,那就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了。只要这个最小的儿子肯为他自己卖命,就像当初为她、随后又为三个孩子卖命那样。三个孩子是约翰和艾拉在一个夏夜送到她的门前的。他们到达的时候,塞丝却没到,这让她既害怕又感激。感激是因为活下来的那几个亲人是她自己的孙儿—最初几个,也是据她所知仅有的几个:两个男孩和一个都会爬了的小女孩。但是她的心还悬着,不敢去想这些问题:塞丝和黑尔怎么了?为何拖延?塞丝为什么不同时跟着上车?没有人能单靠自己成功。不仅因为追捕者会像老鹰一样把他们抓走,像捕兔子一样向他们撒网,还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走就跑不了。你可能会永远迷失,如果没有人给你带路的话。
所以塞丝抵达的时候—浑身都被捣烂、割裂,怀里却抱着另一个孙女—高声欢呼的念头在她脑子里又进了一步。可是,由于仍然不见黑尔的踪影,而塞丝本人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她咽住了叫声—不希望因过早地谢了上帝而减少他的机会。
是斯坦普·沛德开始的。塞丝到达124号二十天之后,他来看望他曾用外甥的外套包裹起来的婴儿,看望他曾递给过一块炸鳝鱼的母亲,然后为了某些个人缘故,拎着两只桶去了河沿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那儿长着黑莓,味道鲜美可喜,吃起来仿佛置身教堂一样。只需一颗莓子,你就会觉得像是涂了膏。他走了六英里路来到河畔,半滑半跑地下到一道因灌木丛生而难以接近的深沟。他在荆棘丛中摸索着,一排排刀刃般嗜血的利刺划破了他的衬衫袖子和裤子。同时他还一直忍受着蚊子、蜜蜂、大黄蜂、黄蜂和本州最毒的母蜘蛛。他浑身都被划破、擦伤和叮咬,却干得很巧妙,用指尖那样轻地夹住每颗莓子,没有碰损一颗。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回到124号,把两只装得满满的桶放在门廊上。贝比·萨格斯看到他撕成一条一条的衣裳、血淋淋的双手、伤痕累累的脸和脖子,坐下来放声大笑。
巴格勒、霍华德、戴软帽的女人和塞丝都赶过来看,然后就同贝比·萨格斯一起笑话这个狡猾而刚强的老黑人:地下使者、渔翁、艄公、纤夫、救星、侦探;挨了两桶黑莓的鞭打后,他终于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对他们毫不在意,径自拿起一颗莓子,放进三个星期大的丹芙嘴里。女人们尖叫起来。
“她还太小哪。斯坦普。”
“肠子要化成汤儿了。”
“会闹肚子的。”
然而小宝宝激动的眼睛和吧嗒的嘴唇使得他们都跟着依样学样,一颗一颗地品尝着教堂味道的莓子。最后,贝比·萨格斯把男孩们的手从桶里打出去,打发斯坦普到压水井那里去冲洗。她已经决定了,要用果子做件对得起这个男人的劳动和爱心的事情。就是那样开始的。
她揉好了做糕点的面团,觉得应该招呼艾拉和约翰来做客,因为三个或者四个馅饼对于一家人来说太多了。塞丝认为他们还可以再添上一对鸡。斯坦普说,鲈鱼和鲇鱼正在往船里头蹦呢—连线都不用放。
从丹芙的两只激动的眼睛开始,聚餐变成了一个九十人的宴会。124号的喧闹声在深夜回荡。九十个人吃得这么好,笑得这么欢,这反而让他们心生怒气。他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斯坦普·沛德用一根胡桃树枝穿着鲈鱼油炸,伸出左手掌挡住四处飞溅的滚沸的油星;想起用奶油做的玉米布丁;想起吃撑了的孩子们疲倦地睡倒在草窠里,手上还拿着烤兔肉的小骨头—于是生起气来。
贝比·萨格斯的三个(也许四个)馅饼变成了十个(也许十二个)。塞丝的两只母鸡变成了五只火鸡。大老远从辛辛那提一路运来的一块方冰—为了掺进他们用捣碎的西瓜拌上糖和薄荷做成的潘趣酒—变成了掺进一澡盆草莓酒的一大车冰块。124号被笑声、诚意和九十人的饕餮摇动着,让他们生气。太过分了,他们想。凭什么都让她占全了,圣贝比·萨格斯?凭什么她和她的一切总是中心?凭什么她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恰好该干什么?又出主意;又传口信;治病人,藏逃犯,爱,做饭,做饭,爱,布道,唱歌,跳舞,还热爱每一个人,就好像那是她独有的职业。
如今,又拿两桶黑莓做了十个或者十二个馅饼,吃掉了足够整个城镇吃的火鸡、九月的新鲜豌豆,不养牛却吃到了新鲜奶油,又是冰又是糖,还有奶油面包、面包布丁、发酵面包、起酥面包—这把他们气疯了。面包和鱼是上帝的权力—它们不属于一个大概从来没有往磅秤上搬过一百磅的重物,恐怕也没背着婴儿摘过秋葵的解放的奴隶。她从来没挨过一个十岁大的白崽子的皮鞭,可上帝知道,他们挨过。甚至没有逃脱过奴隶制—其实是被一个孝顺儿子买出来,再被一辆大车运到俄亥俄河边的—解放证书折放在双乳之间(恰恰是她的主人运送的她,还给了她安家费—名字叫加纳),从鲍德温家租了带二层楼外加一眼水井的一幢房子—是这对白人兄妹为斯坦普·沛德、艾拉和约翰提供了逃犯们用的衣服、物品和工具,因为他们比恨奴隶更恨奴隶制。
这使他们怒不可遏。第二天早晨,他们靠吞食小苏打来平息肚子里的翻江倒海,这纯粹是124号那场大方、轻率的慷慨表演造成的。他们在院子里互相嘀咕着肥耗子、报应以及多此一举的骄傲。
浓重的非难气味在空中凝滞。贝比·萨格斯在给孙儿们煮玉米粥的时候注意到它,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儿,她站在菜园里为胡椒秧捣碎硬土时,又闻到了那气味。她抬起头四面张望。在她身后向左几码远的地方,塞丝正蹲在豆角中间。她的肩膀被垫在裙子下面辅助治疗后背的涂了油膏的法兰绒弄得变了形。她近旁的一只蒲式耳箩筐里是三个星期大的婴儿。圣贝比·萨格斯举头仰望。天空湛蓝而晴朗。树叶明晰的绿色中没有一点死亡的迹象。她能听见鸟叫,还能隐约听见远处小溪流过草地的潺潺声。小狗”来,小鬼”正在啃昨天宴会剩下的最后几块骨头。房子附近什么地方传来巴格勒、霍华德和那都会爬了的女孩的声音。似乎什么都没出毛病—然而非难的味道异常刺鼻。在菜园后面更远的地方,离小溪更近、不过阳光充足的地方,她种下了玉米。尽管他们为宴会摘下了那么多,那儿仍有一穗穗玉米在成熟,她站在那里就可以看得见。贝比·萨格斯又弯腰为胡椒秧和黄瓜藤锄草。锄头的角度刚好合适,她小心地铲断一根顽固的芸香茎。芸香的花被她揪下来插进帽子的裂缝中;剩下的丢在一边。劈木头单调的哐哐哐的声音提醒了她,斯坦普正在干他昨天晚上答应的差事。她冲手里的活计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又直起腰,再一次去嗅那非难气味。她拄着锄头把,专心致志地嗅着。她已经习惯于没有人为她祈祷了—但这肆意飘荡的嫌恶却是新的。那不是白人—这一点她还能肯定—所以只能是黑人了。于是,她全明白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在生她的气,因为她走得太远,施与得太多,由于不知节制而惹恼了他们。
贝比闭上眼睛。也许他们是对的。突然,就在非难的气味后面,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嗅到了另一种东西。黑压压地赶来。是一种她拿不准是什么的东西,因为非难的气味盖过了它。
她使劲挤着眼睛去看它到底是什么,但她能看清楚的只是一双样式不讨她喜欢的高靿鞋。
既沮丧又惶惑,她用锄头继续锄着地。会是什么呢?这个黑压压赶来的东西。现在还剩什么能来伤害她呢?黑尔的死讯?不。她已经为那个作好了准备,比为他活着作的准备还要充分。那是她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时她几乎没瞟上一眼,因为犯不上费心思去认清他的模样,你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看着他长大成人。她已经干了七回了:抓起一只小脚;用自己的指尖检查那些胖乎乎的指尖—那些手指,她从没见过它们长成母亲在哪儿都能认出的男人或女人的手。她至今不知道他们换过的牙是什么样子;他们走路时头怎么放。帕蒂的大舌头好了么?菲莫斯的皮肤最终是什么颜色的?约翰尼的下巴上到底是一个裂缝呢,还是仅仅一个酒窝而已,等下颚骨一长开就会消失?四个女孩,她最后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腋下都还没长毛。阿黛丽亚还爱吃煳面包底儿吗?整整七个,都走了,或是死了。如此看重那个最小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们允许她留下了他。他一直跟着她—到每一个地方。
她在卡罗来纳时屁股受过伤,这对于加纳先生来说可真是笔划得来的交易(价钱比当时只有十岁的黑尔还低),他把他们俩一起带到肯塔基,到了一个他称做”甜蜜之家”的农庄上。因为屁股,她走起路来像只三条腿的狗似的一瘸一拐。可是在”甜蜜之家”,看不见一块稻田或者烟叶地,而且更没有人把打翻在地。一次也没有。不知为什么,丽莲·加纳叫她珍妮,不过她从来没有推搡过她、打过她或者骂过她。甚至当她被牛粪滑倒,摔碎了围裙里所有的鸡蛋的时候,也没有人说”你个黑母狗,你犯什么病了”,更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
“甜蜜之家”同她以前待过的许多地方比起来实在很小。加纳先生、加纳太太、她本人、黑尔,还有四个一多半都叫保罗的男孩子,构成了全部的人口。加纳太太干活的时候爱哼歌儿;加纳先生呢,则表现得似乎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好玩的玩具。谁都不让她下田—加纳先生的男孩们,包括黑尔,包了那些活儿—也是件幸运事,因为反正她也干不了。她只管站在哼歌儿的丽莲·加纳身边,两个人一起做饭、腌菜、浆洗、熨烫;做蜡烛、衣裳、肥皂和苹果汁;喂鸡、猪、狗和鹅;挤牛奶、搅牛油、熬猪油、生火……不算回事。而且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
她的屁股每天都疼—可她从来没提起过。唯有黑尔,在最后的四年里一直仔细地观察她的动作,知道了她上下床必须用两手搬起大腿才行;就是为了这个,他才跟加纳先生说起要赎她出去,好让她坐下来有个变化。多体贴的孩子啊。是他,为她做了件艰苦的事情:把他的劳动、他的生活给了她,如今也把他的孩子们给了她,现在,她站在菜园里纳闷非难的气味后面那黑压压赶来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就刚好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甜蜜之家”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毫无疑问。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悲哀就在她的中心,那丧失自我的自我栖居的荒凉的中心。那悲哀,就好比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们埋在哪里,或者即便活着也不知是什么模样。事实上,她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丝线索,帮助她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她会唱歌吗?(她唱得好听吗?)她漂亮吗?她是个好朋友吗?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吗?可以成为一个忠贞的妻子吗?我有个姐姐吗,她宠我吗?假如我妈妈认识我她会喜欢我吗?
在丽莲·加纳的家里,她从伤了她屁股的农活和麻痹她思想的疲惫中解脱出来;在丽莲·加纳的家里,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或强奸她)。她听着那白女人边干活边哼歌儿,看着她的脸在加纳先生进来时骤然亮起来,心想:这个地方更好,可我并不更好。在她看来,加纳夫妇施行着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对待他们像雇工,听他们说话,把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教给他们。而且,他不用他的奴隶男孩们配种,从来不把他们带进她的小屋,像卡罗来纳那帮人那样命令他们”和她躺下”,也不把他们的性出租给别的农庄。这让她惊讶和满意,也让她担忧。他会给他们挑女人吗?他认为这些男孩兽性爆发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在招惹天大的危险,他当然清楚。事实上,除非由他带着、否则不准离开”甜蜜之家”的命令,并不真是因为法律,而是考虑到对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奴隶放任自流的危险才下达的。
贝比·萨格斯尽量少说话,以免惹麻烦,在她的舌头根底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那个白女人发现她的新奴隶是个沉默的好帮手,就一边干活一边自己哼歌儿。
加纳先生同意了黑尔的安排,再说,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让她获得自由对黑尔更有意义了,于是她就自愿被运过了河。在两件棘手的事情中—是一直站着,直到倒下;还是离开她最后的、恐怕也是唯一活着的孩子—她选择了让他高兴的那件难事,从来没问他那个常常令她自己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混到六十岁、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似的女奴要自由干什么?当她双脚踏上自由的土地时,她不能相信黑尔比自己知道得更多;不能相信从没呼吸过一口自由空气的黑尔,居然懂得自由在世界上无可比拟。她被吓着了。
出了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她问自己。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也不好奇。可是突然间她看见了自己的双手,同时,头脑中清晰的思绪既简单又炫目:”这双手属于我。这是我的手。”紧接着,她感到胸口一声捶击,发现了另一样新东西:她自己的心跳。它一直存在吗?这个怦然乱撞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就放声大笑起来。加纳先生扭过头,睁大棕色的眼睛看着她,也不禁笑了。”有什么好笑的,珍妮?”
她仍然笑个不停。”我的心在跳。”她说。
而这是真的。
加纳先生大笑起来。”没什么可怕的,珍妮。原来怎么着,往后还怎么着,你不会出事的。”
她捂着嘴,以免笑得太响。
“我带你去见的人会给你一切帮助。姓鲍德温。一兄一妹。苏格兰人。我认识他们有二十多年了。”
贝比·萨格斯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去问问她好久以来一直想知道的事情。
“加纳先生,”她问道,”你们为什么都叫我珍妮?”
“因为那写在你的出售标签上,姑娘。那不是你的名字吗?你怎么称呼自己呢?”
“没有,”她说,”我自个儿没称呼。”
加纳先生笑得满脸通红。”我把你从卡罗来纳带出来的时候,惠特娄叫你珍妮,他的标签上就写着你叫珍妮·惠特娄。他不叫你珍妮吗?”
“不叫,先生。就算他叫过,我也没听见。”
“那你怎么答应呢?”
“随便什么。可萨格斯是我丈夫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