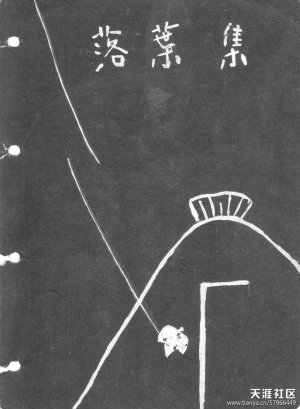四、“诗史互证”的一九六四
物证、人证都没有,只有另辟蹊径。
据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示:在明显的外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外在的证据必须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如从同时代一些相关的事件中找到暗示,或从别的可查考日期的事件中引出的线索等都是这类内在的证据。但这种能补充说明外在证据的内在证据,只能确定该作品与那些外在事件有关的部分的写作日期。”(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63 页)当然他们指的,是“假如我们一定要考证那些没有写明著作日期的手抄本的系年问题”而言。对《我早期的六个诗集》而言,情况还不一样。起码我所拿的稿本上,很多诗是“写明著作日期”的。
所以我的工作,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有”的基础上,进行审核、落实。
“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本证或内证的方法。这是顾炎武指出的——“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音论》)当然实际工作中,经常本证、旁证交叉进行。对我而言,就是在“诗自相证”的时候,适时引进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方法。不敢绝对说,它畅通无阻。而是说,要看什么作品、要看什么作者。对于带有“见证”性质的写作,我以为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对于带有“写吧,记忆”自觉的写作者,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
我们古代有“感物说”、“缘事”说,也有“心不孤起,仗境方生”(吴乔)的谈论。其实至今也说不上过时。就像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思忖——“即使那些保持了内心自由的人,所思考的也仅仅是强行塞到我们跟前的眼下。思想被俘虏了。某种程度上,思想总是为其时代所俘虏,但时代本身又扩大或限制思想的广度,而我们的时代把思想限制到了可怜的极限。”
无独有偶的是,陈墨表达过类似意思。曾在读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时反思:
现代人写诗,无论如何都不及古人空灵,难免粘滞。意象空灵,意蕴才能宽泛。就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恐无一首现代诗能触到点上。因为我们生存的条件,精神的荆丛,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我以为这些话,对于认识其《落叶集》,也是有效的。一般来说,很多悼亡诗立意上具有超时代、超时空的性质。因为死亡不分中外古今。只是死亡又是个体的,只是《落叶集》这个集子,确实有“纪念碑”、或做见证的冲动。就像第一首第一句: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完全喑寂的世界
还有更触目惊心的《无墓》:
抬望眼/仰天长啸:/这儿本就是一座/大墓/我们都是活死人/走着的肉/行着的尸/相互还嚷着腐臭的/语言 陷害/在尸群中公开进行/……
——这些诗句有“时代烙印”吗?还有下面的《真》,能以“诗”说“史”吗:
惊蛰声中/千山万水充军跋涉/迷惘宁愿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小雪大雪之间/你黯然坠落
我以为不好沾滞。但是如谨慎地讲:用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考察、判断其写作年代甚至年头……应该是可取的?我甚至想说,如果运用恰当,不仅能以史证诗,或者还能“补史之阙”?就像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写:“代宗朝时,(杜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 年版)
刚接触此诗集,曾想当然认定:“这是一个完全喑寂的世界”云云,当然是写“文革”,只能是指“文革”。那时的我,其实对“文革”,只有脸谱化、符号化的认识。只是与陈墨访谈后,经过阅读与思考,越来越认定,“这是一个完全喑寂的世界”,根本无关文革“动乱”,而是文革爆发之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社会氛围的写照。
《落叶集》让我看到:史不言一九六四,“黑五类”已活不下去——先看“史”:
1964年6月,京剧《红灯记》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0月某日公演,引来如潮好评。11月某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陪同下再次观看(此前曾在周恩来邓小平陪同下观看)。除了《红灯记》,还有《东方红》。官史至今洋洋自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第一部歌舞史诗巨片,为国庆15周年献礼,由周总理担任总导演,3500名艺术家集体创作出的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
1964年10月2日,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有3500多名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拉开帷幕。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掌声如潮。毛泽东也在10月6日观看了演出,并在观看当中多次鼓掌向演员致意。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编创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恩来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除了《东方红》,还有《红色娘子军》,“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更有早些时候,1963年1月《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发出号召:“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一九六四,味道究竟如何?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假如你是将要被扫除的“害人虫”呢?假如是那样,滋味并不好:
蜀犬吠日/因为那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吴牛喘月/因为那时/石头/都被烤裂/于是眼中的形象/被昏昏噩噩的思维/扭曲
时间不会生根/地下流行/呕吐综合症/红十字插到哪裏/思想的佛尔马林/熏得人想死
思想的石女/拒絶怀春/语言发酵/却越蒸越硬/雄鸡也左声左气/连篇累牍/不动脑筋/明明是沼泽/却被唤做星星
为了干凈/不惜将世间的病菌/杀尽/八卦炉却传出/悟空的鼾声/乌托邦/在底片上曝了光/洗不出照片/臆语总是没有句号/疯狂地在/印刷体中繁殖/漫无国境
人心髙速旋转/苟延残喘得地老天荒/打字机/滴滴答答地咳/医生的潦草/让心跳骤停/丛丛荆棘/点缀房前屋后/鸡鸣声有些扭曲/东坡梦游/天上 地下/到处黑沉沉/甚么都没有
上面诗句,我边抄边想:如果那时被“人赃俱获”,会怎么样?!……就继续抄:
我们向阳/几乎沦为天数/同那觅食的蚁群一样
小数点左移/黑色沦为负数/死亡之门洞开/生变成死的学生
镣铐的细胞/在疯狂地裂变/与延伸/看不到这/噩梦的尽头
父亲在雷锋塔下/母亲流放到西伯利亚……
一部半个世纪前,政治贱民的哀歌。相当时过境迁,才能“蓦然回首”:
在阶级斗争肆虐中华大地的年代,城乡青年倍受其难。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烈度最深的,莫过于“阶级路线”造成的伤害。几千万城乡青年,因家庭出身“有玷”(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侮辱乃至摧残。直至今日,对于这段历史悲剧,披露它的真相仍有相当难度。官方文献,往往将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即便偶有记载,也是轻描淡写或几笔带过。……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曾经的北大学生,据说很早就写诗的周国平回首“四清运动”: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
他们说的,无论是否真切,毕竟不能等同于——“贱民能否发言”。
贱民怎配发言?!马大胡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定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武器的批判到了东方斩钉截铁:“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造反”大潮起来后,遇罗克写《出身论》: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为他的揭案而起,付出了生命代价。所以再多不满,都得埋地下。多少年后高尔泰发问:“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高尔泰:《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其实只是当时,血腥污泥深处,抖抖嗦嗦的《落叶集》在“少陵野老吞声哭”:
皇族/必得充分地奉承/但月前/应该属于/奴隶的我们/我们披着头发/在郊外祭祀祖先/长歌当哭
天安门太对称/一劈两截/火花四溅/化着流星/可钉上苍穹/只有我的背叛……
抄着这些诗,一切阐释都多余——简直是噩梦:
傩祀已走/面具世界恢宏/铿锵话语一统/水面飘着暗喻/哪裏才是意义的萍踪?/吴刚不停地/砍桂/捣药的玉兔/瞌睡得蒙蒙董董/舞蹈旋转的/嫦娥/停不下来/传说取悦于传说
——这不是跟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吗?全国人民都深情:“我失骄杨君失柳……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躲在暗处的人却含沙射影:“传说取悦于传说”——一个传说是嫦娥、吴刚,一个传说指乌托邦……双重解构。先看“史”:公元1963年,毛泽东70岁寿诞来临之际隆重推出《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再看“诗”,《残萤集》中另一则:
听人家说/太阳是沉默的老人/他并不骄傲/“骄阳”只是误传
再看《落叶集》中,一系列“对话关系”:
程序化/喂不肥一头/思考的猪/雷锋塔是柄/去势的刀/美人鱼和美女蛇/都入了脸谱系列/七星瓢虫/髙兴得拍手/病到一定程度/写日记/成了新的赌博/——将其当作/一头会思考的猪
——容我向历史“破案或揭发”吧:这黑五类狗崽子,竟将伟大中国的“学雷锋运动”,攻击为“雷锋塔是柄去势的刀”,更说什么“写日记成了新的赌博”……有人或许分辨:“雷锋”不是“雷峰”,此“雷锋”非彼“雷峰塔”……我会赞同说,是的,《无父母》一诗中,“父亲在雷锋塔下”云云,说明诗作者系错别字大王。或者无心插柳,可是怎么说?就像几十年之后,曾当过文化部长的某著名小说家耍贫嘴:
学雷锋时我常常想起“雷峰”,这种汉字的谐音可真够叫人分心的。再有就是,一旦有机会, 我真想写一部《白蛇传》题材的叙事长诗。
(王蒙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林彪题词所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
……在六十年代的反修防修斗争中,不仅需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而且更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个人崇拜者”。《雷锋之歌》的独到贡献就是大大宣扬了对崇拜者的崇拜。领袖在雷锋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偶像, 而这位偶像崇拜者的雷锋又成为了大众心中的偶像, 通过他, 把一系列反修防修的精神打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心灵之中。
(董健《论反修防修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03期)
我关心的只是,探求“今典”,窥探“互文”关系,有助于确定《落叶集》的写作时间。再查《将其》一诗,不是跟《雷锋之歌》过不去,他过不去的还有郭沫若先生:
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毛主席《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有句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昆仑)裁为三截”。我读了《雷锋日记摘抄》,感觉着雷锋同志就像这样一把宝剑。
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年,
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坎里,
他的声音永远在空中回旋。
“我是大海中的一珠水,
我要无保留地为人民贡献。
党要我入地,我就入地,
党要我上天,我就上天。
“我自己实在是非常平凡,
有人说我是猪,我也心甘情愿,
我是牧猪儿出身的人,
对于猪倒有十分的好感。”
(《中国青年》1963年5、6期)
且看怎么互文:一个说“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一个说“雷锋塔是柄去势的刀”……此即话语旅行。话语旅行的表现还有:郭沫若“劈断昆仑”,说明是引用毛主席《念奴娇•昆仑》。根据目前考证,《念奴娇•昆仑》托词写于1935年10月“长征”途中,发表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最豪迈是后几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据作者自注:“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63年版改“还东国”。现在看《落叶集》中,什么伴随“长夜之饮”:
只有我的背叛
可钉上苍穹
残萤死在草丛
打碎的夜光杯
语言重新胶合
盛着热血 依然
作长夜之饮
天安门太对称
一劈两截
火花四溅
化着流星
可钉上苍穹
只有我的背叛
——难怪到了后来,写出《天安门》。九九《魂断台北》写:
陈墨君有一个别号“黑乌鸦”。当年,他一年四季服装漆黑,里里外外,衬衣、鞋子、甚至袜子,买不到黑色的就自己染成。黑色意味着什么,真是不言而喻!如果在“文革”中他有工作单位,都凭这装束,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打成反革命。然而黑色,却是他的风格:
……我的感觉是,陈墨君衣黑裤黑,也许,连思想都是黑色的。不然,后来1976年他怎么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长诗《垮了,天安门》?(见《野草》1979.4.第二期)
肯定是后话了。记得1995年元月,“梅、周百年纪念”活动之际,陈墨写《戏话——并非玩笑》一文,说宁愿变蛇、变鱼,躲开这矫情、虚伪之徒横行无忌的人间:
……我辈“牛鬼蛇神”及“黑五类”,在“正统”的淫威下,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活得象条狗时,痛定思痛,宁可终身备受“脱鳞”之罪,也要变人!虽然“法海铛”依然法力无边,光芒万丈,而且愈来愈“刺目”;虽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来愈“崇高”!
怎能忘一九六四?《东方红》中的朗诵声,依稀在《落叶集》中回响: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哪,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