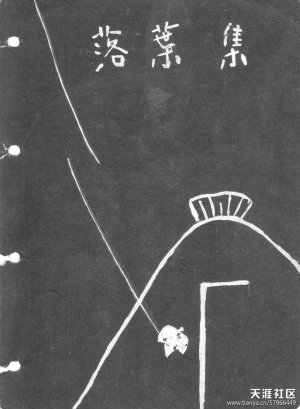五、“吾犹昔人,然而并非昔人也”
其实《落叶集》中,“以时事入诗 ”(胡震亨)的印记还多:
等级化的图案/勾引着性欲/赤橙黄緑青蓝紫/沦为后宫/月牙泉渐渐干涸/左摆 右摆/椰树林群情亢奋/从赤道划来的独木舟/搁浅?
当然指1964年推出的《红色娘子军》中,“左摆 右摆”的妖娆镜头。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禁欲主义的年代,“大腿满台跑”给青春期男孩多少刺激。以至于多少年后,诗人耿耿于怀着当年,“我个人还有性压抑的忧伤”。
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5年5月的《叶子老师教我象征主义诗歌》之八云:
纵被狗咬,你也要功成八百、行满三千
穷街娃读禁书,梦中都不敢调戏牡丹
漫说是用飞剑斩了为非作歹的黄龙
自宫的念头都把我折磨得形只影单
写于1967年5月的《自宫》一诗,同样感叹“当想到解脱,解脱却被锁定/我跋涉在荆棘遍地的山”。可想而知,当年眼瞪着“赤橙黄緑青蓝紫/沦为后宫”……会有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其实我在,事后诸葛亮地轻描淡写……据福柯提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云:“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他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总之,“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了”。此为身体的政治。显而易见,“羡慕嫉妒恨”的诗人,已经有见于此种身体的政治。前面引用过“艺术与性欲/几乎同时涨满全身……”,以及“自宫的念头都把我折磨得形只影单”,可他并不头昏脑胀:
惊蛰声中/千山万水充军跋涉/迷惘宁愿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
——固然荆棘遍地,也要见招拆招,恶攻《东方红》中《抬头望见北斗星》。
仇恨不能闻鸡起舞/饥饿更不能/叫化鸡/叫化出一轮红日/把婚姻烤成干猫鱼/不鲜 徒有其腥
——对于“仇恨”的解构,让人想到“收租院”,大喇叭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让人想到《红灯记》,李铁梅唱“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至于“叫化鸡/叫化出一轮红日/把婚姻烤成干猫鱼”,讽刺意味很明显。
相信我长大后/会跟你一模一样
——透露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孤苦无依,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和《红灯记》“革命还有后来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接班人之歌”……之互文。
好不好说,还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意志较量?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且看“史”: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这是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然后就有1964年6月,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再看“文”:《红灯记》,“学雷锋”,社教运动,“文艺整风”,《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叙说:“文革”前夕,在青少年中涌动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潜流。下面这首朗诵诗曾一度在校园中广泛演出和传抄,它表现了新一代要崛起的意志:
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革命的红旗谁来接/亲爱的党啊/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子孙啊/革命本性永不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老一辈的血……把未来的世界啊/交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接班人之歌》(徐荣衔、钱初承)1964
杨健评说: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不是考虑如何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巨人”,而是从政治功利出发,培养他们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左倾思潮,以便利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冒进政策的需要。“它在提倡社会道德纯洁化的同时,还提倡个人迷信,从而造就了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一代青年。……新生代被包围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从震耳欲聋的时代宣传中,分辨出微弱的抵抗之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5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现在来看,甚嚣尘上的鼓噪背后,清醒的抵抗是有的。只是被埋没。
“诗史互证”的考察足以让人认定:“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的尘埃落定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誓语自深深处传来。
相信我长大后/会跟你一模一样
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布罗茨基提示,“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这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文明的儿子》)我想遵循他的指引,换一个角度,从诗歌写作主体及其心理特征的角度,推断《落叶集》的“心理年轮”。
且看《一问》:
一问/杜鹃花便谢了/远山含雪/不再是炊烟的/背景/草儿依旧青青/锈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奋
我心沉沉/因为一问/满是补丁的衣服/太小/雁阵飞过时/愿我在梦中/不曾听到它们/匆匆的声音
叶落了/你走了/可是灵魂的/一次迁徙?/我宁愿在等待裏/变得苍老/任它红霞满天/鸟语花香/我的迁徙跚跚来迟
再看《与》:
你说/……/我想/于是亲情/成为亚宗教/关系不变/毋需智力/分裂亲情的“学说”/鞋成了荆冠/脚有什么智慧?/我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开始失眠……
还有《他》:
心中一经有了/上帝/世界倾刻间/便沦为了/他/……/最后一声叹息/像流星/我睁开沉重的/眼……
这些细节与心理,过了半个世纪,就跟昨天一样。《落叶集》这些诗,该是“一问/杜鹃花便谢了”时写的。“草儿依旧青青/锈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奋”,当是刹那间的震动与唤醒。今天或许觉得,感情过于强烈,其实正好说明,“悲歌可以当泣”。要是拖上几年,大概会写不出来。所以我以为《落叶集》,是先哭出来,再沉淀、在推敲、再结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陆机)
——何况深爱的人。何况自己的恩师。更何从小是“弃儿”,他对他亦师亦父。
更何况是,一个人竟然从世上不翼而飞!从十五岁起,就“变得沉默寡言,落落寡合,郁郁寡欢”的陈墨,借用鲁迅的描摹,正所谓“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叶子老师走了?倾刻间世界沦陷。
“相信我长大后,会跟你一模一样”,是当时的心理,也是自知“未长大”的人自然的口吻。诗人1945年底出生,1964年11月刚19岁,一旦发现“在我眼中,你就是我的父亲”猛然不见,在不敢相信、悲愤欲绝之际,产生“我长大后”怎么样的联想很自然。“长大”一词自然流露了“刚刚开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若是过上三、四年,比如在1968、1969年,当诗人二十二、三岁时用此口吻,基本没有可能。
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还要提及的是, “长大”一词具有“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烙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方知“等我长大了要……”云云,是那年代的洗脑神曲: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物质匮乏,少年宫合唱组即编排了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提起这个话题的是合唱组的老学员周正彪,他一说到这儿,一同受访的伙伴们便哼唱起来。罢了,几位学员无不感慨,“唱完这首歌,等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些人就真的都去当农民了。
(于淑娟:《少年宫里的旧时光:社会主义的儿童殿堂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长大”一语有点“这个”。联系前引“感觉如同踏浪而去……将你的花心藕骨”,还有下面《这个》,含混而真切地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茫然、无定:
淅淅沥沥的这个/像疯疯傻傻的少女/走失了/在深夜的长街/她被许多眼晴/窥视着 企图着/……
天狼星在西北/你握着的只是/黄卷青灯/这个还是耳鬓厮磨/窃窃私语/走不出/淅淅沥沥
这个/一旦沸沸腾腾/也许是灾难/也许是苏生/像她被许多眼晴/窥视着 企图着/可能被蹂躏/可能被救赎/……
起初读《这个》,让我费思量。肯定是淅淅沥沥了,成都的冬春会下雨。而且经常是,晚上润物细无声地来。肯定是失眠,一个黄卷伴青灯的少年,“走不出淅淅沥沥”。后来我又觉得,或许是“香草美人”的路数?甚至不排除,有《红色娘子军》中孤女吴琼华的影子。
诗歌当然是跳跃的。只是解读,得一步一步来。
就让我说明,如何此处的“她”,与“大腿满台跑”的芭蕾有联系,在此基础上,“吴琼华/洪常青”的关系,转换成了现实生活中“我/叶子老师”的镜像?
一篇女性主义视角的文章指出,“革命样板戏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在地主、土匪的欺凌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救世主的出现”:
……女性成为苦难、压迫、剥削的承受者,成为“苦大仇深”的原型(如吴清华、喜儿、常宝),她们的个人痛苦只有在遇到代表正义与拯救的男性(洪常青、大春、杨子荣)时才上升为阶级和民族苦难,具有救赎的价值。可见这些样板戏中为数不多的受难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依然延续着传统男权文化中“支配与被支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女性的独立意识与价值完全遮蔽在“高、大、全”的男性英雄之下,对她们的受难与伤口的展示,更多地是为了衬托和突出男性英雄的高大和完美,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男女两性模式的恪守。
(盛晓玲:《时代、政治与男权文化的合谋——女性主义批评下的“革命样板戏”》,《四川戏剧》2013年05期)
《落叶集》的确有,“未及”的哀怨:
未及弯曲的仇恨/伤到自己的正直/和头上三尺的眼睛/涟潋是你的哀怨么?
哀怨是“未及”(无论心理,还是生理)的表征。但是也有对于养育的感念:
我吃窗台上的面包/长大 成人/不在西伯利亚/这儿/是你的窗台
更有辗转反侧后,幸遇“常青指路”的胸有成竹:
于是你把月前/最动人的故事/讲给我听/从此/我的月前/有了人生最美的色彩/最真的祈祷/和最善的梵音
因为我 因为我/终于有了归属/像稚嫩的翅膀/追赶着前面/“人”字形的雁阵
此处还有写,“稚嫩的翅膀”。此后就更多,告别哀伤的沉稳:“八卦炉却传出/悟空的鼾声”;“向秀不在旷野/叮叮当当/他锤打着一块/红红的铁”;“历史已走/鱼肠剑在中途折断/黑衣人/走过板桥/清啸一声/雪花在叶间纷落……”,可能无须乎解读?
但还是想援引一点,从成长角度解读鲁迅《铸剑》的文字:
十六岁失父之后鲁迅即步入了成人社会
眉间尺的突变残留了鲁迅对于自己成长过程中那种突然面对全新而且艰难境遇的黑色记忆。
与眉间尺通过母亲的讲述获悉杀父之仇的成人仪式相比,鲁迅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这个强大仇敌的存在与威胁。
十六岁这个临界点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对比无论对于眉间尺还是对于作者来说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铸剑》增益的开头也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眉间尺优柔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独自完成复仇使命,黑衣人的出场成为叙事逻辑上的必然;……
(王海燕《鲁迅〈铸剑〉的精神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这里涉及的心理突变,我以为跟《落叶集》一致。几乎可以说,诗中“黑衣人”后面,有个未出场的眉间尺——其实《未及》,有所暗示。最好还是倾听一下,很多年后的2000年9月,陈墨故事新编“茶铺派文学理论”时,关于“黑衣人”的放言高论:
人生,倘若不甘于为生存而平庸,就得有一个令生命得以光华的目标。眉间尺生而就是复仇的,而黑衣人则像是荒原上一条伤痕累累的狼。然而他的报仇与其说是所受伤害过深,毋宁说是追求一种解脱。——他必须用这完美的形式来告别生命,告别这令他无限困惑的人世,而仅仅留下一曲复仇的千古绝唱。
……须知黑衣人乃鲁迅极力刻画的“复仇天使”呀!他非侠非盗,非巫非仙;不是职业杀手,更不是变态鹰犬;他只是一个叛逆的“另类”,一个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唯美主义者。
鲁迅在后来将《眉间尺》更名为《铸剑》,已透露出此篇深刻的立意。因为此篇小说并未叙述眉间尺父亲铸剑的过程。所以我以为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铸剑的其实是黑衣人。……于是,我清楚:作为一个现代愤世嫉俗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在这个极权加后现代的社会里,除了无法逃避“人我所加的伤”而外,还得忍受在人群中不期而至的孤独感。而孤独又几乎让我“憎恶了我自己”。
(《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五 铸剑》)
当然是“后话”。现在言归正传:我以为《落叶集》中《老师》:“生命上下求索/找寻着意义/正如语言左冲右突/遍体鳞伤/当她重新上路/这才是诗!”……这些诗句跟收入《灯花集》中,标明写于1965年3月的《草鞋》形成“姊妹”关系:
草鞋苏醒在昨天
刀耕火种的希望
与风雨结伴
跌落在历史的深渊
磨损的笔穿上草鞋
为了重新上路
走进鸟语
重拾春天
——都有“重新上路”,写作时间该近?当然“走进鸟语/重拾春天”的心情,跟《落叶集》基调有所不同。一个是单篇,一个是巨制,后者当然是“交响”。总觉得“重新上路”,暗示《落叶集》主体部分已“竣工”?再看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思想的嫩芽长在历史的空隙
反思只是想从这颠簸的鹿车上下来
再次品尝无路可走时隐痛的潮汐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翠碧
杜鹃鸟不累,不如归去芳心太急
忏悔的木鱼能敲出一天云霞?
超脱的翅膀不会让你在山顶兀立
湘妃竹也许在每个月夜淅淅沥沥
斑斑点点的哀怨,浩浩渺渺的空寂
制笺的碓依旧晨晨昏昏起起落落
不眠的只是她求白时汲水的木屐
看山是山,看水依然还是水滴
空山只是哭穷途翻白眼的阮籍
吾犹昔人,然而并非昔人也
我终于知道《广陵散》何以又名《何必》
毫无疑问此时,《落叶集》早已完成。大声讲“看山是山,看水依然还是水滴”,以及“吾犹昔人,然而并非昔人也”,毫无疑问是宣告,某些重大事件或转变已发生。分开来说,如果我理解不错,则“叶子之死”是陈墨之成人礼。《落叶集》是献诗,是十九岁青年带着豁出去的心理,以文字铸造的《广陵散》。而《空山》的“自我叙述”,落脚到“何必”。
就是说,大拒绝。包括“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忆”。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