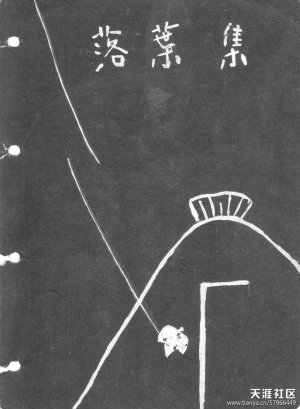七、“新月”是父,“现代”是母
但是,犹有分说:
说《落叶集》1964年底创作可以,未必马上完成吧?说1968年“重新统一”誊钞是真的,说誊钞过程中没有修改、没有调整,不一定吧?如果允许借用一个“版本”的概念,则我以为,假如确实有个完成了的1964、1964年“版”的话,我们永远见不到了;现在见到的,只是1968、1969年“修订版”。
下面两节,属于我的看见。不一定是事实,不指望“确认”。
据我了解,陈墨是那种“郊寒岛瘦”路线,推崇“三年得两句,捻断数根须”的唯美主义者。因此之故,《落叶集》三十六篇,可能有个反复推敲的过程。试举一例:《火化》中“朋友不由分说/把我的文字塞进/灶烘 火化”的“今典”,发生在什么时候?
陈墨1997年5月《“天才”话——怀念诗友白水》一文回忆:
那时,因我的几个文学好朋友都离开了成都(邓垦去荥经当道班工,徐坯去会东当炊事员,明辉去云南修路),唯有寡言的张基又住在城北,而叶子老师又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同季康常在一起,唱外国歌,读外国小说,“绞得很粘”。
询问了他的老友,可以确定的是:邓垦去荥经为1965年3月,徐坯去会东为1965年5月,则“朋友不由分说”大概率发生在1965年5月后。此事既然入诗,说明那时还在写作中——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诗集主体工程已“竣工”,这一桩“今典”是1968、1969年修订时加进去的。再看另一个,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修订”——《无父母》一诗:
“新月”是父
“现代”是母
父亲在雷锋塔下
母亲流放到西伯利亚
超载的雪花
纷落
迷失在这儿
这儿的每条江
都叫
“延河”
此诗出现《落叶集》中,让我眼前一亮。作为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人,知道从五十年代初起,新月、现代诗派就被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派”。1957年高教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直指“新月派和现代派是革命诗歌发展中的两股逆流”。直到“新时期”开始后好几年的1983年8月,才有唐弢撰写文章,提出从文学角度分析,“新月派”也有些好东西,值得肯定;对“现代”派本身也要有分析(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然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本六十年代的诗集,六十年代的地下诗集中有此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放言无忌”……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要慢慢读,一步一步确认,“诳语盘空时代暗有蛙声醒堤……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一步一步确认,那“登髙何必,埋名江湖,野草苍苍”的诗江湖就在这儿。既然是茫茫苍苍的江湖,就未必轻易以哪条江、哪条河自居——据我所知,以“野草派”为“锦江派”,是后来加入的无慧,在2000年后提出来的(《草堂三咏及其它》)……可是显然,它知道自己的命运、遭际,也知道自己所为何来。从“史”的眼光看,此一“寻根”非同小可。毕竟过来的人都知道,“延河”意味着什么——早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所作《新的人民的文艺》(发表于《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创刊号)工作报告中,提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从此,一条名叫“延河”的地方河上升为全国的“母亲河”。现在研究人员辨认,那是“党的文学”: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学观念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 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我认为,在意识形态话语层面, 无论是“工农兵”还是更为抽象的“人民群众”,只是让“党的文艺”或“党的文学”观得以合法性存在的一种修辞策略而已。
(袁盛勇:《“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03期)
官方也没讲,不让别河流。过来的人知道,究竟咋回事。《残萤集》小诗写:
命中注定既是看客/那就看古代的百花/外国的百花/因为这儿的“齐放”/太假
还有《叶子老师教我象征主义诗歌》之四,《凡情常理之颠覆(采和)》一诗云:
百花齐放,在你的竹篮而不是人间,
天真烂漫,一切苦难都不能掩埋你的光鲜。
你的笑容就是最美的醇酒啊,
但饮你的人又总在边沿的边边。
你已经百多岁了,却童颜憨憨,
你的锄头闪光,却敌不过锈镰弯弯。
你打着一只共和的赤脚,
另一只却穿着朝廷的权阉。
哦,原来你就是政清人和的标杆,
一顶理想主义游戏的桂冠。
可惜花儿各自依自己的季节开放,
空把那花蝴蝶望眼欲穿。
现在的问题是:远在文革之前的1964年,年轻的“苦力诗人”陈墨就有了“新月是父、现代是母”的认识吗?——不是不相信,只是觉得“兹事甚大”,有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陈墨写于“鸡年隆冬”,就是1993年的《野草诗选》序云:
1963年初冬,通过学友徐坯的介绍,认识了七中才子邓垦(时以雪梦为其笔名)。……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徐志摩、戴望舒等的作品;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学写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8年冬,我开始着手编《中国新诗大概选》,于1969年夏编成《1918一1928第一分册》。在此期间,深感在新诗的历史上,创立“派别”的重要;尤其是当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而相互影响,使之爱好与创作出现同一趋向时。为了固化这种相互影响,为了使探索成为凝聚力,也为了让我梦寐以求的“派别”得以在形式上成为可能,所以,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梦兄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了一本《空山诗选》。
对照邓垦《〈空山诗选〉始末》回忆,此“同一趋向”几乎呼之欲出: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时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东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天黄昏。那天,我和陈墨从上午抄写到下午,黄昏时约出去散散步。我俩沿府青路的法国梧桐林荫道漫步到刃具厂,又从刃具厂漫步到40信箱。夕阳西下,我俩一路上边走边谈“新月派”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现代派”的成就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落叶集》等“见天”后,陈墨《关于“黑色写作”——〈我早期的六个诗集〉后记》一文中之谈论:
……在资源主要靠手抄本传阅的年代,我对象征主义诗的偏爱并未影响到我身邉的诗友们。我要树“诗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于早期新月传统的“新格律诗”。而这方面,我和我的诗友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从来不跟我身邉的诗友们探讨象征主义诗歌,这方面跟他们交流不起来;“偏爱”得有点孤独,也有点缺乏自信。
尝试言之:此一“诗派”之“同一趋向”,乃“新月派+现代派”。
因此怀疑,《无父母》一诗,非1964年或1965年所写。陈墨那时的写作,是冰心译泰戈尔式(据徐坯讲,曾笔名“佩戈尔”)。《落叶集》的文体、语言,又有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的神韵。而且现有《落叶集》中,除了《无父母》一诗外,也基本上没有“新月是父、现代是母”的表现……面对此“所指”与“能指”的不一致,又该怎么解释?
一个人的性格和语言,会保守过他不同时期的“观点”。《落叶集》时期的语言,是读了1957年《译文》七月号后,“邯郸学步式的盲目模仿”。据研究“陈译”的学者讲:
从她的创作和翻译实践来看,她对“形式”的理解与戴望舒迥异。她重视“形式”的目的是反对诗歌“散文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但不意味着对格律诗情有独钟。相反,她敢于突破形式的限制,把《恶之花》译成了自由诗。……陈译不但没有保留原诗的押韵模式,而且没有设置明显的韵脚。但陈敬容自小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古典诗歌熏陶,对韵律和节奏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感觉,这在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宽泛的平仄和有意无意的韵脚,使她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似有若无的音乐感。
(杨玉平《从“形式”到“质地”——对〈恶之花〉翻译的思考》,《法国研究》2014年03期)
看来《落叶集》的语体,其来有自。
再看陈墨的心性及趣味,有他下乡后,写给邓垦的《解语花•记梦兄小诗》为证:
岩壑未醒,松风又瘦,四野碧无情。色衰香凝。恰如是,月夜环佩归魂。路通红尘,听秋声,翻作泥泞。拭冷泪,目送飞鸿,一意独孤行。 休怪平生耕耘,有归去来辞,泽畔行吟。乐道安贫。春未老,青山无语向人。竹篱柴门。风雨过,柳暗花明。且前往,穷山深际,寒星似鬼磷。
如拉通来看,从《落叶集》和《灯花集》、《残萤集》中一些“早期更早”的诗作中,看不出多少“新月派”的表现。上一节引了他文革中作品,如未收入《乌夜啼》,而是归入《灯花集》的《超声波》、《无人在听》等,也还是有着我们熟悉的“陈译波德莱尔”灵光乍现、浑然天成之妙。或可说,这是其“在流派之外”的“本色”?……我能否因而推断,《无父母》所表达的,表面上是“我”的,其实是“我们”的主张——就是其中有,诗友们在高音喇叭吼叫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的影子?
从认知角度分析:“在资源主要靠手抄本传阅的”摸索中,一个人说出“××是父,××是母”这种“认宗”的话,几乎不可能——如我们回到1964年底“现场”,面对“叶落了/你走了”,会更多“吾父何在”的迷茫、或眉间尺式的哀伤,怎会有如此坚定、从容、有主见?——即使有,我想那更多是做人的、而非诗学的,两者不是一回事。要有明确的诗学主张,若脱离“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时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而仅靠对“超载的雪花纷落”的逆反,恐怕做不到吧?综合考虑,我以为《无父母》像是1968年、1969年的。
再一次要说,诗人从根本上讲,是“文明的孩子”。从“互文”的角度讲,我以为“无父母”不可能是事实,而有着民国时期周作人译波德莱尔《外方人》的影子:
外方人
告诉我,你谜样的人,你最爱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么?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
那么你的朋友呢?
“你用这一个字,直到现在,在我是无意义。”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它所在的纬度。”
那么美呢?
“我很愿爱她,那不死的女神——!”
黄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们憎恨你们的神。”
那么,奇异的游子,你爱什么呢?
“我爱那云,——那过去的云,——那边,那神异的云。”
——摘自《陀螺》(1925年新潮社)
再看另一“意象”——1964年的陈墨,是“紧张惊警”的,噩梦看不到尽头:
嫌苦难的滋味/不浓 死心塌地地/怀疑女人的智商/生理和心理/在康桥永别/你拒絶接受/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 (《干凈》)
那时的叶子和他,拒绝接受整个世界。而非徐志摩一般,仅“作别西天的云彩”。即使用了“康桥”意象,与之搭配的却是“永别”。永别与再别,岂可同日而语?然后进一步讲,长歌当哭的《落叶集》时期,他可能不心仪徐志摩,也送不出“月下雷峰塔影”: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当然现在是“黄金时代”。在“巴不得人不吃不屙不睡”的恶补中,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该读的他都读了。他会带着新的眼光、新的认识修改、完善旧作。可是基础性的东西,就不可能动摇。见到徐志摩“雷峰塔影”,他也不会有动于衷——无须多申说吧?
还有一个例子,好像也能表明,现有《落叶集》有1968、1969的印记:
鞭痕结痂/灿若桃花/这段歳月到此为止/音符凝固在夜空/卦者的羊角/瞬间落地/生命更为抽象/向秀不在旷野/叮叮当当/他锤打着一块/红红的铁 (《逝世》)
——明写向秀,实写嵇康。而且完全属于,“创造性的背离”。如此成熟的“构思”,能让我确信是1964年,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所写?何况多年以后,其《正话与反话》写:
文革武斗期间,我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结识了书友冯里(后来成为诗友之一)。1968年某天,他突然给我一本196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说:“里面有一篇陈翔鹤的中篇小说 《广陵散》,写得相当好,相当感人,你看看!”
这篇写嵇康的小说我是边流泪,边想,边看完的。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篇历史小说是最“刻骨铭心”心的。可以说它改变我的人生——我从此十分崇拜嵇康,他成为我心灵的“人格偶像”。并且发誓要把嵇康他们“竹林七贤”的故事写一个长篇小说。说来也许无人能信,我1970年之所以毅然下乡,其中就有想在政治干扰相对较小的偏远的农村创作我的《广陵散》这条缘故。
(《正话与反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再正反》)
此话有分量:“从此十分崇拜嵇康”。那么此前呢?该知道嵇康,晓得《广陵散》。因为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意味深长——“终于知道《广陵散》何以又名《何必》”(当然也有可能:此语也有1968年“修订”的痕迹)……尽管如此,读陈翔鹤“刻骨铭心”,是不可忽视的。但凡懂点中国文化的人,其实无须多说。“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再回头看《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不妨说,六十年代的陈翔鹤不仅在写陶渊明和嵇康而且也在写他自己。”(郭冰茹:《陈翔鹤小说论》,《文学评论》2007年01期)。
但凡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演进过程,就晓得陈翔鹤《广陵散》等,是六十年代初“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在一个文学体制极其严厉,文学环境高度一体化的年代里,这种独特的个人声音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是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人格的折射, 是对体制铁幕的反动。”(朱美禄《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喜欢某种情调的人,会对小说中涉及的“商音”产生兴趣,领会“其特点正在于表达那种肃杀哀怨、悲痛惨切的情调!”(陈翔鹤《广陵散》);内心有块垒的人,更容易对《陶渊明写〈挽歌〉》中的话产生共鸣:
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总觉得,《落叶集》中——比如《干凈》一诗,有这些议论的影子。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