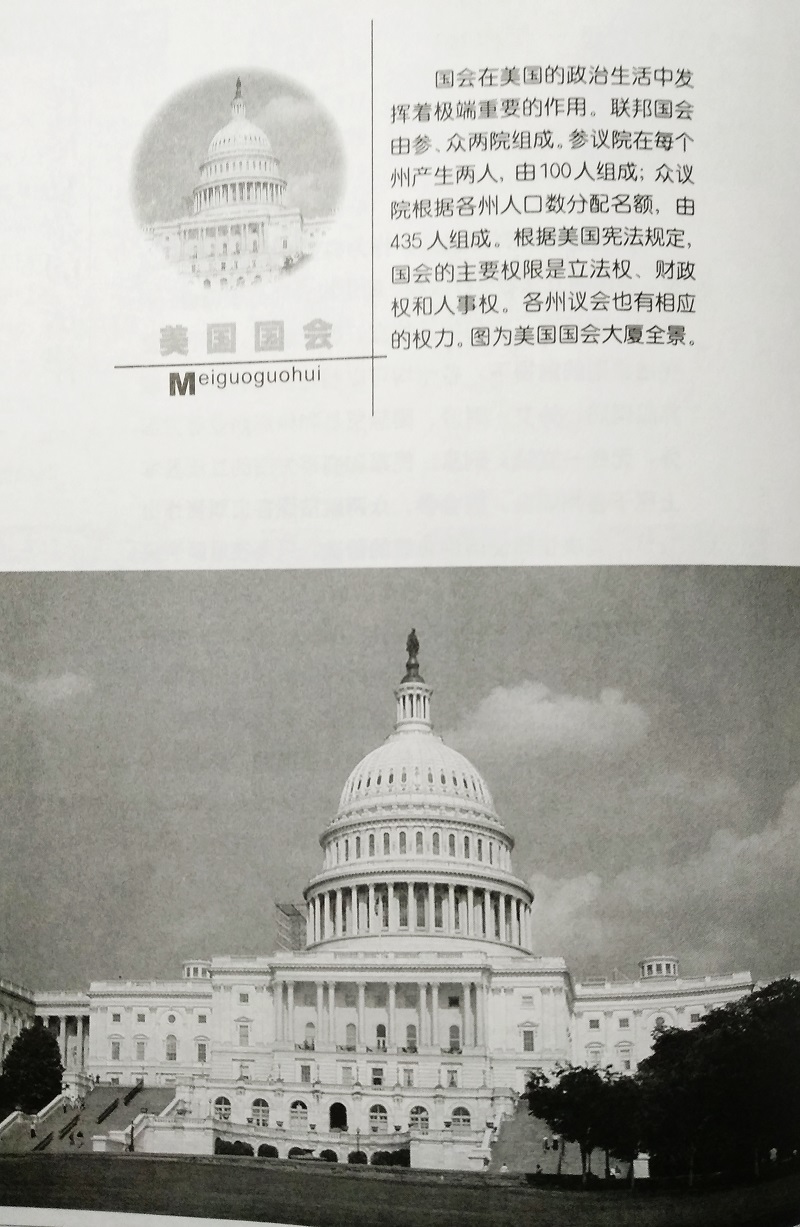氢弹的秘密(2)
请大家接着上文继续看下文:
这案件一旦归到《原子能条例》下面,就成了一个暗箱。瓦德。莫兰的辩护人在保密的挡箭牌下,不能知道有关此案的几乎一切信息。被告也无法回答前面一大堆问题。任何试图被引进法庭的证据,都有一个保密的陷阱等在那里。例如,瓦德。莫兰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料来自公开的读物,他拿来一本自己的大学教科书,政府官员说,他在教科书上画的线必须擦掉才可以拿出来。他又拿出一些杂志文章,一个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拿出来的东西都被司法部宣称是秘密的:指出文章哪一部分是秘密的行为本身,是秘密的;争论它是不是秘密的争论,是秘密的;法庭对于这些秘密的看法,也是秘密的。要知道,新闻检查制度这个字眼在美国分量是很重的,或者说,是很难听的。所以当《进步》杂志社在法庭上指责美国政府是新闻预禁时,政府的一些人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律师说这不是“检查”,这只能称作是“删除”。《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对此气愤地说,你就是把它叫作奶油点心我都不在乎,可它还是新闻检查。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该案的法官心情很不轻松。他写道:“如果发出一张初步的强制令,据本庭所知,这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用新闻检查制度禁止新闻出版的第一个实例。这种声名狼藉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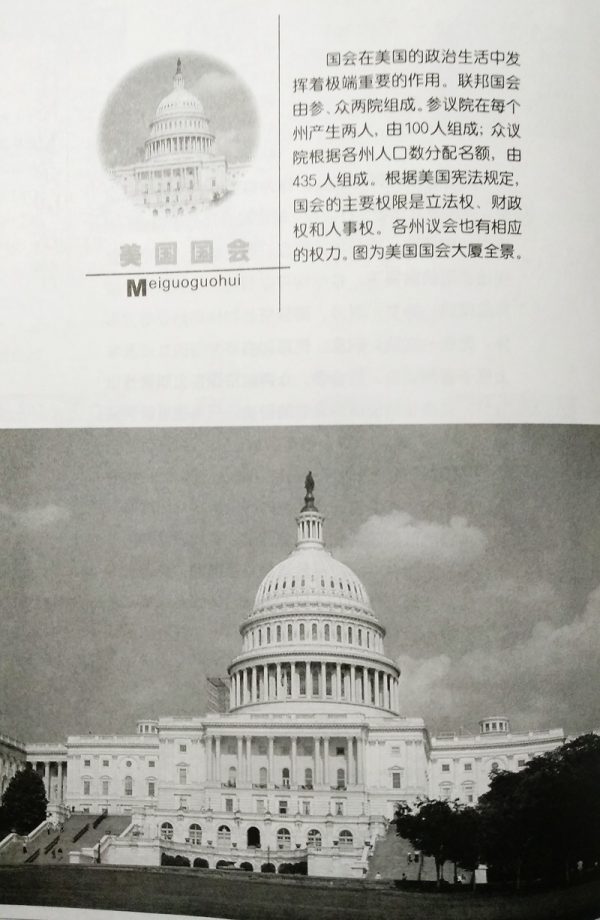 1979年3月26日,法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首先指出,这个案子与“五角大楼文件案”不同,后者是国家行政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阻止新闻发布,而这个案子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原子能条例》授权禁止。法官认为,这个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下的条例是清楚的,范围是适度的。最后,他主要是注意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风险。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勿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他写道,“如果作出一个反对美国的裁定,这一错误将为我们所有的人铺平通向热核毁灭的道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生存的权利受到威胁,(所以)出版的权利变得可以商榷”。最终,法官“遗憾”地签下了这份预禁令。
1979年3月26日,法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首先指出,这个案子与“五角大楼文件案”不同,后者是国家行政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阻止新闻发布,而这个案子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原子能条例》授权禁止。法官认为,这个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下的条例是清楚的,范围是适度的。最后,他主要是注意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风险。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勿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他写道,“如果作出一个反对美国的裁定,这一错误将为我们所有的人铺平通向热核毁灭的道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生存的权利受到威胁,(所以)出版的权利变得可以商榷”。最终,法官“遗憾”地签下了这份预禁令。
我想,这个法官的判决是能令人理解的,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但是这个案子也暴露出许多令人琢磨的问题。例如,在案子中出现的“暗箱问题”,就是很值得深思的。当一名被告所被指控的一切都变成了“秘密”,甚至连他的律师、法官、陪审团都不能清楚地了解与案情有关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可能进行一场“公平的审判”,被告的权利还怎么可能得到保护呢?
公允地说,法官的判决确实是“依法办案”,而且从大道理上说,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理应得到保障。所以,言论自由一旦对此造成威胁,当然应该进行适当限制。但问题是任何法律都有缺陷,像上述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保密”,就不由得让人产生强势力量强词夺理,“暗箱”操作之嫌。这种情况在许多官与民的司法诉讼中都有所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之中也曾有所闻。那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弱势群体又该怎么办呢?而作为强势力量又该怎么对待弱势群体的“依法抗争”呢?这个案子以后的进程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难道安全与自由就不能并行不悖吗?
大家接着看吧。
美国的“反恐怖法”草案当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怎么回事?立法反对恐怖活动当然很有必要,问题是具体的做法,也就是“反恐怖”应该怎么“反”法。当“反恐怖法”草案在国会参议院通以后,人们在电视里看到一场专题辩论节目。它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和民间社团组织组成,在一起讨论有关“反恐怖法”草案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也谈到前面所提到的审判中的“暗箱”问题。辩论中,作为政府一方,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都对他们在工作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发出抱怨。他们坚持说“反恐怖法”草案所放松的限制,对于美国的反恐怖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作为民权组织等属于“美国人民”的另一方,却对“反恐怖法”草案中有可能发展成侵犯公民权利的部分提出严重质疑。例如,该草案有条例规定,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经费,就可以对他进行起诉。对此,民权组织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宣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中,有著名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民权组织指出,哈马斯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组织。在美国,完全有可能有一些公民只是在宗教上认同这个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因为出于宗教的原因,向属于哈马斯组织的医院捐了十块钱而受到“反恐怖法”的起诉,并且有可能因此而被判刑,这显然是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在“反恐怖法”草案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使人们感到吃惊的,并不是一个“反恐怖法”草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而是美国人民对于所有的立法和案例所涉及到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所持有的认真态度,惊叹他们的持久的顽强和理性的思索。在这次辩论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还提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他说,在俄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提醒国会过度反应并不是无稽之谈。当年珍珠港遭日军偷袭后,美国政府担心日裔移民中会有人向其母国提供情报,结果,由罗斯福总统下令,把美国西海岸12万日裔移民,全部迁移到落矶山脉东部的十个临时居住地。12万人一夜之间全部失去了自由。在这一天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支持美国军队而努力工作。在被集中圈住的四年当中,他们当中还有人收到为美国战斗的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今天,当我和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无法想像的错误。
“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案的主审法官伊藤,其父母就是当年12万日裔人中的两人。伊藤法官谈起美国的这段历史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这就是美国人今天对待任何一个民权案件的基本态度。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么,它也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一个公民并不相识,甚至也许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女作家刘瑜在《他也可以是我》一文中用浅显的道理指出: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剝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有五十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上述文字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普遍现象:当好人变成“坏人”之后,才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中国人啊,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让我们继续揭示“氢弹的秘密”吧。
这个案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这只是地方法院的判决。《进步》杂志马上提出上诉,发誓要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进步》杂志上诉只有几个星期,政府的阵线就开始溃散了。1979年5月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位调查员跑到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公共图书馆,从目录里查询有关“武器”的一栏。他查找到一份文件,发现这文件里已经包含了瓦德。莫兰文章里的大部分所谓“秘密”的“限定资料”。一年前,图书馆清理资料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地把这份应该是保密的资料放到了公开的书架上,也是非常凑巧地正好让这个调查员给翻到了。
大家还记得,《原子能条例》里规定,“限定资料”里不能包括已经解密的资料。因此,由于这个调查员的发现,司法部的不少人都觉得撤回起诉算了。但是,情报部门却照会司法部门说,尽管图书馆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些资料还没有被那些“敏感”的外国政府弄到手。因此,阻止莫兰的文章发表,仍然是必要的。
虽然这篇文章由于官司尚在进行之中,并没有与读者见面,但是这场官司本身是无法保密的。如此一个大案,使新闻界无比激动,尤其这牵扯到他们本身的权利,知识界会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场划时代的辩论。全美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著有关的报道。有的记者有意地去重复“莫兰历程”。他们运用他们可以利用的公共图书馆之类的途径,企图去复制同样的工作,有人得到的结果与莫兰十分相近。也有一些记者,他们的本意是了解《进步》案的全过程,可是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无意中就频频闯入了氢弹的“秘密”领地,糊里糊涂地就掌握了一些氢弹“秘密”。
这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叫恰克。汉森的怪人。你可以说他是“原子能爱好者”,也可以说他是“氢弹迷”。他发起了一个反对政府起诉《进步》杂志的运动。他不但使抗议信像雪花一样铺天盖地飞向国会议员和美国能源部,他还发起了一场“氢弹设计竞赛”。谁的设计能第一个让能源部定为必须保密,谁就是这个竞赛的优胜者。当年秋天,他给一个参议员寄了一封信,里面描绘了他自己版本的氢弹秘密的轮廓。他搞出来的东西和莫兰的很接近。他还把这封信寄往全国各地的一些报社。
9月16日,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很小的报纸,发表了汉森的那封信。第二天,政府就对《进步》杂志撤诉了。司法部长承认起诉已经毫无意义,汉森的信已经发表,有关报道已经满世界都是了,再去阻止另一家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呢?
1979年11月号《进步》杂志以通栏标题《氢弹秘密:我们怎么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全文刊登了莫兰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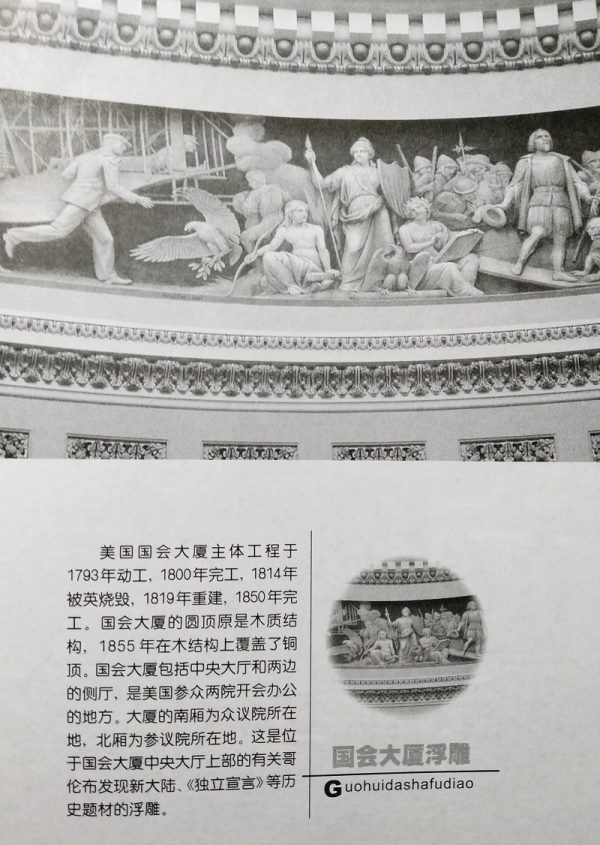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结果。可以说,它说明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了很多问题。人们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撇开这文章该不该发表的问题,只谈操作的话,在美国,阻止文章发表的操作比在任何国家都难。就这个案子,大家都看到了,就算那个实验室的图书馆没有犯错误,也会有人出来向这个案子挑战,不出那个汉森,也会出个汤姆或者约翰。更何况由于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禁止,等美国政府看到时,许多老百姓已经看到了。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发表了,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戏剧化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一种恐惧。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讨论核武器。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扰也不愿意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因为,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结果。可以说,它说明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了很多问题。人们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撇开这文章该不该发表的问题,只谈操作的话,在美国,阻止文章发表的操作比在任何国家都难。就这个案子,大家都看到了,就算那个实验室的图书馆没有犯错误,也会有人出来向这个案子挑战,不出那个汉森,也会出个汤姆或者约翰。更何况由于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禁止,等美国政府看到时,许多老百姓已经看到了。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发表了,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戏剧化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一种恐惧。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讨论核武器。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扰也不愿意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因为,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案子撤消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仍然认为,这些资料的发表,对于美国是有害的。对其是否真的有害和可能的伤害程度,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而权威的判断。人们仍然要问:这些资料的发表,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类似问题,也许会涉及更严重的国家安全,那时又该怎么办?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安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在这个《进步》杂志案子里,美国政府也是相信国家利益真的有可能受到伤害,发急了才出此下策去起诉杂志,因为政府官员是最不愿去向新闻界挑战的。几个部长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下赌注。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个案子的结果是,美国人民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很可能确实支付了国家利益的代价。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应该知道所支付的国家利益并不是政府的,而是整个国家,也就是全体美国人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国家利益”这个震慑力量就让步的话,早就没有美国的新闻自由了。因为,新闻自由所遇到的真正困扰总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检查制度和禁止发行之类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政府打算以预检预禁这样的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或者,政府不希望公布不利于它的材料的时候,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借口就是“国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丑闻,如果要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材料的公布,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定,说这是一种国家利益,也能说得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每一个案例来看,力量对比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不仅仅是一个报社或杂志社与美国政府的人力财力和掌握的手段无法匹敌,而且发表一篇文章的分量和国家利益的分量也根本无法相比。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有一天能够炸开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所以,这不仅仅是美国新闻界的恐惧,这是美国人民的恐惧。以上所看,这种恐惧甚至压倒了他们对于热核武器威胁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美国人民现在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而且自由自在。他们有数量比例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关心着各种只有在衣食无忧、思想无拘无束时才会关心的问题。大家看,连“核武器”都会冒出一大群“业余专家”和“迷”来,他们应该都是吃饱喝足了的。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正常运作,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舆论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运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种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就是二百多年来,美国民众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看了以上的报道,总觉得美国老百姓喜欢与政府作对,而政府总是忍气吞声甘受欺负,不敢对民众玩横的。像这种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如果放在东方某些国家,谁敢捋这虎须呀?也就是在美国,讲人权讲法治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了。有人说美国在世界上搞霸权,到处侵略干涉,欺负弱小国家,如狼似虎;但奇怪的是,美国政府对待美国老百姓却温顺如猫,任民众攻击谩骂,说三道四,而不敢造次。这就和Z国的表现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原因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权力是美国人民授予的,他不讨好美国人民怎么能上台呢?至于美国在国外搞没搞霸凌,你先去问美国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是否受到美国的欺负了?如果没有,美国为啥放着身边的软柿子不捏,而要万里迢迢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60年了,美帝连鼻子底下的社会主义的古巴都亡不了,还能亡你十多亿人的泱泱大国?至于苏联东欧,美帝根本就没想到它们会在几年时间内就解体消亡了。
最后,作者写道:“那么,你一定要问了,美国政府还怎么保住国家秘密呢?只有他们自己看牢点,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唯一办法。”
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封口呀!
荀路201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