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素子(采写) 周有光( 受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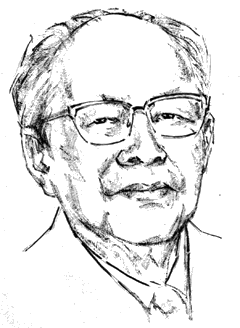
周有光 1906.1.13~2017.1.14
© 采写:周素子
© 受访:周有光
周素子:你这个年龄在北京排老几?
周有光:东城区调查人口说,我是东城区年龄最大的(转载者注:周老当时是106岁)。北京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惜早年被破坏太多。假如按照梁思成的计划,老的北京城保留下来,加一加工,东面造一个城,西面造一个城,不要破坏原来的。破坏了原来的,这是很可惜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周素子:你和沈从文是连襟,还有没有跟沈从文的老照片?
周有光:老照片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不要的,都被送到宁夏,去劳动改造,叫作“五七干校”。等到回来呢,家里住的是造反派,他们搬走的时候,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个废纸片都没有了。本来我家里照片多得不得了,现在一张都没有了。
我们家三次被扫地出门。什么叫扫地出门呢?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搞光了。第一次要讲我的曾祖父,他是反革命分子,清朝他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攻破了常州城后,他就投水而死,清朝封了他一个官。皇帝每年要给我们很多钱,恩赏我曾祖父的。
第二次,抗日战争我们逃到四川。苏州的老家由一个老家丁照看,他管得很好。我们本来以为最多三年要回来的,结果隔了八年才回来。等我们回来,老家丁已经不认得我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是第二次扫地出门。
第三次扫地出门就是“五七干校”下放,“反右”嘛。我还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是上海解放才从国外回来的,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我是搞经济学的。一直到1955年年底,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来参加。会议结束以后,中央把我留在北京,在一个新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不行,我的语言文字学是自修的,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复旦大学校长劝我改行,说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要建设新中国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民都没有文化。那个时候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文盲,复旦的校长也劝我,我就到北京来了,从此改行不搞经济学了。我是1955年年底来的,1956年没问题,1957年就“反右”,“反右”不得了,上海两种人是重点,第一是资本家,一个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第二个重点就是经济学家,上海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我的好朋友自杀了,我在复旦的学生、好多博士生都受牵连,有一个博士生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都不知道,那三年时间是不能随便通信的。但我在北京改了行,不算我的账了,上海好多经济学家没有讲错一句话,可是也变成大右派,因为你当教授不可能不写文章。你一篇文章,就是二十年监牢。所以我逃过了一个反右,四川话里这叫“命大”。
周素子:你如何保持这样清晰的记忆?你的阅读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每天都读书。我是85岁才离开办公室,在家里以后就不做学术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杂文,主要是看世界历史还有文化,中国人不大懂文化学。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了不起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文化的中心跑到中国来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就根据国际文化学者的研究写了篇文章。杨振宁他搞物理学的嘛,他这个人人缘不好,在美国大家都讨厌他,他觉得在美国没有趣味就回来了,先到香港,香港请他演讲,他不讲物理学,他讲文化、讲语言文字,讲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一个大笑话!我百岁以后衰老很迅速,首先是耳朵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不过理解力还没有衰老。理解力要衰老那就不行了。
周素子:你对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同源词研究》有什么评价?
周有光:陈独秀在语言学文字学上,他是的确外行,这方面胡适懂。
周素子:陈独秀搞学问的话,地位也会很高的。
周有光:对,他如果搞学问就好了。
周素子:你最难忘的朋友是谁?
周有光:最难忘的朋友是胡适,他是我的丈人的朋友。其实他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认识他。我的老伴,还有老伴的妹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都在胡适的学校里面听过他的课。其他的朋友想不起来,朋友太多了。现在看起来,胡适讲的话都是对的,他没有胡说八道。中国,今天最重要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哪里来的,胡适讲的,是胡适讲出来的,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周素子:当时你也很激动?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有光:是很激动!因为我们经过抗战,那个时候我们青年都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专制,国民党专制都是从苏联来的,也是学苏联的。苏联那个时候很厉害,它一手抓国民党,一手抓共产党,很厉害的,害了我们。
周素子:你怎么评价季羡林?
周有光:季羡林应当说跟我很熟的,他也是政协委员,在政协我们常常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他在外国读了八年书,在德国学梵文。外国大学都有梵文这一课,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什么用处呢?学佛教文化,学了梵文你才能够看佛教的材料嘛。他的梵文是挺好的,可是回到中国来没有用处。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的,中国人研究佛教不通过梵文而通过中文,什么道理呢?因为从唐代开始,中国人把佛教的经典都翻成中文。所以许多的佛教经典中文有,印度文都没有了,印度是失传了,中文里面倒有。所以你真正要研究佛教呢,要用中文典籍来研究佛教。人家把他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笑)
周素子:你是老经济学家了,你是如何看中国经济腾飞的?
周有光:今天许多人讲中国好起来了,经济好起来了,这是完全错误的,GDP不能讲总数的嘛。
周素子:你现在上网吗?
周有光:上网。我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机在那个房间,我平时写文章就用这个计算机。
周素子:中国买美国债券对吗?
周有光:对的!发行要有准备,发行准备用什么东西呢?从前最好是黄金,可是黄金的问题就大了,第一是不方便,第二是黄金的价值不能跟着需要变化,所以黄金可以作发行的准备,但只能作一小部分。发行你要准备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刻卖掉变成钱。所以美元、美国公债,最合算,也最靠得住。因为美国公债或者美元立刻可以变成你需要的货币。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全世界都是买公债,其他东西都次要的,因为其他东西没有那么大的量,没有一种东西可以随时卖出去,立刻变钱的,就只有美元是最方便的。这是一个知识问题,你要反对你自己倒霉。这个美帝国主义是很厉害的!债券你可以立刻变成美元,从美元的角度来看债券不会缩水的,而且它的利息也是比较高。美元是会缩水,但也不敢缩得很多,缩得太多他自己不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美元是全世界通用的。
周素子:你跟外国亲戚们联系多吗?
周有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外国好多趟。讲到去外国的事,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刚刚想起来。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没什么事情做,但是我很高兴,就在家里面,把从前做的研究写成一本一本书。有一天,是1979年的冬天,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个礼拜你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的衣服都破光了。他说衣服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做最好的,但回来后,都交给公家。好,要走了,派了两个人送我到飞机场,送到飞机旁边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不给你美元了。又说你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外国去的。我把皮夹子交给他,我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人家就问我,你没有一分美元没有一分人民币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人已经到飞机旁边了,跨一步就进飞机了,你不进也得进嘛。不过我一点也不心慌,要是真的有点问题,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嘛。
—— 原载: 《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