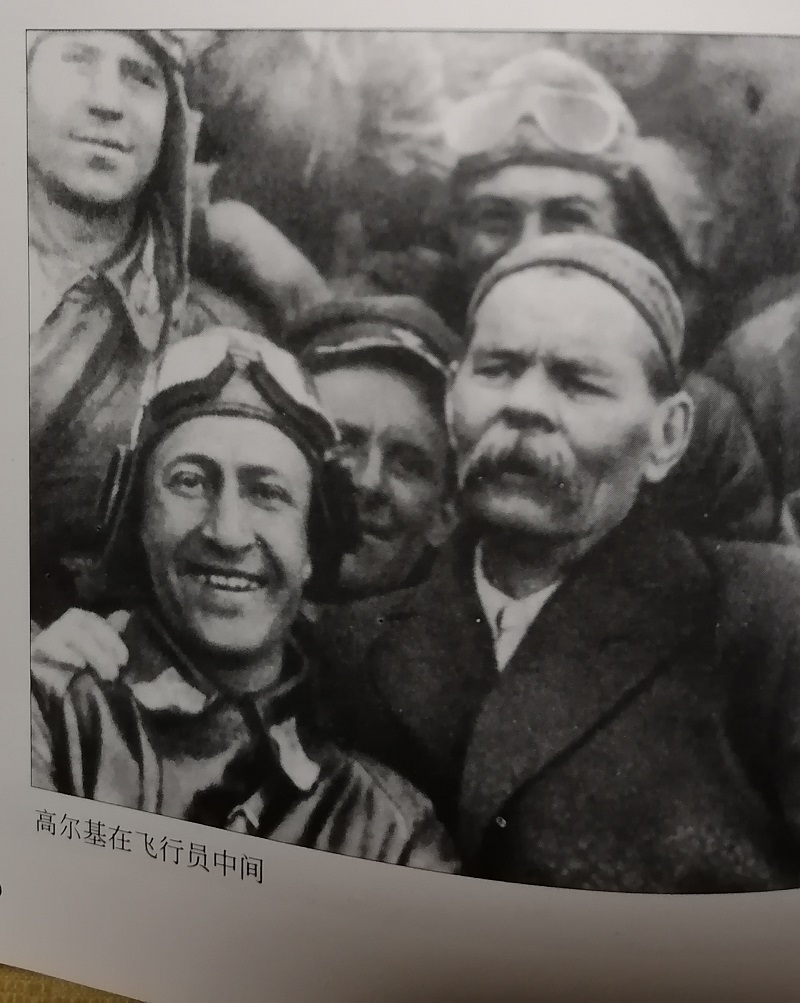“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八)
1918年6月6日,正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大地如火如荼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发表了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将他对时下革命者的剖析得令人觉得真是入木三分。现将他对 “永远的革命者” 的表述转录如下:
在观察当今的革命者们的工作时,我们会清楚地分辨出两种类型的革命者: 一类可称作永远的革命者,另一类则是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
在第一类革命者身上体现着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他们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全部丰富思想的继承者,这些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理智中,而且表现在他们的感情中,甚至还表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类革命者是无穷无尽的活生生思想的链条上最活跃、最敏感的一个环节,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他们受自己全部的感情和观点的限定,一辈子都是不满足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并相信,人类有永远不断用好的事物创造更好的事物的力量。
这类革命者热爱永葆青春的真理,但是这种爱不只是感情上和形式上的,他们绝不会用拳头把真理强行填入那些被过去僵死的现实所奴役或不可救药地钟情于腐朽事物的人的心里和头脑里。对于这类革命者来说,人是一种永远在创造新的感受、思想、观念、事物和新的生活形式的、生动而活泼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这类革命者想使存在于地球上所有人头脑中的全世界的智慧都活跃起来,充滿灵感。但是,在追求他们这唯一的、真正革命的目标时,他们并不善于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强迫人的方法,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必要情况下才怀着本能的厌恶感采取强制措施。
这类革命者深深懂得,正如一位著名的俄国思想家所言,“历史的可怕性和历史的巨大不幸,在于人总是受到残忍的欺凌。” 的确,人受着大自然的欺凌,大自然在创造了人之后,就把人像野兽一样扔进了荒凉的世界里,使其置身于各种野兽之中,为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和其它一切野兽相同的条件; 人还受到各种神祇的欺凌,而这些神祇本是人出于对自然力的恐惧或欣喜,过于匆忙地、不高明地、过于 “按自己的面貌” 制造出来的; 人还受到那些狡诈的或者强大的同类无休止的欺凌,最可悲的是,人还受着他自己的欺凌,受着他自己在古老的野兽和新人之间的摇摆的欺凌。
但是永远的革命者从不对别人记私仇,他总是善于站得高于自我,善于克服自身那种因所受的磨难和痛苦而报复别人的卑微、恶毒的愿望。
这类革命者的理想是让人成为身强力壮的、美丽的兽,但是这种形体的美同精神的巨大力量及精神的美处于完全的和谐之中。所谓人性的,就是精神的,就是理智创造的东西,由理智又产生了科学和艺术,产生了被越来越多的人朦胧感觉到的人们的目的与利益是统一的这一意识。永远的革命者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加深和扩大这一意识,使这种意识能够把握全人类,摧毁把人们分割成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种种障碍,并在世界上创造一个由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成了主人的劳动者在为自己创造着一切生活的瑰宝和欢乐。
对于永远的革命者来说,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善仅仅是人类通向理想境界的无尽的阶梯上的一级台阶。他们不会忘记,历史进程的意义就在于此,而他们个人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必然之一。
永远的革命者是不断地刺激人类的头脑与神经增长的酵母; 这些永远的革命者或者是破除在他们以前创造的真理并创造新的真理的英才,或者是安详地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的,燃烧着悄无声息的、有时甚至是无形的火,照亮通往未来之路的谦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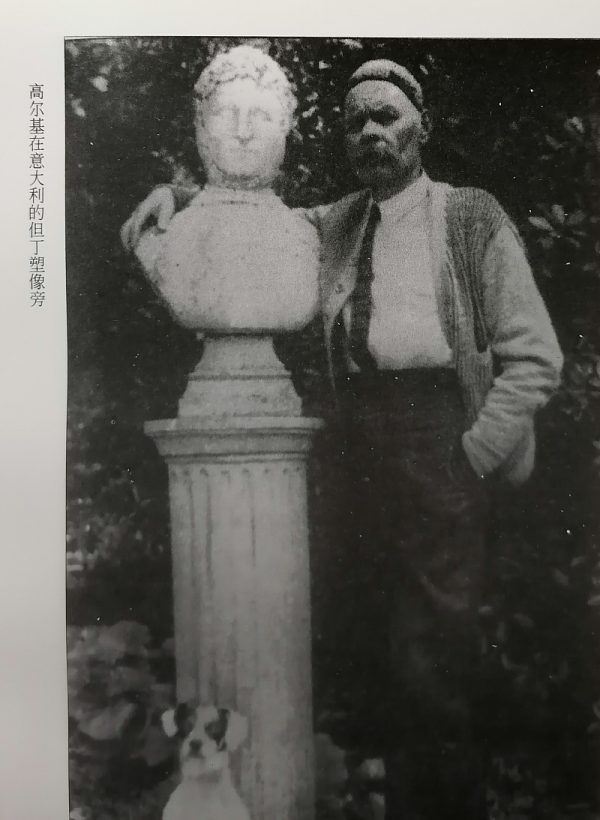 在高尔基的心目中,真正的永远的革命者不仅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而且还是丹柯式的英勇无畏的献身者。这些革命者心怀宽广,具备理智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具有 “善于站得高于自我,善于克服自身那种因所受的磨难与痛苦而报复别人的卑微、恶毒的愿望” 之品质。
在高尔基的心目中,真正的永远的革命者不仅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而且还是丹柯式的英勇无畏的献身者。这些革命者心怀宽广,具备理智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具有 “善于站得高于自我,善于克服自身那种因所受的磨难与痛苦而报复别人的卑微、恶毒的愿望” 之品质。
而以上面的标准来衡量活动在当时俄国大地上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显然是不够格的。这里,高尔基推崇的 “永远的革命者” 只是他心中美好意愿的一点表露。他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不得不借助赞美理想中的革命者来释放心中的块垒。他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中有知识、有道德、有理性的先进分子。这种愿望在他1918年5月16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可见端倪:
应该记住,一切都在于我们,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我们在创造一切事实、一切现象。我们能否在自己身上培养起对我们本质的兽性的一半,对我们心理中那些使我们互相粗野和残酷相待的动物成分的由衷厌恶?我们能否自己和互相培养起对痛苦、罪行,对谎言、残酷和那厚厚地积在我们每一个人一一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多高的文化一一心灵上的全部卑鄙的尘垢的厌恶?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应该学会仇恨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灭痛苦。应该教会人哪怕稍微爱人现在的样子,也应该热爱人将来的样子。
……
工人不应该忘掉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成分,他只有在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对劳动者们是必需的、有拯救力的,而且还将把所有的阶级、把全人类从患病的、撒谎成性的、自我否定的旧文化锈迹斑的锁链冲解放出来时,才能信心十足地感到自己既是新真理的使徒,又是争取新真理胜利的强大的战士。
特权阶级不接受社会主义,不觉得社会主义中有自由、有美,他们想像不到,社会主义能把个性及其创造活动提高到何等高度。
但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工人多吗?对于工人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只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利己主义之上的经济理论,就像其他社会学说建立在私有者的利己主义之上一样。
在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之中,不应当抛弃对全人类美好事物的追求。
只有在对我们自身的和我们以外的一切残酷的、粗俗的、卑鄙的东西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文化有真正的敏感,对文化有真正的理解。
你们在尝试培养自己的这种厌恶吗?
高尔基正是这样的 “真正的革命者” 一一厌恶假、丑、恶,赞扬真、善、美。俄国作家瓦季姆.巴拉诺夫在《高尔基传一一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一书中,表示他要为高尔基 “剥去各种外衣,塑造历史上真实可信的精神面貌,毫无粉饰的面貌,这就是我的使命。” 他首先指出:“高尔基作为生命的热情赞颂者,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人性,首先是反对置人于死地的那些人。1917至1918年间,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系列文章体现了这种精神。在这些文章中他与已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论战,捍卫俄国文化的巨大价值。”
十月革命后,红色恐怖笼罩了俄罗斯大地,曾有很多不适应急速转变的社会环境的知识分子面临灭顶之灾。高尔基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了许多知识精英,使之免遭赤祸荼毒。巴拉诺夫在书中举例说:
比如说,为争取放行(诗人)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他不知花了多少力气,四处奔走斡旋。结果怎样呢?先是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交涉,打报告给列宁。两个人都同意了。文件转送主管出境事务的明仁斯基(契卡副主席)手上。此人不问青红皂白便命令在国内的某个疗养院为诗人安排较好的条件。……
可是,政治局支持不同意明仁斯基出国的建议并于1921年7月12日通过决议,避而不谈亟待解决的医疗问题,只谈 “改善布洛克的供给状况”。
高尔基愤愤不平,又去找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写了一份详尽的意见,向俄共中央提出异议,其中提到布洛克 “与高尔基一起是我们整个文学的精华和骄傲”。终于拿到了许可证,但又开始拖延办理布洛克夫人的出国手续。高尔基又从彼得格勒致电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会重新请求中央委员会:“专此奉呈高尔基的急电,谈及根据中央委员会决议放行A.布洛克之事,急请……” 等,不一而足,终于下发了布洛克夫人的许可证。但不知谁在莫斯科把申办护照的表格弄丢了一一苏维埃人司空见惯的马虎作风。当另派可信赖的人正准备去莫斯科取护照时,不幸,布洛克于8月7日与世长辞。
夏里亚宾(俄罗斯男高音歌唱家)对高尔基的评价比较公正。1918年,他在一封信中证实:“不知有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才得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是个大好人。” ……
为了帮助人们,他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有一次,来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要求与作家见面。原来她是一个初学写作的诗人,吃奶孩子的母亲。孩子需要牛奶。高尔基当即写了字条,为了有把握办成事情,又补充写了一句,这是他的私生子。自然,他请求对这种有刺激性的事情严守秘密。
感恩戴德的女诗人走了。如果没有高尔基的帮助,她儿子怎么可能在闹饥荒的彼得格勒活下来。可是,许多其他的母亲也纷纷问高尔基提出同样的请求。高尔基为她们的孩子四处奔走的同时,也多次运用了那种计谋。食品分发人员终于支撑不住了,于是宣布无力给高尔基那么多的孩子供应牛奶。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和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的处世之道常常是不合辙的。两人之所以能够在外人面前保持和谐相处的形象,完全是因为各有所需:高尔基以人道为本,力图拯救更多的受难者;列宁以王道为标,企图维持红色的政权。人道的高尔基希望王道的列宁高抬贵手放过白色的知识精英;王道的列宁指望人道的高尔基发挥作用影响更多的民众支持苏维埃。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报道了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歧见与龃龉: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和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的处世之道常常是不合辙的。两人之所以能够在外人面前保持和谐相处的形象,完全是因为各有所需:高尔基以人道为本,力图拯救更多的受难者;列宁以王道为标,企图维持红色的政权。人道的高尔基希望王道的列宁高抬贵手放过白色的知识精英;王道的列宁指望人道的高尔基发挥作用影响更多的民众支持苏维埃。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报道了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歧见与龃龉:
高尔基为之说情的某些 “残存的贵族” 是一些精神贵族,耍笔杆的贵族。其中有一位是历史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他想到芬兰去著书立说。高尔基在列宁面前为他说情,请求准许他出国,于是高尔基就从列宁那里收到一封列宁写给彼得格勒当局的 “特别” 信。但是当高尔基回到彼得格勒后,得知大公已被处以死刑。据著名的孟什维克作家波里斯.尼古拉也夫说,1922年高尔基在柏林时,曾怀疑正是当他的请求在形式上得到列宁的答应时,列宁本人或者是他的一个亲信却下了处死大公的命令。这个怀疑为《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第27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381页)上所复制的一封电报所证实,在这封电报里列宁命令季诺维也夫(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动身要加以阻拦。
高尔基像诉诸终审法院那样诉诸列宁,从而拯救了很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命。而列宁是需要高尔基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的作家的,因为这位作家是来自人民、描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作的。苏维埃政权疏远高尔基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列宁与高尔基在莫斯科继续会晤:高尔基带来了一份有关已经发生的不公平事件的清单,列宁企图 “劝导高尔基走正道儿”。……但是高尔基的立场依然未变:为了坚持自由的原则,他委婉地但却是不屈不挠地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施加压力。他说:“我常常同列宁谈到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残酷性。”
“ ‘您想要怎么样?’ 他惊异而且恼怒地问道,‘在这样空前猛烈的战斗中还能讲人道吗?哪儿还有仁慈和宽大的位置呢?欧洲封锁我们,我们失去了早就期待着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反革命像熊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而且也没有权利斗争和抵抗吗?……难道您认为,如果我对被反对的东西深信不疑,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 ‘在打架的时候,您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而哪一拳又是多余的呢?’ 在一次热烈的交谈之后,他这样问我。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能含糊地回答。
“我常常拿各种各样的请求去麻烦他,有时候我感到由于我老是替人说情而引起了列宁对我的怜惜。他问:
“ ‘您不觉得您是在干一些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但是,我继续做我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而这位了解无产阶级敌人的打算的人那愤怒的斜视,并没有使我退却。他伤心地摇着头说:
“ ‘您这是在同志们和工人们面前糟踏自己的名誉呢。’
“可是我指出:同志们,工人们,‘在激动和愤怒之下’,往往把有价值的人的自由和生命看得太轻,太 ‘简单’;依我看来,这不仅是以过分的、有时是毫无意义的残酷来糟蹋正当而又艰苦的革命事业的名誉,而且在客观上对这个事业是有害的,因为这排斥了不少重要的人物,使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事业。
“ ‘唔,唔,’ 列宁怀疑地哼了几声,向我指出知识分子叛变工人事业的许多事实。
“ ‘在我们当中,’ 他说,‘有许多人之所以叛变革命,不仅是由于胆怯,而且是由于虚荣,由于怕丢脸,由于害怕他们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碰壁时会吃亏。我们是不怕这个的。理论,假说,在我们看来,并不是 ‘神圣的’ 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工具而已。’ ”
列宁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并不在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地地道道的 “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在十月革命问题上他可是豪赌了一把,幸运地撞了大运。但是,正如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指出的那样:“对历史的自然进化进程的破坏,变成了俄国的灾难。
“列宁激烈地同任何无法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概念相容的思想进行斗争。事情的这一方面是需要特别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需要对两点情况给予注意:一是改良主义被列宁彻底抛弃;二是涅恰也夫精神(注:恐怖冒险精神)在列宁的实践中牢固地得到了确立。
“但是生活终究是生活。它对待那些开始对生活施加强暴的人是不那么仁慈的。因此一切也就偏离了正道。”
一个偏离了正道的国家最后能走到哪里去呢?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动了69个春秋的苏联国旗,像深秋的一片枯焦的落叶那样,在寒风中徐徐沉落,直到落进历史的深渊。……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6)
一天,美国总统福特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争吵起来,互不相让。一个说,在我的任期内,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归入我的体系; 另一个说,不对,在我的任期内,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应该归入我的体系。就这样,他们各持己见,谁也不服气。后来,他俩去找上帝,请上帝来作出判断。上帝对勃列日涅夫说: 在我的任期内,你的目的是实现不了的。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4月9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