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长
大约在1972 年,董连长和申指导员先后调走,张耀勋和田振国分别接任连长和指导员。
张连长一身戎装,个子不高,绰号“小个张”,但是他气宇轩昂,相貌英武,看来也是个厉害角色。
起初张连长给我的印象反差很大,他在全连大会上叉着腰摇头晃脑地讲伯恩斯坦、贝特莱,我们在下面一片茫然地挖着鼻孔,根本听不懂。他丝毫不顾大家的感受,顾盼自雄,口若悬河,令人想起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奸商。

在非正式场合,卸下伪装的他好像换了个人,满口的国骂加人体器官,春意盎然,令人倍感亲切,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972年底,张连长采纳了马廷的建议,要我重新负责质量检查工作。我表示拒绝,其实是想趁机讨个说法。我对张连长说:“这浑水我不敢再蹚,动不动就打成反革命,我找谁讲理,还是另请高明吧。”张连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回答:“你小子少来这套阴阳怪气。”说完后就将我赶了出去。
张连长的父亲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因为是土八路,没有参加正规部队,解放后没有安排相应的职务。张连长勤奋好学,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来兵团之前是北京军区装甲兵的教官。难怪他讲起理论头头是道,原来是在过教官的瘾。
当时有一本内部发行的书《中苏战争》,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我读过后,向张连长证实一些数据。张连长惊讶地问我这些资料的来源,然后兴奋地和我谈了很长时间。通过长谈,我发现张连长眼界十分开阔。他读完《第三帝国的兴亡》后写了厚厚的一叠心得体会,并拉着别人一起探讨,他不但详细分析了双方的得失,并绘制了各大战役的态势图。我当时与张连长已经很熟了,便没正经地回答说,一个小连长还操司令的心啊,还戏称他“张大帅”,虽然嘴上挖苦,心里却对连长很是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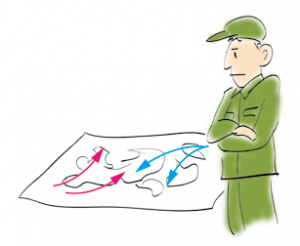
与前两任连长相比,张连长少了些书生气,并且拥有一种洞穿人性的智慧。他平时聊天时总把“莫信直中直”挂在嘴边,可惜当时我把它当做连长随口而出的口头禅,没有引起警惕。
中国所有单位的组织结构都是由党和政两个系统组成的,目的就是要两个系统互相监督制约,两个系统团结一致是不能允许的,这就等于互相勾结,违反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互相掐才是常态。我们连也是这样,连长和指导员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之间的争斗永无休止,而这种争斗总要把下面的知青卷进来。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连长们的接触比较多,几位连长对我的工作也比较认可,所以我被划为连长一派。有时这种划分也很随意,甚至当事人也不清楚自己所属的派系。我和李培楠、杨建国、苑再励四个人是一个“公社”的,是在一口锅里吃饭的哥们,四十多年后才知道我和培楠属于连长一派,建国却属于指导员一派。按说这派那派的名堂我很小就知道一些,和小朋友们玩打仗游戏时总会喊“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长大后反而糊涂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受到打击。
当官是要有成绩的,当连长的必须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踏踏实实做出无可挑剔的成绩,不仅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也需要一些管理的能力,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指导员则有两个努力方向:树人和整人。树人指炮制出够级别的先进典型,百年树人,听起来很难,实际上笔杆子们可以闭门造车,搞出足以乱真的各种先进事迹。树人的难点是先进的指标是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拿到兵团级和师级的先进指标机会很小,故而搞出大动静并不容易。另一招就是整人,这个没有指标的限制,制造“阶级敌人”可以轻易在业绩簿上浓墨重彩填充,无疑是条捷径。
在政治挂帅的年月里,搞权力斗争这套东西,玩弄政治的指导员们有天然的优势,连长们的精力主要在生产方面,因此总是很被动。在一连历史上的三次党政之争中,前两次都是连长失利,书生气十足的董连长被调走后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这第三次却是张连长大获全胜,他不在政治方面和指导员纠缠,那不是自己的强项,而是瞄准了对手的作风问题。当时作风问题最不可原谅,结果田指导员以丢人的丑态栽倒,一把揪住小田裤裆里的那根把柄则成为连长制胜的法宝。
田指导员被撤职,张连长仍要痛打落水狗,非要把小田留在连里当一个“摊儿长”。本来最小的官是班长,接到生产任务后,班里根据任务临时分为几个生产小组,我们把一个生产小组叫做一摊儿,负责人被称为摊儿长,管三四个人,也不是正式的职务,张连长如此安排的目的当然是羞辱对手。最终上级把田振国调到团里,拒绝了张连长的要求。通过这件事,我隐隐约约看到了连长的另一面。

过去连长一派失利,我也跟着倒霉,这次总算赢了,我却没得到什么便宜。田指导员的兴趣主要在女知青身上,根本没把我这个无名小卒放在眼里,即使他胜出,也没工夫找我的麻烦。我觉得这个胜利对自己而言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没有什么含金量。
没有了指导员,政治环境宽松了许多。张连长十分爱才惜才,很欣赏陈斌儒等老高中生的学识,我是老陈的朋友,连长爱屋及乌,我也沾了不少光。
张连长调来之前,我因听敌台被整。在边疆地区听敌台其实是很普遍的,敌台的功率大,距离又近,有时它的信号比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还强,几乎人人都听过。这种事情放下屁轻举起来千钧重,如何处理全凭领导的心情。田建国为我打抱不平,向张连长介绍了我挨整的情况,并说,其实没有必要禁止那些有分析能力的人听敌台。连长听后哈哈大笑。
过了不久,连部班的班长胡军找到我,期期艾艾地说了一大堆,我最后终于听明白了,他是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和我谈话,要我写一份入团申请。我当时就伸手摸胡军的额头,胡军推开我的手说你再不入团就超龄了。经历过几次折腾之后,我的政治上进心早已被摧残殆尽,回答说这个东西我已经在1969 年写过了,遗失不补,现在找不到了是你们团支部的责任。胡军要我再写一份,我推辞说入团申请我已写过,再写就该是写入党申请了。

来来回回扯了几次,我总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张连长倒田成功后,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在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张连长忽然对团支部的委员们说了一句:“有一次新华问我‘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入团?’我无言答对。”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愣住了,我这样的异端怎么会突然异想天开地要求入团呢?明知连长胡编,但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无论怎样荒唐,团支部也要执行党支部的指示,特别是在这个重新洗牌的敏感时期,他们只好继续做我的工作。胡军和赵志华是我的介绍人,最后胡军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怎么就不明白连长的意思呢?你过去惹出那么大一堆事,现在不就是等于给你公开平反吗?”一语点醒梦中人,如果辜负张连长的良苦用心,我未免太不识抬举了。
尽管如此,我仍不肯重新写申请,最后团支部也不再坚持,让我直接填表。其实填表就等于申请,我非要端着架子,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故意气胡军。胡军和我的关系一直不错,我如此欺负老实人,很有些过分。
以前我主动申请入团的时候,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竭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斗私批修,却总是被人以各种理由挑出无数毛病,似乎我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被整得半死不活。现在却走到另一个极端,我被各种表扬包围着,连多吃了几个窝头都被说成是因为干活卖力的缘故。
当时连里开会或政治学习我是不参加的,领导对此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认态度。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和马文然玩一种纸上游戏,连里通知大家参加全连会议,马文然去开会,我一个人也就无法玩下去了。我正在兴头上,就和马文然一起来到小礼堂继续我们的游戏。会议结束前,忽然听到副指导员左志顺在表扬我:“你们看看人家新华,平时工作忙,不能参加会议,今天来到会场,头也不抬,认真做笔记。”
 你们看看人家……头也不抬,认真做笔记
你们看看人家……头也不抬,认真做笔记
表扬咱们哪……
转眼之间我被打扮成先进分子,就和几年前在指导员的谋划下转眼之间把我定义为敌我矛盾那样突然。就像一个机器人,只要领导轻轻拨动一下开关,我就可以在好人和坏蛋模式之间迅速转换,先进与反动就是这样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工作表现还是可以的,但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官方距离很大,之所以能入团,我猜想可能与父亲当时已经恢复了工作有点关系。
在发展我入团的大会上,赵贞忽然提了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未能与右派母亲划清界限,根据是我仍然随着母亲姓刘。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我的父母去延安后都改了名字,父亲原姓刘改姓林,母亲原姓胡改姓刘。我姓的是革干父亲原来的刘,而不是右派母亲现在的刘,此刘非彼刘,说得我汗水流,这件事情实在太凑巧了,解释起来显得很勉强,最后我自己都没有底气了,只好长叹一声说,没想到第一天入团就立刻感到了组织的温暖。于是大家在哄堂大笑中一致举手通过。
不久后张连长回到部队,几年后我也回到北京。在上个世纪90 年代曾与连长有一次重逢,连长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背微微发驼,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一些往事已经模糊,我却永远无法忘记,是连长带领我突破偏见的屏障。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