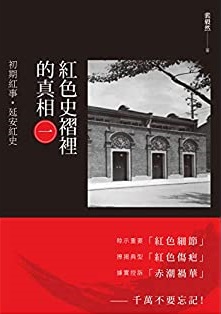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册(结语)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册(结语)
如何看待苦难乃是社会文明度的重要刻线
中共红色革命乃不成熟的早产儿,肇灾之巨,绵延至今。总结起因,相当意义上源于对苦难的认识,过于激进,企求「一锅烩」解决,未意识到苦难的存在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如何看待社会苦难,看似一道比较简单的道德问题,实则内涵深广,触须深远。苦难不仅是一切社会改革的初始动力,也是所有革命理论的支撑性价值。苦难激起人们的强烈道德感,继以审视既有道德既有法律。革命也总是从苦难起步,或曰革命者总是从「说苦难」开始构筑价值起点。消除苦难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第一感,也是解决苦难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很简单,设若没有苦难,还需要改革吗?还需要发动革命吗?
不过,如何看待苦难?如何具体地历史地看待苦难?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工程。今天,当我们再来讨论这一基础性社会命题,再来考察这一关键性认识起点,依托中外近代数百年革命史,有着诸多史实性论据,应该较易形成共识。
本文基本论点:一、苦难必然对道德现状与现代法律提出质疑,乃是修正道德法律标准的价值起点之一。从价值顺序角度,道德与法律只是一种追补型堵漏,从源头上消弥苦难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二、深入分析苦难成因乃是社会文明度刻线之一,道德与法律并非万能,理性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消弥苦难之源泉,或逐渐趋向这一目标,才是社会文明的实质性提高;三、理性提出解决苦难的方案乃是社会综合实力的体现,告别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设计,承认客观现实的种种掣肘,逐步解决而非不切现实的“毕其功于一役”。
为达上述目的,首要之点便是合乎分寸切合实际地看待苦难,谨防将局部苦难放大成全域性,动辄要求对社会开大刀、动大手术,势必一脚踏进乌托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非有苦难就必须革命,或曰决非只要苦难存在,就是必须举行革命的绝对理由。其实,从相当意义上「炉灶」本身就是经验的凝聚。即使万恶的专制,也是「存在即合理」,有着不得不然的「合理因素」。专制因权力集中而行政效率甚高,所需人员较少,管理成本低廉,与农业社会落后缓慢的生产力相一致。清代官员总数未超过四万,官民比例仅万分之一。以农业社会的经济承载能力,不可能供养太多的官吏;再以其时的公务,也不需要频繁开会的议会,没那么多事儿。而对弱民愚氓来说,「一切老爷作主」,既省事又省心。因此,万民都希望拥有一位「青天」,因现实而合理。
当然,从绝对意义上,所有苦难都是社会能力不足的外化表现,都是一个社会与国家脸上不光彩的瘢痕。从道德角度,所有苦难当然应予消除。但历史经验痛苦地告诉我们:苦难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解除苦难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今世界各国普遍铺设「社会保险」,便是一项现代社会才可能提供的当代产物。旧时不仅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构想,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社会可能。消除苦难,关键当然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谈不上呵!
苦难原因十分复杂多样,有单因也有复因,很多时候也裹含受难者自身原因。如何对待苦难者,一味救济,无视苦难者身上的人性弱点,照样好心办坏事。韩国对待「脱北者」的一系列设置,先救济后鼓励自立,才叫授人以渔,真正「扶上马,送一程」。每位「脱北者」首先得到韩国政府50万韩元/月(约合2900元人民币)定居援助金,一共半年;然后给予半年~一年职业培训,政府支付20万韩元奖学金/月,培训结束再得240万韩元(约人民币13600元)奖励,如完成带技能的大学课程(一年),奖励200万韩元,获资格证书再得200万;「脱北者」参加工作一年,奖励450万,次年500万,第三年550万。每位「脱北者」三年共获2140万韩元(约13万人民币)。可怜的「脱北者」还有严重的「社会主义」骄贵病——不愿承担肮累危险工作,甚至放言「正是因为韩国政府提供金钱能让自己衣食无忧,才冒生命危险越境,才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什么非要从事韩国人都讨厌的3K工作(脏、累、危险的日语首字母)。」一受上级斥责,立马走人,无故缺勤、装病休息等,不断整出麻烦。尽管韩人对「脱北者」有所歧视,韩国政府仍尽力帮助每一位「脱北者」。[1]
1950~70年代,「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乃是一个不顾客观现实的经典史例。一个扫街清洁工,无论社会贡献还是社会承认,难道能与工程师、医生、教授或市长一样吗?如果真的一样,尤其收入一样,谁还愿意耗费数年宝贵光阴去上大学、去攻硕读博,去获得进入社会名流的努力?社会又如何从低走高?又如何实现全民知识化智慧化?既然无知者最光荣最高尚,知识者最无耻最卑鄙,谁还愿意吃吃力力去成为一个被唾弃的有知者?可见,没有价值秩序的正确码放,便不可能得到符合客观现实的结论,社会也会因此而遭扭曲。
再如似乎最最响亮的「劳工神圣」,仅就这一口号本身,似无多大问题,对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工农具有启蒙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正确无比,难道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工农不神圣吗?麻烦出在其后的第二步逻辑连缀,即紧随「劳工神圣」提出的政治要求:「一切权力归工农兵」、「穷棒子坐江山」。如此这般,麻烦便随着错误一起来了。工农当然「神圣」的一面,但也有缺少知识化的另一面。片面强调他们「神圣」的一面,掩盖他们缺少基础教育的另一面,既不合乎客观现实,也使其连缀的政治要求——「一切权力归工农兵」、「穷棒子坐江山」——失去价值基础。工农毕竟没有受过基础教育、不会读写、缺乏现代化知识的武装,不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缺乏处理社会事务应有的审慎之态,极易情绪化……
将简单劳动者一夜之间魔术般捧抬为「最高贵者」,将他们从最卑微的社会底层推升至指点江山安排社会的「当然主人」,除了混乱与蛮干,还能指望得到什么理性之果?因为,既然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知识,也就不可能明白知识的作用;既然他们除了自己的乡村与工厂之外,对现代世界所知甚少,怎么可能具备「最聪明最高贵」的知识结构?既然他们不明白社会各方利益的复杂性,也就不可能理性地安排利益关系。尤其对于财产,他们此前除了嫉妒,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财产成为「经济增长点」。工农运动中这一弊端,当然不幸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更不幸的是:这一结果竟早为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所揭橥——「笨蛋闯进了天使都不敢落脚的地方」。柏克的一段话具有经典性:
一个理发匠或一个蜡烛商的职业,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桩荣誉——更不用说许多其他伺候人的雇工了。这类行业的人,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压迫,但是如果允许像他们那样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来进行统治的话,国家可就要遭受压迫了。在这一点上,你们认为自己是在向偏见进行斗争,但是你们却是在向自然开战。[2]
从相当意义上,人类社会也是一项自然产物,也需要「保护自然」,不能随意破坏「生态平衡」,打破既有重大价值逻辑链条,势必引发社会震动,往往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所谓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思想现代化,或曰认识现代化,即正确码放各项社会价值,依次处理各项社会事务,而非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极左思潮的哲学错误就在于错码社会价值顺序,将局部苦难放大为必须更动所有制的社会大革命,革命革命再革命,既左又左再往左,最后弄得不可收拾。文革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一刻都不能想到自己,有违人类本性,这人还能活吗?又如何捍卫自身权益?根据这一价值起点放射出去的逻辑,还能正确吗?社会还能不被搅得稀烂吗?只要稍微想一下,如果自己都不管好,还怎么去帮助别人?又如何革命?就是按你红色逻辑,也必须适度存私呀?!否则,一点都不能想到自己,一动欲望就「反动」,你叫人怎么活?革命者本身都无法存在了。
当然,不可否认工农乃是最广大的社会苦难承受者,但苦难的承受者就一定得成为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者么?两者之间存在哪些价值性必然联系?解决工农所承受的苦难难道可以单方面满足工农的自我要求么?难道可以无视社会秩序的整体性么?难道毋须兼顾社会利益的其它各方么?就社会和谐而言,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呵!
现代化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最终得转化为文化现代化,方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性推力。为达此目的,肃清极左思潮的文化垃圾与后滞性影响,便是我们应该清晰认识到的「时代任务」。
初稿:2010-3-1;补充:2010-8中旬
[1] (日)水沼启子〈韩国「脱北者」问题严重〉,原《读卖新闻》;《检察风云》(上海)2009年第20期转载,南康译,页50。
[2] (英)柏克(Edmund Burke):《法国革命论》(1790),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9年,页56~57、59、65。
原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