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2

约恩·福瑟是挪威当代的国宝级作家,其作品迄今已被译成近五十种文字,在全球上演逾千次,囊括了几乎所有最顶尖的国际艺术大奖,也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二〇一〇年,他摘得了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奖项,易卜生奖,而人们在介绍他时,也往往会冠之以“新易卜生”的名号。2014年,“福瑟之繁花”5部戏剧作品也作为ACT十周年的特别版块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
舞台上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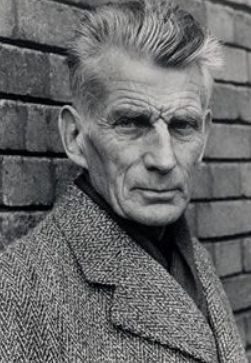

除此以外,贝克特和哈罗德·品特也是最常与福瑟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名字,他对两者风格的继承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与贝克特悲剧性的沉默或品特戏剧性的停顿相比,福瑟的作品虽不乏张力却更趋内敛,遵循着精确的节奏和格式,比起剧本,更像是“舞台上的诗歌”。
福瑟的戏剧都是用新挪威语,或称尼诺斯克语(以口语为基础的挪威书面语)写成的,一种“事实上从不被诉诸于口”的语言。他的剧作中少有戏剧性的转折,对话、动作也少之又少——一种“极简主义”的写作;而真正构成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的,是那些重复、停顿、空白和沉默。他赋予我们日常熟悉的词语全新的涵义,无论你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挖掘到多少源自前人的灵感和启迪,他始终是西方戏剧界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时继承和超越了现代戏剧的定义。
别样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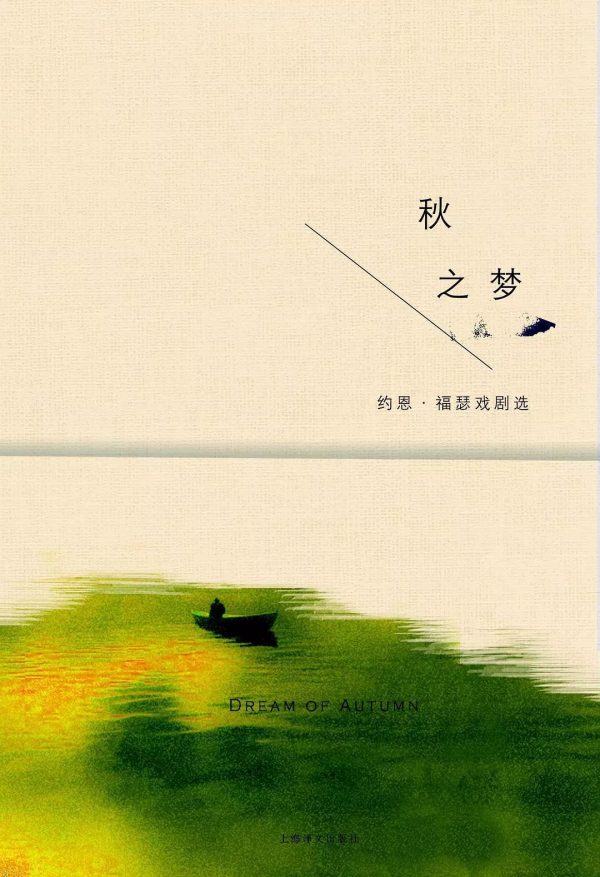

福瑟九十年代初首登欧洲戏剧舞台时,他的作品,就像他剧中的角色一样,好似一个“局外人”。除了他以成名作家的身份转型剧本写作这点外,当他的处女作《而我们将永不分离》于一九九四年在卑尔根首演时,彼时的北欧剧场里几乎都在上演拉斯·努列的家庭剧,或者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新生代剧作家,如萨拉·凯恩、马克·雷文希尔等人的作品。在九十年代的激越与抽离之间,福瑟的作品投射下一片别样的、自成一体的光芒。
尽管我们不会把这些剧作定义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却依然能够从中触及现实的片羽:城市与乡村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人口的迁徙,年轻一代回到家乡拜访被留下的老人,以及最重要的,也是最易让观众产生共鸣的,在新环境中漂浮无依的空虚和不确定感。他的角色看似退守消极,内里却蕴藏着一股不安的喧嚣。他们大多面目模糊,只是“他”、“她”、“男人”或“女人”,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也鲜少被提及。这些角色存在于某个地方,却从不属于这里,在一个无所依托之地,演绎着人性最基本的情感,试图还原人类最本质的处境。
无名的空间

福瑟笔下的角色都深陷于时间的流动,夹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试图寻找一个“无名的空间”(non-space),却又不得不看着它被过往与未知所侵蚀。一九九六年,《一个夏日》在奥斯陆首演,四年后获颁北欧剧协最佳戏剧奖。在这部剧中,时间分化成了“过去”与“现在”,角色看似身处同一个空间,却难以消融彼此间的隔阂,也始终无法相互理解。话语如同潮水般一波一波袭来,循环往复,终究找不到出路。一旦回到最本质的、有关存在的问题时,以人类有限的语言,能够给出的仅有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毫无意义的,或许,最好的谈论某件事的方式就是沉默,单纯的空白。
为尚未到来的时代写作
阅读他的作品是困难的,但更困难的是将它们搬上舞台。作为“剧目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我们往往会看到他的作品以迥异的面貌在不同国家的剧场里上演。对于观众而言,观看他的作品也非易事。福瑟的舞台就像是一个房间,他的角色就是观众的向导,只是他们鲜少将我们引向一个确定的答案——甚至根本没有答案。另一方面,这也恰恰佐证了他的伟大:戏剧是阐释的艺术,越是了不起的剧作家,越是能赋予演绎者更多的阐释空间。正如瑞典戏剧评论家莱弗·策恩所言,“福瑟是在为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写作。唯有在演绎者和观众共同的梦境中,这个戏剧的时代才能到来。”
 Jon Fosse
Jon Fosse
约恩·福瑟
有“新易卜生”之称的约恩·福瑟(Jon Fosse),是当代最富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多次获得各类国际艺术大奖,也是近两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