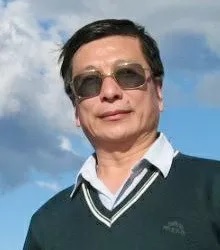本文作者
田沈生,沈阳出生的北京人。1966年投身革命(文革),1967年高中肄业,1969年奔赴陕甘宁边区(插队),四年后革命意志衰退(回到北京),2年闲赋于市井(待业),曾跻身老九2年(中学代课),1974年混入工人阶级(电工,汽车司机),四年后搭上末班车成为知识分子(上大学),又是四年,搭机飞过赤道,在南半球深造,定居至今,33载弹指一挥间。自1988年起,先后在海内外华文报刊杂志网络上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时评等近百万字。创办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任澳洲《朋友》主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理事等。
牛传银老师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对母亲说:“体育教研室的老牛去世了,心肌梗死。前些日子遇见他,看着身体还不错呢,怎么说走就走了!”父亲感慨地说。
“您在说谁?”我闻讯跑来,突然插话问父亲。“是牛传银,牛老师,你在附中的时候他还教过你呢。”
真的?我的心咯噔一下,再没有以往听到牛老师名字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诙谐。记得1960年代初,在北航附中上初中时,由于附中的体育师资不足,牛传银老师由大学临时抽调到附中,正巧教我们年级体育课。那时我十四五岁,对体育正着迷,尤其喜欢跳高。在牛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跳高成绩不断提高,在当年校运动会上还夺得了初中组第一名。
那段时间,我与牛老师接触很多,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了解他的性格。牛老师为人和善,不爱批评人,课上总是一遍遍为我们做示范,不断的鼓励和表扬,在我们这帮学生中,牛老师的人缘很好。别看他平时言语不多,可偶尔蹦出一两句话来,不是令你深思就是叫人捧腹。
记得那是文革以后,有一回我去校医院帮母亲取药,在内科诊室门口意外地遇到了牛老师。说起来,我们虽然同住在一所大学里,可自打那年高中我考上了北京一0一中学,便离开了附中。后来文革开始,中学大学以致全国都乱了套。再往后,中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学教工奔赴五七干校,算起来也有十来年了,我一直再也没有见过牛老师。印象里牛老师黑红的脸膛如今变得有些黑黄,人也显得消瘦苍老了一些,可精神头儿还是那么足,依旧不减当年运动员的风采。
“牛老师,您身体还好吧?”我主动问候。
“马马虎虎。不瞒你说,要真好就不到这来了。”说罢,他指了指内科诊室的牌子。“您?”“可能是这儿出了点儿小问题,”牛老师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胸,“胸闷,有时感到心脏突突地跳。”“您可要悠着点儿,上课时运动量别太大了。”“上课好说,恐怕是这场文化革命的运动量大了点儿。”牛老师突然压低了声音,“你想,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运动,天天敲击你的心脏,能不出点儿毛病?”
这话有点诙谐却是真的。谁都知道文革那年头儿,全国从上到下,没日没夜地斗批改。今天大联合,明天抓叛徒,抓走资派,后天又你死我活地打起来了,几年也没消停过。就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闹到最后,清华北大的两派革命斗士也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还死了不少人。尤其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更恐怖,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一句话,就会招致大祸临头。深更半夜,一伙人突然闯进来,抄家抓人,已是家常便饭。
那年月,无论你有事没事,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没几个人能过上安稳日子。别说得病,就我们学院里没病没灾的,服毒、上吊、跳楼、沉湖的,一个接一个,往少说也有二十多人。后期通过内查外调,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几乎全都是由于惊吓过度,寻了短见。
“好在都过去了,我想我这心脏也没什么大碍。今天抽空来查查。”牛老师轻描淡写地把话题又拉了回来,我们又闲聊了几句,就此告别。
人生难料,没成想那次巧遇竟成永别。牛老师,愿您一路走好,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吧!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着。
杨发金同学
说起牛老师的名字,当年我们这帮十几岁的学生十分调皮,常在暗地里起哄。“金比银贵,牛老师叫传银为什么不叫传金呢?”还有一位同学竟以牛老师的名字出了上联,悬赏一个苹果,征求下联。要说背唐诗,对对子(注:那时不懂平仄,对着玩),那是我的强项。他的“牛传银”刚出口,我不假思索,举手答曰:杨(羊)发金。众人哗然,拍手叫好。
杨发金是我们小学的一位同学,由于家庭困难,劳务繁重,学习渐渐跟不上,小学毕业便辍了学。虽然他没有上初中,当时他家还住在学院里,时不时大家还能见上一面。就是到现在,许多同学并不知道我和杨发金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友情。
当年,我与杨发金同在一个学习小组,论年纪,他比我大一岁。说到学习,我就比他自豪多了。我是班里的优秀学生,而他几门功课同时不及格。因为我是组长,老师指定我来帮助他。别看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对老师的委任却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帮他渡过考试的难关,也算不辜负老师对自己的信任。
说到杨发金,他也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听我母亲讲他老家在山西,由于家里穷,父母从小把他给了人。现在的养父是一位年老体弱的工人,养母又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一家人仅靠养父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生活十分困难。
听杨发金后来对我讲,从十岁起他就肩负起全家的洗衣做饭和全部家务劳动,还要照顾多病的养母。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起床,做好饭以后才能去上学。由于家里穷,舍不得买煤,做饭烧水几乎全用柴火,烟熏火燎不说,柴火也全是靠他到校外几里地的土城上去砍,然后一捆捆背回来。冬天,常常见到他手背上一道道裂口和一条条荆棘的划痕。问他痛不痛,他总是憨厚地笑笑说,没事。那时,我常听母亲感叹地说,都什么年月了,恐怕整个学院里也就他们一家还在烧柴火。
也许是久病在床的原因,他的养母脾气古怪,尖酸刻薄,只要是他在家,就把他指使得团团转,一刻也不得闲,动不动还对他又打又骂。有几次我都看不过去了,可他总是一声不吭,逆来顺受。“我不恨她,把我拉扯大,他们也不容易。要不是他们,我还在山西农村,那里怎么也比不上北京城啊!现在我就想快点长大,能去挣钱就好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这样想,这样说,着实令人感动。
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杨发金学习再努力,成绩也很难提高。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下决心去帮助他。
下午放学,我先陪他回家,由我出面告诉他养母,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要在学习小组里完成,我是组长,所以要去我家做作业。见我这么说,他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我俩顿时像挣脱缰绳的野马,抡着书包向我家奔跑。那段时间,我俩几乎每天在一起复习讨论做作业,终于他顺利地通过了期末考试。
漫长的暑假来临了,妈妈把我送到城里的大姨家和表哥表弟他们一起玩。杨发金却一天也没有闲着,除了家务,他养父还给他找了份挣钱的差事,回收铁钉。那些年,学院里提倡废物利用,凡是大小弯曲的旧铁钉,用榔头敲直,皆可卖给院工程科,按斤付费。每天忙完家务,杨发金就提上起钉锤和一个洋铁桶,满院转悠。墙壁上的,木板上的,凡是不用弃用的废旧铁钉,不论大小,一个个启出来,再一个个敲直,等攒足一小桶时,像端宝贝似的送到工程科。一个暑假下来,他卖了四块多钱。那年头儿,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十元,这些钱在他眼里就像个天文数字,乐的他咧嘴大笑。当然,钱大部分交给了父母,他也偷偷地留下一小部分。
暑假快结束时,我回到了家里。杨发金闻讯,急忙赶到我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能不能帮他个忙。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一分两分的硬币其中还有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他告诉我这些钱是他挣来的,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发现说不清。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想买一副绒线手套和一双胶鞋,留冬天砍柴时用。
我听了二话没说,把自己的那个存钱罐拿出来,交给他。我知道罐里是空的,我存的钱暑假早花光了。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数着往里塞,嘴里在不住地叨念着:一毛,两毛……总共是一块六毛二分。完了,还工工整整地用笔写了一张小字条贴在罐上:1.62元日期1960年8月**日。他把存钱罐交给我,我将它放在了柜橱里。
从那以后,杨发金隔长不短地跑到我家里来,有时只是捧着存钱罐摇一摇,听听响,有时往里放上一分两分钱,然后在字条上写下新的数目和日期。
有一次,我父亲在柜橱里发现了这个存钱罐,问其缘由,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父亲叹了一口气:“这孩子也真是可怜!”说罢,翻出兜里的零钱,一股脑塞了进去。从此,家里不管是谁,见到一分两分的硬币,都记得塞进这个存钱罐。
冬天来了,存钱罐上的记录是1.96元。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一九六零年的冬天很冷很冷,席卷全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外省就不提了,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们也不得不在呼啸的寒风中一次次勒紧裤带,抵抗着饥饿的袭击。那时物资匮乏,商店里空空如也,充斥货架的是锅碗瓢盆,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就这也必须持有工业劵等票证才有资格购买。
说到副食商店就更惨了,除了大缸或瓶装的酱油醋,散装的粗细盐,连一根咸菜也见不着影儿。有时排上一天队能买上一斤干海带,或是一两棵腌白菜就算万幸了。
据说这是对首都居民的特别优待,当然,没有购货本或是购货本丢了,你就是祖宗八代住在北京也没有用。那时,有钱没有票证是买不到东西的。有好事者统计过,当年居民手中的各种票证多达几十种。如果出门不小心拿错了票证,肯定是要空手而归,白跑一趟。
那年冬至的前一天,杨发金来了,我看见他手背上又出现了裂口和荆棘的划痕。一进屋。他就抱起存钱罐摇个不停,最后小心翼翼地将罐子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出来,全神贯注地一分钱一分钱地数开了。看他庄重的神色,似乎每一分钱都在牵扯着他的心。也难怪,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的血汗钱哪。
“你打算去买手套和胶鞋?”我在一旁一面看,一面问。他轻轻摇摇头,没有回答,继续数他的钱。“那你取钱干什么?”我奇怪,又问。“我……”他欲答又止,还在不停地数着。
“咦!”他突然叫出了声“这钱不对数,怎么多出来啦?”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罐上的记录,纳闷儿地说:“明明是1.96元,怎么数两遍都是2.73元呢?”我笑了笑,开始敷衍他:“你没听说过银行存钱是有利息的吗?”“真的?在你这里存钱也会有利息?”他将信将疑。
“不对!一定是你往里放了钱。”他回过味儿来了,说着就要往外数钱。我见瞒不过他,一面拦住他,一面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好一阵才对我说,改天一定来向我父母致谢。说罢,拿着钱,急急地走了。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杨发金,他也没有再来过我家。
寒假快结束了,有一天我在院里遇见了他。他左手拿着小钉锤,右手拎个小铁桶,东张西望地在寻找旧铁钉。“杨发金,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一个寒假也不露面?”我有些不满地说。“我……”他支吾着。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是他家里出了点儿事。
冬至前几天,他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大他两岁,从未见过面的哥哥,从山西老家一路讨饭来到北京。那年头儿城市按人口供粮,本来家里就困难,再凭空添上一张嘴,养父母自然不会高兴,勉强留宿一夜,第二天就要打发他回去。只见他哥哥“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大声哭了起来。原来四个月以前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入冬的时候母亲已经饿得起不来床,临终时才告诉他,还有个弟弟在北京。“妈顾不了你了,你有命的话,就到北京去吧,兴许还有条活路。”
哥哥已经是家破人亡,如今这条道也被堵死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真是走投无路呀!
哥哥的遭遇,杨发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除了陪哥哥哭以外,他又能做什么呢?这时他想到了那个存钱罐。兄弟俩分手时,他流着泪对哥哥说等他挣到钱就会给他汇去。
哥哥走了,尽管天寒地冻,杨发金还是拿起了钉锤。
我初中毕业时,听说杨发金已经工作了,好像在山西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他早已不在学院里居住了,所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文革后期,听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说起杨发金,他已经死了,好像是在文革中,是病死的还是武斗打死的,谁也说不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杨发金的消息了。
新三届2019-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