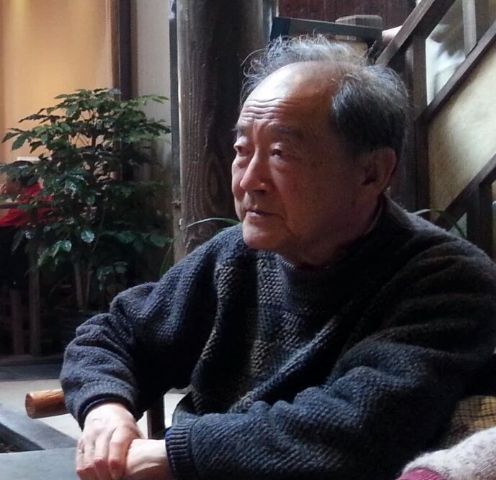2005年初夏,郁风、苗子来电话,告以收到一封误投给他们的邮件,说寄给我看看,可以做写杂文的材料。
原来是,石家庄有位退休的王维平先生,爱好书画收藏,在2000年收到信札七页(没有信封),结末署名“苗δδ”,因是竖写,两个圈圈被王先生误认为“子”字,遂以为写信者是“苗子”,并推测为黄苗子。后来听说郁风在文史馆工作,便把复印件寄到中央文史馆转交,“看看是不是黄老亲笔信札”,如经确认,当“物归原主,了却我的心愿”。
这是一封长达七页,两千七百来字的信,用“冀东行政专员公署信笺”(竖十三行)毛笔书写,下款注明“十二,廿一”,另有钢笔“一九四九”,或是收藏者王先生所标。
写信人苗某自述生年四十岁,如健在,今年当臻百岁了。他说“合省后我奉命来省府民厅工作”,应是从冀东行署调到河北省民政厅。从行文口气(如对乡村纠纷指点解决途径)、习惯(如最后“此致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等看,大概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领导干部。
受信人三同志(方正、子文、正舟),写信人说“许久不见,亦未通信,颇以为念”,可知原在冀东行署时也并不在一起工作。从信的内容看,乃是苗某家乡(二区商家林村)的县区以上主管干部。七页信札的前两页半,是请他们帮助解决他家乡的村里抗(日军人家)属跟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提示了原则和办法,总的说来是顾全大局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部分,作为六十年前的原始史料,让我们看到一部分当时中共基层干部良莠不齐——用政治术语说,就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甚至是很严重的。
这封信札,其实只是一封信的草稿。从后面署名写姓氏,名字用圈圈代之可知。过去人们的习惯,个人的文书最后不署名或署名不全,甚至直写某某的,必是草稿无疑,以示并非正件也。
此稿前一部分谈的是公事,如同领导同志指示,抽象原则和具体办法,都有规则可循,对一位领导干部,说起来并非难事,根本用不着起草。所以郑重其事地起草,加以反复推敲的是信的后一部分,谈他家庭的私事,请三位有旧(是曾相与共事且互有了解和一定感情的)当地干部,帮助他“解救”其母亲和“弟男子侄”。事情发生在土改期间,看来他的父亲成分应属土改斗争对象,土地房屋被没收后分配给贫雇农已成定局。写信的这位决心与“落难”的父亲划清界限,承认其父思想行为“封建”“顽固”,并以其在家中即实行“奴隶主”式的压迫,使母亲等深受其苦为理由,将母亲与其父加以区别,用“另立门户”即分家另过的方式“营救”出来。按:在土改中的成例,凡划为地主分子的,夫妇总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些在地主阶级家庭中确实遭受虐待,其地位如同佣工的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获宽贷,但这为数极少,属于特例。这样做的难度极大,这该是写信的人所深知的。所以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多费心,快营救我母亲逃出人间地狱生活吧!”
自然,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更深知这样做所冒的政治风险,那就是政治运动当最忌讳的所谓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家庭。他处在矛盾心态中,他心中的传统“孝道”,与当下组织纪律性的矛盾:“我们党员既非枭獍,谁无父母?苟非万不得已,孰肯与父母决裂如此?”大约几经权衡,决定舍父保母,又对受信的三位同志动之以情,希望他们“分忧”,用心良苦。
至于他的哥哥毓春等几位弟兄,长年在外谋生,并不分享地主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应作为逃亡地主看待。苗某代为申诉,至少在今天我们看来,是正常的。
我在这里说了半天,却还没让读者看到这封信稿,是有些喧宾夺主了。现将信稿全文移录如下:
子文
方正同志:
正舟许久不见,亦未通信,颇以为念!合省后我奉命来省府民厅工作,一切很好,请释念。(按:在上款和首段天头,原写有“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各同志身上了”,又用笔勾掉)
估计你们的救灾、秋征、集训农村党员、消灭奸特、召开人民代表会、颁发地照等等工作……一定会很忙很累的!但你们都是老于经验理论丰富的老同志,一定会很快很好顺利地完成任务的!
现在有两件琐事向你们谈谈,同时也是我的希望和要求。
(一)我村(二区商家林)抗属和村治安员及支书(女)的纠纷问题:昨天抗属代表来省请愿,我曾以私人资格给他们解释,不可兄弟阋墙自残骨肉,省掉阶级敌人的暗喜,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然而事实业经县区处理,已成“强弓之弩”,以私人关系既不能平息,只有用公事方面解决了(省里将行文到专县)。
据我了解村干有他一定的功劳,也有他一定的错误:如我村干在十年当中,被日寇蒋匪轮番蹂躏下,在极度惨酷环境中对敌作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这一件功劳是不可抹煞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贪污腐化、侵占胜利果实、压迫甚至打骂抗属、独裁不民主的作风,也是相当严重的——解放前的伙会副大队长(日寇蒋匪两朝奸特)曾绑护抗属及群众敲诈勒索腰缠万金;解放后参加了革命(据传闻),因有私人关系而待遇则超越老抗属,此尤为绝大多数抗属所不满——其他事实不多赘,想早为你们彻底所了解。
再有一件来:我村伙会商荣商然之妻等,赓续夜间被村干或民兵轮奸(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属实,我认为虽是阶级仇恨心所致但也影响政策,有伤风化,请调查制止,并加以批评教育。再从多方面考虑,万一该妇女们思想上尚存在反动残余,若由肉体关系引诱,也容易使我党员变节,你意以为何如?
对解决我村的纠纷,提出我的意见,供献给你们考虑:由党内和行政结合起来处理这一问题。对抗属方面多强调说明村干的功劳;同时也明确指出村干的错误,并教育抗属去掉偏狭思想及自私观念(方式须讲究)。更应使抗属认识到是自家事,骨肉相连,不可分裂。在村干方面则以整风方式,严格检讨错误(甚或有罪恶),若坚持错误,则须及时处理。使村干认识错误后向抗属道歉,双方破啼(涕)为笑,务求达到团结同舟共济之目的。在可能范围内进行调整胜利果实清理会账;再结合人民代表会或发土地证或其他中心工作进行整理支部及村政权。企求各方面心悦诚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一步。以上的建议,不一定正确,权作愚者千虑一管之见,提供参考。
(二)我的家庭问题:关于此点,早为你们各同志所关心,对这事苦心积虑的设法解决,其踌躇程度,当不减于我个人的负担,但我母亲及弟男子侄等均未获解放,这说明咱们大家的责任还未尽到!
我生平(四十岁)从未敢批评过我父亲,此次不得已我写了逾三千言的一封信,这是破天荒新纪元的批评和揭发我父的缺点;可是我没有半分信心可以改造老人家。因为他的封建顽固性是牢不可破的,除非打击他别无良策——固然,我的家庭也等于你们各同志的家庭,决不愿自己家庭——尤其是自己老人不愿有尴尬,惟至万不得已处,只有下决心!
马克斯(思)恩克(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二章中段,已明白指出必须消灭家庭,以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虽然不能过早提出消灭家庭,起码也要改造封建式的家庭,要解放悲惨的被压迫者脱出封建枷锁。
我的家庭在中国来说是典型家庭,同时我父也是典型人物(可详细的参照给我父亲的那封信),因之我大声疾呼:“同志们多费心,快营救我母亲逃出人间地狱生活吧!”
我对解决家庭问题提出意见如左:
我个人理解孝道,其标准须由父母说起,如果父亲站在党的原则下行事,那我们尽孝道是完全应该的——这话是不是说以党的尺度来衡量父母呢?不,不完全那样;但起码也须父母不背于党的大原则——我们党员既非枭獍,谁无父母?苟非万不得已,孰肯与父母决裂如此?
同志啊!我母亲与弟男子侄,被我父统治压迫的不能活着呀(尤其是我母亲更严重),纯粹的家庭法西斯蒂与家庭大封建主(奴隶主)压迫奴隶一样,这决不是张大其词!
所以我主张把我母亲以下家庭所有人口都搬出来,除给我父个人留一份房屋土地外,把我家房屋土地由农会分配给农民,重新由外村或我村分配给我母亲以下各人口土地房屋一份,如此就粉碎了我父的封建意识(他经常说“土地房屋是我的,你们都吃我不中”),并由政府明白指示他,说明我母以下各人口均自立门户,不许搅闹,如有搅扰,是犯刑事罪的(同时也必须由区村监视他,如果搅扰就认真办他),坚决地把我父一人孤立起来,等到社会主义再说。
关于我父的恶作剧,可参照我给他的那封信,更可到我村了解,故此不用多写。
其次还有一事,就是我弟兄敏(按,应为毓)春、毓民、毓文等都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小手工业工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第二种工人(有东北我解放区政府的证明),村办公人硬把他们屏逐农会之外,说他们是关外来的,当做还乡地主那样看,是错误的,是不认识本阶级的,是关门主义的……既不帮助建立家务,更不许在农会发言,我兄毓春前在农会会场发言,被逐出会外,这是实情(村干呼口号赶出来的)。我党是给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是本阶级的人,我们是本阶级的党,村干认识错了,请给以解释纠正,是盼!(按:此段天头加写:他们家庭虽是中农,但均在外负苦十五年以上,其本人成分决定是工人)
根据以上所述,我再不多说了,我把希望完全寄托你们各同志身上。把千斤担子在我思想上是换肩了(由你们担负)。
同志们!多操心吧,替我分劳吧,让我把精神完全用在工作上吧,我多做了工作,就是你们各同志的成绩呀。
纸短话长,不尽所云……并希多通信,在工作上在思想上多帮助我,是所至盼!此致
布礼
苗δδ
十二、廿一·
(旁注:一九四九)
我头一遍看这封信,在他设计为母亲开脱的地方,直觉反应是他在以权谋私。因为按我们的思维定势,遇有这种情况,作为干部、党员,首先应该划清阶级界限,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避嫌,其处理原则是:政治第一,运动第一,工作第一,什么亲情、孝道,不能让这些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封建道德”干扰破坏像土改这样伟大的政治运动。从这样的大道理出发,苗某显然已经缺理,当时如遇揭发,光是这封信,就够批他一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呀!
但静下心来想想,不知这封信稿,是否誊清发出,如果发出,那三位至友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如果确能如所期待,那末,几十年间只是少了一个被蔑称为“地主婆”的五类分子,使她的子侄们也得以因她的侥幸,而免于被蔑称为“狗崽子”“黑五类(子弟)”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共产党也少了一个“敌对阵营”的成员,又有什么不好呢?
也就是说,当苗某出于亲情,呼吁他的至友出力开脱他的母亲时,至少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人性在与党性的角力中一时占了上风,他的良知使他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抛到了脑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并没有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此时此地此一问题上,却逸出了政治成见的常轨。
不过,即使这封信的设计成为事实,也仍然只是土改中的一个个案。而且是借助于那三位当地当权派的运作才能成功的。这在我们的认知中,仍是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常态,也是一定程度上“官本位”或“党本位”(因为写信的当事人与受信的三位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无疑)作用的结果。一般广大的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的中国人,是连这点可怜的侥幸都没有的。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一个也是土改中的事例。
事例的主人是著名苏联文学翻译家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老人。上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曾应曹靖华之请,为老人写过一篇《教泽碑》,表扬他为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老人一直生活和执教在河南伏牛山区的卢氏县。1946年内战爆发,从鄂北宣化店突围的中共李先念部一支三千人的先头部队,来到伏牛山区时人地生疏,钱粮不继,借重于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曹植甫,联络当地士绅,稳定民心,使筹粮工作顺利进展,部队粮足饭饱,士气高涨,打出了军威,稳定了初建的豫陕边区政权。1949年建国前夕,国民党军刚刚退去,经历了“拉锯”惨剧的深山区人民,对新政权能否巩固将信将疑。曹植甫老人再次走出草庐,四处奔走,寻找教师,立即开学。在10月1日马耳岩庆祝建国的村民大会上,老人和驻军首长一起讲了话,号召山区的父老兄弟跟着共产党走。
就是这样一位从心底拥护新政权的老教育家,却在不久开始的土改试点工作中被划为地主。在这之前,曹靖华还给老人来信,要他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个思想准备,信中说:“不久故乡就要随着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望阖家欢迎,全心全意鼓起全身的气力的欢迎。因为土改是最好不过的,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老人欲加入欢迎的队伍已不可得。划为地主后,他就从马耳岩村搬出来,又住到当年为躲避国民党骚扰而住过的鹳河岸边的草房子里。土改工作队里有位老教师,因仰慕而来访,老人把多年来自己用毛笔抄成两厚本的儿子来信《靖华手札》给他看。老教师坐在老人的土炕上看得入了神,并深为曹氏父子间的亲情所感动。没想到他回去受到严厉责备,问他“为什么到地主家里去”?批评他“划不清阶级界限”。
在成分问题的震动中,曹靖华1951年去南方老根据地访问途中,从汉中专门给父亲发来一信,信中说:
日前儿函询关于家中土地改革,是想要知道依此划的成分对不对?因为你我父子阶级,依法令,是均不能划为地主的。你一生主要是笔耕舌佃为经济,而非靠生产农业作营生,是专门用脑力的知识劳动者。说到儿我的本身,行年十四即出外,迄今总算起来,脱离土地生活已四十余年,无昼无夜无寒暑,伏首芸窗,委身砚田,除执教中外大学外,抽暇编辑译著:一方面努力为青年储蓄精神食粮,一方面为国家除旧增新,倾心干革命工作,并不曾依赖土地,更不能算是地主。且今日大学教授,尽入全国工会(儿亦为工会会员),属工人阶级。未知故乡公民将你的成分仍划为地主否?这些地方,当局恐不尽彻底(了解),安知成分划错,是常有的,是当改正的。
1951-1952年之交,曹氏故乡进行土改复查。春节时,卢氏县扩干会上传达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指示:根据曹植甫老人毕生献身山区教育事业,他家里虽有少量土地出租,够不上地主,只能是个“小土地出租者”,以前错划的成分,应予改正。
如果只靠曹植甫老人在当地向复查工作队申诉,不一定能惊动得了省委书记下达指示。然则很可能是曹靖华从家里了解情况后,直接“上书”给河南省委,用今天的话说,是“越级上访”,碰上吴芝圃知道曹靖华是何许人,也读过鲁迅为他父亲写的教泽碑文,于是问题迎刃而解。但这也有赖于被错划者是知名人士。有些地方负责复查工作的就是原先的工作队员,他们是不是能够那么顺畅地解决问题?在中国盛行“屈死不告状”的传统思想影响下,有多少被错误处理的人懂得上告、申诉,有勇气且能够上告、申诉?又有多少上告、申诉者能够如愿顺利地改变错误的决定?这些就不是我们所能确知的了。
关于曹氏父子的这一段故事,是我从《张羽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版)上册中《山区教育家曹植甫轶事》和有关曹靖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的。
2009年3月11日
(《随笔》总第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