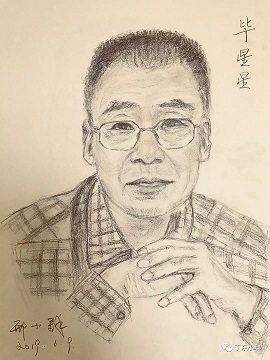《三上桃峰》是一出晋剧,经历过“文革”大风大浪的人们都知道它。地方戏流播的地域有限,晋剧也就在山西省中北部及其周边一带地区演唱。但在“文革”中间,《三上桃峰》事件却是一场翻卷政治风云、牵动全国视听的大事件,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山西省界,震撼全国。至今翻检“文革”历史,“1974年华北现代戏会演”,仍然是国人记忆犹新的话题。
《三上桃峰》成为《三上桃峰》,有一个复杂的诞生、完善到爆炸的演变过程。
《三上桃峰》的源头,应该追溯到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匹马》。说的是河北抚宁县一个村子,把一匹病马卖给邻村生产队,发现以后,几次追讨赎回。两个村子友好互帮的故事,在当时被赋予“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时代新风来颂扬。山西晋中青年剧团编导许石青,社教运动运动中下乡就有过类似的生活积累,曾经编演过一出小戏,剧名就叫《一匹马》。许石青抓住这个题材再度创作,先后改为《桃李争春》《当代新风》演出。剧情人物丰富了,场次也成了五场。中路梆子可说大戏了。嗣后再修改,省文化局委派戏研室杨孟衡帮助,定名为《三下桃园》。“文革”以前,《三下桃园》在山西各地各剧种都有移植演出,成为一出影响较大的现代戏。
“文革”中间只能演出“革命样板戏”。样板戏都是京剧,京剧覆盖全国,但一地民众喜好的还是当地的地方戏。除了以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演出外,各地也演出一些自己编创的地方戏。当然这些编创,一定要严格依从样板戏的创作演出法式,亦步亦趋模仿,不得越雷池半步,地方戏的特点减色不少。即使如此,当地人还是偏好观看当地的戏。这就为一些地方戏的艰难生存留下了一小块自留地。当局感觉到京剧不能一统天下,也就容忍各地有限度地编演一些适合当地口味的曲目。“文革”期间各地的地方戏调演,一直到文化部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戏曲调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下桃园》公演以后,由于这种你推我让的君子之风容易出喜剧效果,各地评价都不错。“文革”号召“十年磨一戏”,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戏定了型。适逢吕梁地区会演,地区就把这个戏拿过去再加工。其时山西省话剧院的一批编导恰好在吕梁下放劳动,地区抽调了治黄办公室的李旦初和许石青一起改剧本,李旦初是个摘帽右派,发配到吕梁,右派有文化,能写的多,他是有名的笔杆子。省话的专家方彦等人帮忙排演。剧本情节没有大动,只是把故事的背景改在了吕梁山。《三下桃园》的背景在晋中平川,故而有“三下”而且“桃园”,故事搬到了吕梁山,自然成了“三上”而且“桃峰”。吕梁地区会演以后,各路领导专家也都肯定了这个戏。
这个时候,山西省文化局已经开始筹备参加1974年的华北地区调演。“文革”中文艺园地百花凋零,参加全国调演是政治大事。省文化局领导同样选中了《三上桃峰》,委派杨孟衡和许石青再次合作加工修改剧本。其实这个剧本改来改去,不外买马、追马、夸马、赎马、赔马这个基本的套路。适应各个剧团男女角色演唱能力,剧中人当然要做相应调整。台词道白自然也会打磨精细,精益求精。1974年的1月28日,文化部举办的华北地区现代戏会演开锣,山西省带着这台晋剧参加了会演。
山西没有想到精心准备的大礼恰好撞在枪口上。其实就在看戏之前,江青控制的文化部就已定了拿《三上桃峰》开刀。山西省带队领导陪同文化部观摩组一起看戏,《三上桃峰》有轻喜剧色彩,演员表演时有开颜之处。文化部观摩的于会咏等人一个个拉长着脸,神色严峻。演出结束,也不上台接见演员,匆匆离开。这一切,都让山西人感觉到大事不妙。
演出不久,文化部那边很快就传出了爆炸性的消息,《三上桃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大毒草,这出戏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理由是:1964年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曾经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文革”中刘少奇已经打倒,“桃园经验”也已经一批再批,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经验”。这个时候,你竟敢“三下桃园”,这不是为刘少奇招魂是什么?虽然你改成了“三上桃峰”,改名恰好证明你心里有鬼。改头换面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掩盖其反革命本来面目的障眼法。兴致勃勃进京的山西人顿时恰似挨了一重头闷棍。咱们是为了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风进的北京,怎么一不留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在山西反还不够,竟敢带着大毒草到北京来反,这才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三下桃园》是创作修改剧本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剧名,以许石青的本意,剧本和“桃园经验”毫无关联。后来的剧本加工沿袭了基本情节,依然和刘少奇王光美不沾一根毫毛。但这时找谁说理去?“文革”中的“革命大批判”汹汹滔滔,不讲道理也不容置辩。一旦上头定了调子,全国上下一哄而上。依照文化部拟定的批判思路,各大报刊纷纷揭露批判《三上桃峰》的包藏祸心。硬要把一出本来普普通通的地方戏,加上骇人听闻的罪名,把老老实实编戏演戏的文艺工作者押上台声讨审判,这就是那个年月的荒唐景观。
翻开1974年2月左右的报纸,那一个时期,全国舆论的重点就是声讨《三上桃峰》。于会咏在揭批会上指斥《三上桃峰》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文化部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计划,报告江青批准部署实施。《人民日报》带头发表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的文章,全国28个省市各大报都刊发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实名的化名的一起上阵围剿,从著名演员到大字不识的工农兵一齐声讨。大黑字体,大版面,长篇评论,无一不是指斥《三上桃峰》的包藏祸心。省市报纸不敢怠慢,各地都组织了大批判组,安排口诛笔伐,仿佛一个戏,会动摇了无产阶级的铁桶江山。被卷进这场厄运的干部群众难以胜数。《三上桃峰》成为继反党小说《刘志丹》以后文艺界又一宗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批判狂潮里,河北抚宁县原来买马卖马的两个生产队扛不住了。买卖双方都是农民,无可揪斗。那匹马却是为刘少奇招魂的“铁证”。经手买马的农民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此时,这匹马已经转卖到张家口,生产队又将你推我让的那匹马揪了出来,现场批判。一开始还是文斗,面对老马批判《三上桃峰》。接着武斗,轮番鞭打群殴。生产队想把老马送出去,可这个时候谁敢要?王光美蹲过点的桃园大队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追踪“一匹马”的踪迹。张家口方面的兽医担心事情越闹越大,终于有一天给马注射了毒药,毒死了事。这大约是“文革”株连案中,死于暴力批判之下为数不多的一个畜类。
《三上桃峰》这场无妄之灾由山西引起,山西自然首当其冲。山西省领导犯了重大政治错误,主要负责人谢振华检讨下台。文化部门主管戏剧的贾克卢梦李蒙等一干人难脱干系,一网打尽。检查批判,拼命给自己扣帽子,难以过关。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类型的批判斗争会接二连三。汇演期间,《三上桃峰》已经定性,成了大毒草,文化部要求剧团继续演出,“供批判用”。一班青年演员台上痛哭失声,主演王爱爱当场晕倒,这才停了演。
山西文化局刚调来一个青年干部叫赵云龙,因为看不惯“三突出”等文艺理论霸道横行,写了文章提交内部刊物商榷,此时当然躲不过去,上纲上线,成了为《三上桃峰》“炮制理论根据”。赵云龙只不过从文艺的基本功能出发,提出“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就欠妥当”。“文革”极左文艺理论横行天下,赵云龙当然是太岁头上动土。于会咏在讲话中多次怒斥施压,《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纷纷撰文公开批判“欠妥当论”。赵云龙多次检查,压力太大,在声讨的声浪中留下遗言上吊自杀,头脸碰到暖气片子,满脸血污惨不忍睹。他是江苏人,交通不便,夫妻反目揭发批判,死后迟迟不能收尸,同事们敢怒不敢言。革命大批判批死了人,在1974年以后,已经不多见了。
《三上桃峰》在山西,株连的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人。“文革”中间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成风,《三上桃峰》又给了一个罗织罪名的题目,深陷这场无妄之灾的人,实在难以计数。这一场政治风暴由山西而起,刮回山西,山西当然格外卖力清洗自己,以期赎回罪过。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的剧团,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请过剧团演出的外交,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处分,就连看过演出的观众也要检讨。
批判《三上桃峰》,山西的任务是揪出“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批准者支持者主要指当时的山西省领导谢振华王大任等人,他们已经承担了责任,谢振华因此离职。这三个层面,有区别也有联系。“炮制者”主要指山西省文化部门的艺术领导和专家,比如贾克卢梦等人。主管戏剧的领导贾克从头至尾狠抓《三上桃峰》的加工修改,从选戏到加工修改定型,贾克善始善终,朝夕监督,艺术加工也有好点子。《三上桃峰》的成功贾克脸上有光,这会儿世易时移,棋局惊变,贾克当然成为头号罪魁。回到太原后,立即被隔离审查,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二十多天。子女和侄女都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十五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因为黑帮子女备受歧视欺侮。
山西省晋剧院代表山西进京演出,编剧杨孟衡当然难辞其咎。在北京调演的揭批会上,就经历了多次面对面的“拼刺刀”,无限上纲已在题中,种种凭空诬陷栽赃的不实之词也乘机抛洒出来。回到太原,在大字报的密林中行走上下班,办公室被查封,抄走了有关“黑材料”,家里也来人清查过。研究处理,杨孟衡被下放到闻喜县东鲁大队插队,实为变相劳改。领导再三吩咐:要以劳动为主,改造思想!一年以后才获得了一个“工作队员”身份。换到晋北继续下乡。
远在吕梁的李旦初和许石青也没有好日子过。凡涉及《三上桃峰》一案,一律集中在地区“办学习班”。在“文革”中间,这是一种变相拘禁的方式。集中吃住,不得离开。地县领导检查“我们对文艺队伍现状不了解,用人不当”。李旦初、许石青,还有剧团负责人贺登朝等人由军代表监督,检查交待,互相揭发,一直到查清问题,“提高认识”才能获得解脱。
许石青生性软弱,逆来顺受。一直努力深挖“反动思想根源”。倒是种种不负责任的指控激怒了李旦初,他找到军代表,拍案而起,逼问:《三上桃峰》有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我顶多是个炮制者。光拿我交得了账吗?我是摘帽右派,你们谁不知道?你们用我,能由我吗?今天关了我,我也只有一床被子,夹了就走!
这个湖南汉子,爆发了火辣辣的血性,终于使得整人气焰有所收敛。
学习班随后散了,关于《三上桃峰》的罪过却负重如山,一直压在他们身上。
直到1978年,思想解放的春风终于吹到娘子关。北京报纸呼吁为赵云龙平反,山西才开始解放干部。1978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报告,以中央文件形式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不过,这些作者们尚未听到传达。
1978年9月2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新闻节目,杨孟衡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喇叭播出了一个激奋昂扬的声音:“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文章:《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
广播首先播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三上桃峰》事件是一个大政治阴谋。是“四人帮”极其亲信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污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由此遭到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平反昭雪……
“文革”的特殊经历,让《三上桃峰》成为一出名剧,提说起来无人不知。而问起《三上桃峰》的作者,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明白。
《三上桃峰》由原创到不断修改加工得过程中,介入的力量太多,插手的人太多,以至于要完全厘清来龙去脉,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最早的《一匹马》改编本已经杳不可寻,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许石青改编的。
《当代新风》尚存有1960年代的钢板蜡纸油印本,封面说明“晋中青年晋剧团编”,“根据通讯《一匹马》改编”,这也是许石青改编的,没有争议。
1966年第一期《火花》杂志刊登《三下桃园》剧本,署名:晋中青年晋剧团集体创作、执笔:许石青、杨孟衡、张正申。
1978年《三上桃峰》平反以后,《吕梁文艺》刊发了吕梁地区的演出本,署名为:晋中地区晋剧团、吕梁地区柳林县晋剧团、吕梁地区孝义县碗碗腔剧团。集体创作。执笔: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
山西省文化局赴京参加华北地区会演本,由于甫一出笼就被打成大毒草,署名为:山西省晋剧团集体创作。不过一般都认为杨孟衡、许石青编剧。
许石青,1925年出生在山西孝义县东许村,民国时代读过教会中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地县剧团担任编导,排演过《游西湖》《下河东》等名剧,是山西著名的地方戏编演专家,一级编导。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种种“历史问题”,长期抬不起头做人,《三上桃峰》事件雪上加霜。
李旦初,1935年出生于湖南安化,读武汉大学时打成右派学生,分配时发配到山西吕梁山。以文字为业,工诗词歌赋,著有《李旦初文集》五卷。后来出版文集时,郑重地收入了《三上桃峰》剧本,排许石青为第一作者。
杨孟衡,出生于湖南祁县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参加解放军文工团,1955年转业到山西,长期在文化部门从事戏剧创作研究。三人的人生轨迹在《三上桃峰》交汇,也是一段难得的缘分。前世今生,冥冥之中有命运牵手。
这三个成型的演出本,在山西,一般分别称之为“晋中版”“吕梁版”“太原版”。这是《三上桃峰》在演绎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本子。
可以看出,《三上桃峰》原创是许石青,“晋中版”“吕梁版”他都是第一作者,“太原版”他也参与了创作改编。三个版本,一母同源,许石青是打通三个版本的唯一作者。不仅如此,许石青还是晋中版吕梁版的演出导演。至于其中的导演音乐舞美合作,改去改回,丰富精巧,献计献策,一字之师,种种曲折,难以尽述。人们已经不可能复原历史的一个个细节。世易时移,大而化之。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创作”了。持续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文艺作品出版演出,已经不能署作者个人名字。经过多次暴烈的打击,文艺界见“三名三高”(名导演,名演员,名作家;高工资,高待遇,高稿酬)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远。发展到“文革”时期登峰造极,那就是,作品属于全社会,任何作品改编无须原作授权,原作者也不敢不同意。作家艺术家创作表演,一律没有报酬。既然所有作品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得署个人姓名。署名“集体创作”是“文革”中常见的署名方式。率先推出的那一批“样板戏”,一律标明中国京剧院或者北京京剧院等“集体创作”,上行下效,各地纷纷以某团“集体创作”作为署名规则。电影创作,有署名“第一创作组”“第二创作组”的,反正以不让观众看出是谁编剧为原则。至于报刊发表作品,“文革”中除了集体署名如某厂某社大批判组外,流行以寓意谐音署名。如“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校;“罗思鼎”是上海写作组寓意“革命螺丝钉”;红城是北京部队寓意“红色长城”。此外还有借以献媚的,如江青曾署名“大海”,文化部写作组署名“初澜”;江青署名“峻岭”,文化部写作组署名“小丘”“小峦”,等等。了解了这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石青作为原创人,何以那么轻易地出让了改编权;为什么一出《三上桃峰》会出现那么多的改编本。每一次改编,分别有不同的作者参加组合,这是那个年代“版权公有”“无偿使用”的典型特色。
1978年《三上桃峰》平反,它的声音曾经一度响彻神州山水。遭冤屈,遭打压,从地狱站起身,它愤怒地呼喊,发言人全都是声讨、控诉。与此同时,在山西,《三上桃峰》的演出也一度风靡。好事的观众要看看,究竟一个什么戏,能招致江青大动肝火,整倒了那么多人。
经历了一段简短的火爆,《三上桃峰》复归平静。这一沉寂,就将近30年。
20多年,足以淘漉一代人。“文革”后拨乱反正,许石青1981年入党,担任剧团领导,后在吕梁文化局领导岗位退下,1999年去世。李旦初进入新时期金子终于闪光,经历了人生事业高峰。先担任吕梁高专校长,后又接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退在山西大学。人生终有登高一呼,也不枉快意恩仇。张正申退在晋中文化局,年过七旬。杨孟衡退在山西省文化厅,眼下是80岁的老人了。
《三上桃峰》没有长久沉寂下去。进入新世纪,有关《三上桃峰》的话题重新被人们提起。大约是厕身其间的那一批人年事渐高,回忆往事,想把这一段记忆留下来。
2004年,贾克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回忆《三上桃峰》事件的前前后后。此后,2009年,柳林县雷捷发出版《一剧惊天下--风雨三上桃峰》,杨孟衡也先后在戏剧网站发表回忆长文,诉说《三上桃峰》事件中的人和事。
《一剧惊天下》专说柳林剧团演出的《三上桃峰》,也就是吕梁版。既无来龙,也无去脉。在20万字的一本书里,许石青、杨孟衡几乎不出场,让人感觉《三上桃峰》和他们无关似的。杨孟衡的回忆文章认为,自己主导了《三下桃园》的编剧,执笔署名应为杨孟衡、许石青。至于太原版,杨孟衡说,许石青参与时间很短,执笔应署自己一人。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声音不那么和谐。谁是作者?谁该当第一作者?当事人神色严峻,回忆已经有了争鸣的味道。
只有许石青已经长眠不醒。他安静地躺在故里,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文革”留下的“集体创作”,是一笔巨额糊涂账。五花八门的笔名,汗牛充栋的文字,谁能享受历史的殊荣?谁又应该对失误负责?许多疑案将成为永远的谜团。人们已经清算了“文革”的种种罪恶,而这个“知识产权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当事人的离去,种种无头案会越来越多,这将是一份沉重的遗产。
我们也许可以明辨厘清,也许竭尽努力,最终没能划开无边的混沌。
(此文参阅许石青、贾克、杨孟衡有关回忆文章,在此致谢。)
《随笔》总第200期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