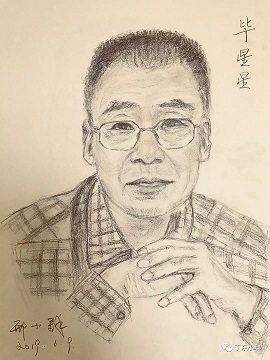1970年8月3日,一支解放军拉练队伍从山西河津行军进入临猗县,经过高头村。他们从涑水河以北走来,越过小石桥,河水淙淙流着,河岸芦苇正发青。部队走到高头村北庄巷口,遇到一个丁字路口,打前站的3个战士折了一根杨树枝插在浇地的水堰边做记号,指示行军方向。听说过队伍,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看热闹。正在生产队出羊粪的毕养功、毕成孩、毕安岗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欢迎解放军。路口就是北庄的粉坊,漏粉条的毕永安等五六人也不漏粉做豆腐了,出来给解放军送开水。粉坊大锅不开,听说后面还有大部队,他们加紧烧锅。不一会儿,大部队过来了。全村一群社员群众由老主任带领,到村口欢迎解放军野营拉练。大家高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送开水的,问候的,村头一片喧闹。部队也回敬欢迎他们的人民公社农民伯伯,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解放军和贫下中农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这是那个年代习惯说的话。这一场欢迎欢送,照例热烈友好,体现了父老乡亲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关怀无限爱戴。
长途行军,不是阅兵演习,一直齐步正步,还不把人累死?部队集合走路比较随便。擦汗的,歇脚的,边走边说闲话,队伍乱着,人也疲沓了,显得军容不整。小伙子们累了,扛枪姿势左右歪扭,队形也不是那么齐齐刷刷的。有一个小战士大概是个新兵,步行几十里,脚底打了泡,走路一瘸一拐,落后了,出来两个战友帮他,一个提了他的行李,一个扛了他的枪。大部队的后面,3个散兵,像拖了一个小尾巴。
部队就这样过去了。村庄,也许就这样继续平安无事下去,接着是吃半饱,磨洋工。
人们没有想到,这一队士兵过去,乡村爆出大案。
当天晚上,毕养功、毕成孩找到大队,举报毕永安反动言论。
他们说,当部队路过时,毕永安在一边看着,一边嘲笑讽刺:“看这一帮队伍,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就跟过去的二战区一样。”
“二战区”是阎锡山的队伍。抗战时期,山西划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他的晋绥军在本土抵抗。后来当地老百姓习惯把阎锡山的军政人员都叫做“二战区”。
大队接到举报,这种丑化污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可了不得,按规定要惩处。询问有谁在场,还有谁听见了,在这天即1970年8月3日,毕养功、毕成孩、毕安岗,都给大队打了证明材料,证明自己当场听到了毕永安的胡说。1970年9月21日,毕养功又一次给大队打了证明材料,重申自己8月3日的揭发。
3人揭发,按说可信。按照专案的规矩,两人以上揭发,视为证实。可是毕竟欢迎解放军那天,村巷里出去了那么多人,怎么只有3个人听见?大队干部心里有点不踏实。踌躇之间,这个查证就拖下来了。
事涉革命反革命,这个事儿当然不会不明不白地拖过去。1971年初,一打三反轰轰烈烈进一步深化。一打当头重点就是打击反革命行为,临猗县委派工作队下乡,公社来了工作队员,查处毕永安的反动言行,重新提上专案日程。有公社的工作队,毕永安的专案立即高速高效铺开。工作队和大队治保干部组成专案组,大面积调查毕永安事件的来龙去脉。高头村北庄,一场搅动小巷全体社员的政治大动员加温开场。
大队又一次找到毕养功、毕成孩、毕安岗,和每一个人单独谈话,做了详细笔录。笔录文件让每人看过,签字画押,有修改的地方,加盖红手印。每一次笔录结束,专案组都严肃告诫对方,要对自己的谈话负责,不得捏造诬赖好人。显然这是严肃正规的专案审查。3人没有犹疑,依然坚持前边的揭发。
毕永安当时在粉坊漏粉条,专案组找到在粉坊操作的5人,粉坊内外的6人,每个人都单独谈话,做笔录。识字的,签名画押。不识字的,盖手印。还有在粉坊附近看到过毕永安进出的,同样一一找到打证明材料。不识字的,找人代笔,念给他听,盖手印。只要在场统统查问。前后接受调查的有20多人,大致在1971年2月底完成。
但是除了那3个人,依然没有旁人站出来明确举证,证明自己听到过毕永安说过这个话。这些人或者说自己没听到,或者说自己到场解放军已经离开。总归是不再有人举证。让毕永安交代自己当天的言行,毕永安坚决不承认自己说过那句反动话。
毕永安到底放毒没放毒?大队还是难以决断。
公社大队还在犹疑,调查揭发活动却在发酵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2月10日,几个在毕永安家里打过扑克的邻家揭发,毕永安在家里偷电。有人看到他进县城买了一盘电炉丝,有人看到他扯了队里电线,通到自家炕洞里,插上电炉一冬整天烧炕。
2月11日,夏天和毕永安一起干活的几个社员揭发,毕永安还有其他胡说八道。6月收麦载麦,毕永安和他们一起装车,有贫农社员说:咱队下这几年就不依靠贫下中农,出头当干部的都是中农。毕永安狠狠顶了一句:贫下中农咬鸡巴哩?
这是当地的一句粗话,意思是顶个啥用?能咋了。
2月13日,几个社员揭发,毕永安趁着夜色,从粉坊往外偷偷担出五六担红薯渣。一家人偷吃生产队的红薯渣。吃不完偷着卖,投机倒把。
这场大揭发还波及毕永安的家人,另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员揭发,1958年,毕永安之父曾经悄悄找到他,给他索要一副马鞍。他爸说,这副马鞍是土改那时你分的,本来是我丈人的,我要还了人家。这是地主富农反攻倒算。
政治动员把群众完全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在睁大警惕的眼睛,随时随地关注敌情,为专案提供依据。
3月8日,三队社员毕养孩作证,有一次外出,他听见本队的一个要好的伙伴说,毕永安在村里说过:那是无意之中的一句闲话,就被养功咬住不放。由此证明,其实毕永安私下承认自己说过污蔑解放军那句话。
正在调查取证的节骨眼上,3月4日,毕永安和本队邻居在家里聊天,说到这件烦心事。毕永安还是那句话:咱无意中说了一句错话,养功就咬住不放。恰巧毕养孩进来串门,在窗外听到二人的对话。养孩立即退出来,飞跑去叫人一起旁听,意思是大家一起听到,举证就能算数。可惜再赶回去,人家已经不再说这个话题。
窗外有人,隔墙有耳,全村群众神经已经高度紧张。大家箭上弦刀出鞘,常备不懈,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为案件找得力证据。一村人随时准备抓捕铁证,毕永安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毕永安在干啥?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反复调查,他坚决不承认说过这句反动话。他找到大队,辩解说这些人都是和自己有仇,伺机报复。
“安岗揭发我,是因为1958年他母亲送进集训队,我爸批斗过。”
集训队是大跃进中随便抓人劳教的场所,不经公检法,公社就有权抓人。
“养功揭发我,是因为四清运动中,我揭发过他爸偷盗库房粮食。一回吵架,我骂过他们家净是贼没一些些夹带。”
“成孩揭发我,因为那年他哥偷偷轧棉花,让我看见了。”
在这场双方尖锐严峻的对峙中,毕庭怀和毕养功是本家,在大小场合附和毕养功,攻击毕永安。毕永安大怒,一天在巷子里遇到毕庭怀,毕永安大骂:“我反革命?搞什么活动啦?还不胜有人当过老阎的编村,当过土匪!”这当然是揭毕庭怀的疮疤。二人当即扭打在一起。两人都扇了对方几个耳光。节外生枝,大队紧急调解二人斗殴事件。
工作组还在调解,毕永安找了几个人,揭露毕庭怀早年在牛杜镇当二战区警察,有人命在身。大队不敢怠慢,立刻奔赴牛杜,外调毕庭怀1940年代在伪政权当差的历史。案中有案,案外有案,一波未了,一波又起。3月的乡野,杂沓的脚步,慌乱的眼神,到处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人群。1971年的春天,村庄一片忧惧不安。
乱了,完全乱了。现实的,历史的,个人的,家族的,各种矛盾搅和在一起,村庄完全陷进对立撕咬打烂账的泥窝里。你揭我的短,我骂你的街,你说我今天的不是,我说你昨天的丑闻。你举报我,我举报你爸你妈。反正谁也不得好过。村庄聚族而居,是一个稳定的居民共同体。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处,其间的恩恩怨怨,往往可以追索到遥远的历史深处。个人的家族旁系,又织成了横向延伸的人际关系网络。1970年代以前,村庄居民很少迁居,没有流动。友好亲近芥蒂龃龉结亲结仇,全记录在岁月的流水账里。这番一个反动言论案,哪里想到能搅动这么纵深这么宽阔的乱局,形成了极其严峻的面对。公社和大队,都有些头大了。
专案组让毕永安先写检查,自己交代,自己检讨,2月28日,毕永安交来了检查书。
检查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格式,纸张的顶天格,都要引一段毛主席语录: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今天斗私批修。我叫毕永安,自1961年走出学校门到农村,11年里,由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突出政治,所以犯了很多错误。首先说我是一个青年人,不能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主要思想根源是没突出政治。
另外我不能团结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主要思想根源是抱着只要自己不犯法,与群众团结不团结有什么关系。所以自己形成了非常孤单的结果。比如说和毕成孩一家,毕安岗一家,毕庭怀一家,毕养功一家,毕虫娃一家,都不团结,都有矛盾。
毕永安在这里提到的,正是举证举报他的几户人家。他用家庭的历史矛盾,解释几个人揭发举报丑化他的原因。
在检查书的最后,毕永安表示:
最后我决心,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我们不剥开坏人的画皮,不搞清坏人的事实真相决不罢休。永远忠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结尾表决心,这是“文革”中间检查书的八股式套路。但这里毕永安显然有些不顶牛。
毕永安承认了辱骂贫下中农,承认了偷电,承认了投机倒把,但是,相对于丑化污蔑解放军,这些最多算一些落后言论,算不上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言论,他不承认。那3个人的证明,不够有力。怎么办?这个真把专案组难住了。
案件查处的戏剧性转折,出现在3月下旬到3月底。
公社和大队工作队,反复向安岗、成孩交代调查取证的严肃性,后果的严重性,一旦落实,毕永安将会以反革命罪论处,关进监狱坐大牢。经过反复思量,毕安岗、毕成孩决定撤回自己的证明。
两人都说,解放军过来时,我们是在场,可毕永安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亲耳听见。具体说了什么,是听养功说的。
安岗说,他刚开始打证明时,在家里说起,他哥就嘱咐他:你听见就说听见,看到就说看到。没有,不要乱说乱写。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去举报。
安岗说,他决定不举报了,给养功说,养功是贫农他家是中农,养功当下就斥责他:毛主席说你们中农就是动摇分子,一点不错。安岗说,你说动摇就动摇。
两人都说,在打证明材料前后,养功曾经几次找他们订正当时场面的种种细节,小心交代他们不要写错,要和自己说的一致。
两人都承认,他们的揭发证明,有挟嫌报复的因素。
这样翻来覆去的还了得,给清查造成多大麻烦?大队不能放过,责令他们检查。
3月27日毕成孩向大队交上检查: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三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找我谈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时我想,他们和我家不对付,安安还说要打我。就产生为了个人利益公报私仇来害毕永安。这不但是害安安,而是侮辱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到纲上来认识,就是政治上的犯罪。我自己因为有私人意见,没有站稳自己的立场。不应当听毕养功说,自己没有见到就不应该说,因为有私人意见,就跟上毕养功说安安,这都是怨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背了毛主席指示,我应当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请罪。
今后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好学习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改造自己的私字世界观,一定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办事,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永当革命人民老黄牛,一定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3月29日,毕安岗向大队交上了检查: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经过宣传队同志谈话,对我来说思想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我自己没有亲自听见,就不应该说成是我自己亲自听见的,在证明材料上写我自己亲自听见。1970年后半年有一次给地里送粪,到晚上叫驴卧下起不来,毕永安他爸是饲养员,他说我把驴使出了病。驴腿是老毛病,偏说我使唤下的。他指着我说:这回坐教育所也得坐(运城俗话管监狱叫教育所)。我这样做是公报私仇。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这一教导,使我感觉到听别人说变成是自己听见,是对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侮辱。解放军是国家长城,解放军洒热血,不怕劳苦,难道还能侮辱吗?我现在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感到跟上别人不结合实际乱写乱说,是对党和毛主席最大不忠,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大犯罪。
请宣传队和革命群众批评指正,把我从泥坑里拉出来,不会使我越陷越深。自己愿意今后做什么事情,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实事求是。我愿意永远站到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革命路线一边,永远革命一辈子,甘当革命老黄牛,拉革命车不松套,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青春的一生。
毕成孩、毕安岗阵前反水,对毕养功是致命一击。举证队伍顷刻土崩瓦解,只留毕养功一人孤立支撑。按照专案惯例,孤证不立。即使毕养功依然死不改口,一人举证已经不能定案。毕永安已经转危为安。
还不仅如此,风云突变,加剧了举证人群的分化。更多的当事人说自己“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成为反举证一方,举证队伍更加孤立无援。除了毕成孩、毕安岗的脱离反正,从3月29日到3月31日,以后又有10多人出面证明自己没有看见听见。原来针对毕永安的专案,此刻调转了方向,成为针对毕养功的专案。既然这么多人都没有听见,偏偏你个人听见了?你这是捏造事实,诬赖好人,妄图把好社员打成反革命!毕养功顿时由革命动力变成了革命对象,工作队目光如刀,逼视着毕养功,你的手段已经破产,快快交代你的居心叵测。
在巨大的压力下,毕养功3月31日也向工作队上交了自己的检查。检查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由来,交代了他和安岗、成孩几次联络,统一说法,修改一致串通勾连的过程。毕养功显然还在坚持自己的揭发,但是3人揭发小集体,当然已经不复存在。
毕养功在检查最后说:
我感觉,我和安岗、成孩做下这事,应该好好地给贫下中农交代。我自己错误在不应该活动成孩,鼓动安岗。我现在给贫下中农、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犯下滔天罪行,我感觉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应当把我的思想狠抓批判,使我在政治上行动上不犯错。
今后应当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把私字完全砍掉。从今后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最后让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养功、成孩都是小学毕业,安岗念过中学,他们能写出这样的检查,看样子费了不少心思。其中当然有句子不通,意思不连贯的地方,不过作文到这个程度,说清楚了。
举证一方四分五裂,毕养功独木难支。毕永安的反动言论案,至此可以以举证不力,查无实据结案,中止清查。轰轰烈烈朝夕警惕的公社和大队工作队,终于长舒了一口气。1970年高头村的一桩反动言论案,经历了悬心吊胆的几次起落,终于因为各方力量打了个平手,要挽起放下了。慢慢的慢慢的,它会沉没,沉没到无人知晓。
1970年的反动言论案,没想到余波袅袅,数年不散。
当年毕养功写证明材料,曾经还有这样一份补充:
解放军走后,我到马房,安安和几个人还说过。江江说,解放山西时,只有临汾运城最难打。打运城时,天上下大雾,对面看不见人,临汾叫卧牛城,可难攻。这时安安系着小围腰过来了,看到我们三人,他也坐下。这时宁孩说,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牺牲的人可不少。铁锁路顶桥(铁索泸定桥)在铁锁链下有的受伤抓不住铁索链就掉在水里。我接着说,那怎么今天解放军从河津过来累得那么厉害,有一个解放军把鞋脱下,我看见脚都走肿了。后面两个解放军背了他的枪和背包。安安这时接着说:这一伙乱七八糟和过去的二战区一样。不一会他就走了,他出门,有孩手里拿着一个馍,一边吃,一边正进小门。
这里的江江、宁孩、有孩,都是三队的小伙子。比功功大个几岁。运城当地给孩子起名字,常叫叠字,或者叫什么孩,什么娃。毕永安叫安安,毕养功叫功功。江江,宁孩,都是一个队里的小伙子。在村里,大家习惯叫小名。
听养功说的这些,前后连贯,有来去有细节。揆度情理,养功不像是瞎编诬赖人。可是就是没人帮他证明。
毕养功这口气一直憋着在心里。明明有人说反动话,怎么就查证不了?明明在场那么多人听见了,为啥就没人出面证明?他不信听党的话,响应党的号召揭发坏人,还能这样不明不白地不黑不白地落个没有下场。他痴心不改,遇事还要揭发。
1977年2月,毕养功又一次制造了一桩揭发案,他联合几个相好的,以“三队贫下中农”的名义,揭发本队队长副队长“不抓纲治国,不学大寨”。这一回,他们写成小字报,深更半夜分头贴到大队小队几个地方。本村人干的,大队很快就查实了。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大家对于大字报小字报早已厌倦,对于互相攻击揭老底早已经憎恶了。公社大队出面,查清了事件,让毕养功写了检查,严肃责令他回村好好劳动。
毕养功是一直散漫惯了的,对社里的活计,一向不怎么经心。集体化那时强调早出工,“早上五点半,一天两送饭”,天还黑的就要上地。他睡到天大亮了才慢腾腾踱到地头,问队长毕永孩派他干什么。永孩正没好气,便说:“没活。你天亮前干什么不来?”毕养功当即又吵又骂,被人劝下才回去了。中午吃饭回家,队长路过他家门口,毕养功怒气不息,从家里抽出一把圆头铁锹,抡起锹把,冷不防朝队长背后猛抽一棍,锹把子断成两截,队长被打伤了坐骨神经,当即躺倒在地。
大队对于这个屡屡挑衅惹事的家伙,早已经深恶痛绝。借着他手持棍棒打人,性质恶劣,齐心先把这个办成刑事案。大队很快向县公安局报呈案件审批,案件性质定为“行凶殴打干部”,群众意见一栏,大队填报说:
“一贯吊儿郎当,不服从干部领导,目无法纪,历任干部感到头疼。更严重的是,无理行凶殴打队长,影响极坏,民愤极大,走上犯罪道路。”
大队意见:应给于拘留教育。
公社意见:同意大队意见。
县公安局还是能掂出轻重的。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冲突案件。公安局确定传讯教育。
县公安局传讯毕养功,批评教育,强制改正。在高头村大队门口,将毕养功戴上手铐,在电线杆子上铐了一天,当街示众。也在儆戒,也在羞辱。
40多年过去了,当年查案时,毕永安26岁,毕永孩22岁,毕养功20岁,毕成孩18岁。当年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都60多岁了,年龄最长的毕永安,已经70岁了。
我是在前几年,接触到高头村的历史档案的。很快就注意到了毕永安和毕养功的这一案。乡村的档案无人理睬,也许它就这样躲过多次毁弃留下来了。回头翻看这些文字,分明还能还原那一场角斗,看到1970年代初期的那一场是是非非他扰自扰。
毕永安的档案材料,主体是辱骂解放军。内装养功、成孩、安岗证明,大队找他们三人两次谈话笔录,2月27日分别找10个当事人谈话证明,全部笔录。毕永安自己交代看解放军经过,毕永安两次检查书。其余,分为若干个子目。《骂贫下中农咬鸡巴》为第一子目,收集4人证明。《偷用电炉之证明》为第二子目,收存4人证明。《偷粉坊红薯之事》为第三子目,收录5人证明。《收马鞍倒算之事》为第四子目,收存两人证明。其余,还有9人没有看到毕永安在场的旁证,毕养孩偷听毕永安聊天的证明。案卷全部不下5万字。案卷的纸张,有正规的从有关部门领下的专用材料纸,大红字头,黑体印着毛主席语录,以下按被调查人姓名,证明人所在单位一栏一栏按规定填写。领下的正规证明纸哪里能够用。大量的是大队仿照专案纸格式自己油印的。这也不敷使用,只有直接上白纸。另外还有带格子的草稿纸,横格子的小32开纸片,显然是从孩子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还有手掌大小的纸片,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交代。乡村群众,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这些忙完了地里农活,回到家又得一笔一画歪歪扭扭吃力写出谁谁谁说什么谁谁谁没说什么哪天听到什么没听到什么的人们,心下有多少苦恼不堪言。规范和杂乱,正式的和代用品,来之不易的纸张,歪歪扭扭的字迹,半通不通的句子,隔三差五的错别字,这就是那个年代极具特色的乡村专案。
毕养功的案卷中,内装毕成孩毕安岗的撤回证明声明,二人的检查书,还有毕养功的检查书,另有在场而证明没看到没听到毕永安胡说的11人。至此,毕养功前后为此事写过大约5次揭发交代检查,应该有上万字。
大量的调查取证文字,自我检查,案卷收束超过10万余字。仅一桩专案,繁复到已经令人吃惊。我在这里列举,只能节录个别段落。
这些庄稼人,原本不是写字的,这会儿要在一段时间写这么多字,还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比下地干活要紧,这可说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中国的乡村,自古一直到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都没有实现严格的政治控制。所谓天高皇帝远,农民只要吃饭纳粮,说什么做什么政府管不着,说的就是这个。自1949年新政权建立,农村第一次实现了严格的政治控制。即使是边远乡村,政府的政治控制和政治影响也畅通有效。至文化大革命中,言论管制便成为政治管制的一部分严格落实。我们总习惯地认为,底层的管束总归要松弛一些。农民是一个最自由散漫的群体,一个农民说什么话,没有人关注,也就任他在广阔的田野放浪言行。“文革”时代,显然起了变化,毕永安随便说那么一句话,立刻有可能滑到反革命的深坑里去。这事确实给一村的农民敲响了警钟,即使在远天远地,也要把住你的嘴。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每一家院落,都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任何时候,任何言行,都不能出格。这就是“文革”时期社会管理的现状。地里打不打粮食不要紧,吃得饱吃不饱不要紧。说什么话很要紧,停工写材料写检查很要紧。现在想起来,奇怪得很呢。
一个土得掉渣的人群,突然一脚踏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在这里,一个农民不靠劳动,要靠说话写字证明自己进步还是落后,革命还是反革命。他们睁大惊恐的眼睛,不知怎样当一个老百姓了。
应该说,各级组织的社会动员是非常成功的。工作队一进村,立刻大发动,造声势。政治运动的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积极热情卷进了这场运动。你看毕养功等人,自觉揭发,反复揭发,只要认为属于反动言论,不顾情面大义灭亲立刻揭发不顾后果。这是典型的政治见义勇为。一个村巷,没有人认为调查毕永安有什么不对。基层的政权组织呢,对于政治清查政治整肃这一套也是热情高涨滚瓜烂熟。拉材料,写证明,做笔录,建档案,上报下达,这一套查办运作的具体程序,乡村政权竟也能熟练操作。侦破取证的技术层面的好多细节,一个大队小队竟也能上行下效,复制得一派真传。一旦启动政治专案,底层乡村立刻熟练地进入既定程序,这也是“文革”时代特有的极端政治化的形态。
无疑的,在这场和众多乡亲的较量对峙中,毕养功他们仗恃的就是政治正确。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揭发反动言论,这还有错吗?他政治挂帅,他突出政治,冲锋陷阵,很勇敢,很无情。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愣劲。依靠这种政治正确,可以因为某个人的一句野地里随口乱说就定人重罪,捕捉一个乡下农民的随口胡说,翻脸无情告到官府,以此为革命行动,在他看来理直气壮。关心国家大事,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号召。阶级斗争错综复杂,资本主义复辟就在眼前,人们当然满眼都是敌情。比赛谁的政治觉悟高,是那时最时髦的流行病。林彪副统帅所强调的所谓“非常革命化,非常政治化”,就是这个思想状态。底层的农民群众日常就是口无遮拦的,毕养功他们本人也是这样。可是在极“左”的革命气氛里,他们完全热昏了头。
毕养功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革命行动遇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抗力量,这就是传统的乡村伦理。
高头村的大多数村民,为什么没有一窝蜂跟着毕养功去证明,去揭发?他们奉行的不是一时的政治正确。他们奉行的是一种朴素的乡村伦理,是千年流传的忠恕仁义。一个人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错话,就能进大狱坐班房,斗得死去活来?这在他们,是万万想不通的。多年共处,他们知道某某不是坏人。大家都是乡邻,和睦相处最好。因为一句话让谁进班房,他们于心不忍。你要他们证明,他们只能装聋作哑,抽回身子。毕成孩、毕安岗为啥打了证明又抽回?也是感觉到了这种群体取向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乡村好伙计,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传达出乡村社会的态度,哪怕一个眼神,一个沉默,一声叹息,他们是会理解的。他们撤回举证,回到乡村伦理,是强大的乡村伦理,唤醒了他们的良心。他们阵前倒戈,终于结束了这场纷争。
所谓的政治正确,在这里分明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千年传承的乡村伦理面前,那个政治正确不堪一击。几番较量,终于败下阵来。
乡野盲目跟风的队伍里,毕养功就是一个典型。他顽固地把所谓政治正确坚持到“文革”以后。此时,革命年代渐行渐远,乡村已经厌弃了那些政治高调。最后那一铐,他因为打人让公安拘留示众,这好像和政治选择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为什么一个打人事件,大队要求严惩?为什么当大队要求严惩,没有乡民为他说话?乡村记着他的无情无理,记着他的致人于死地的凶狠蛮干。面对强大的极端政治化,乡野常常无力反对,无力阻止。乡野只有以沉默来应对天降的灾变,以冷眼来蔑视流行病一样的恶行。乡野的沉默,宏阔有力。有时候,袖手旁观就是最有力的反对。1970年的旁观,让毕养功的举报功亏一篑。1977年的旁观,不啻放任冰冷的手铐用刑强力审判。毕养功的拷问示众,不过是乡野一种不露声色的报复。乡野终于等到了机会,数年之后,伸手轻轻一击,就惩罚了这个迷途的儿子。
依赖一时的政治正确,想一想很危险。当政治正确还靠得住,毕养功输掉了宝贵的人情。当政治正确并不可靠,毕养功只能输得一干二净。“文革”10年就是这样。
一直到40多年后,我都闹不明白,毕永安到底说过没有说过那句反动话。还有,乡里乡亲的,他们后来和好了吗?
40多年过去了,乡亲们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吧。
在村里,我家辈分小。毕永安,毕养功,毕成孩,毕永孩,都是我的叔辈。安安比我大个四五岁,永孩同岁。功功成孩比我小两岁。村里习惯,安安、永孩我要叫叔,功功、成孩比我小,就算了。
秋凉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天傍黑坐在门前,男的女的就都围过来谝闲话。永孩和几个留守的老女人都在。
我问永孩:还记得功功打你那一棍吗?
永孩说:嗨,那家伙,二杆子。一点火就着。
二杆子是当地俗话,指一个人头脑简单,办事愣头青。
我再问:功功和你现在说话吗?
永孩很爽快:说来,咋不说。早没事了。
永孩说了一个事情。功功买了一辆崭新摩托车。那货喜欢在村道上飙车。村道坑坑洼洼,小路又窄,他不管,推了摩托,带上永孩,一踩油门,疯跑起来,一头钻进枣刺窝。旁边的人看着吓得半天不敢出气。一会儿功功满脸是血嘿嘿笑着就从圪针窝里钻出来了。划破一点皮,没事。全村都知道,和永孩,早和好了。
我问大伙:安安叔那事,到底有没有啊?他说过那话吗?
永孩说:咋哩没说过?就是说过么。大家不证明就是了。
几个女人也说,说过哩,说过哩。没人的时候,他承认,说过哩。
成孩也在一边。他什么也不说。那是,在那场风波中间,他很尴尬。
功功在村里开了个理发店,小店里整天挤满了人。避过人,我暗暗问他:
还记得1970年你举报安安吗?他到底说过那话没有?
功功不在意这个事,他不避大伙,大声说:你还知道这个事。肯定说了嘛,我还能冤枉他。
我接着问:你和安安现在说话吗?
他说:说来。
顿了一下,他又说:说来,不多说。
看来,40年前村庄撕裂开的这条伤口,总归还是难以长平。
安安叔不在家,儿子把他接出去了。我没有能问他。
还要问吗?说了又怎样?没说又怎样?一句话定人重罪的岁月,早已过去了。
《随笔》总第217期 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