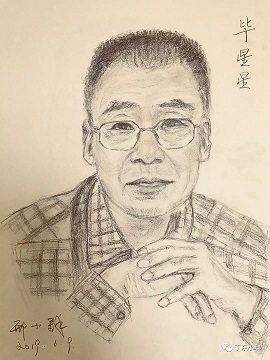我当兵到部队不久,接到外甥一封信,如同“文革”中所有的通信一样,高调亢奋斗志昂扬。他说高头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揪出了反革命分子马士祥。报呈县公安局,立即逮捕。
马士祥?就是那个操着一口河南话,在村里给人绱鞋的马士祥?不错,就是他。我打小就记得,他老两口带着一个男孩过日子。很奇怪,村里人都叫他马士。马士是土改前几年迁住到高头村的,抱养了别人家的一个小子带着。马士的老婆王小女太丑了,眯缝眼睛好像总是睁不开,左脸有一块牛皮癣,常年抓挠,经常是红一道白一道的,抓破了就流血,又脏又瘆人。
马士两口子在村里那叫窝囊。他是河南洛阳农村的,流落到晋南,所谓“外路人”,一口河南土话,当地人很是看不起。马士个子高大,却是没力气,干不了农活,挣工分只能顶个女人。他老婆王小女不下地,也很少出门,见天哼哼呀呀的闹病。得亏有个绱鞋的手艺,还能有点小补贴,日子过得淡味。
这回揪出马士,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家伙老早就是反革命。这个时候想起小时候去他家院子,穿过阴暗的门洞,屋底幽深,人看不清,他戴着老花镜,抬眼从镜框上头看人,暗处只听见一声接一声哧哧啦啦的麻线穿过鞋底,我就愈发相信马士祥是个反革命。那时看电影,凡是钉鞋的补锅的小贩游商,一般都是特务。
马士家在河南洛阳王疙瘩村,稍大一些,就跟着舅舅学绱鞋,游走到山西绛县横水。学成了手艺,勾搭上了有夫之妇王小女。舅舅发觉马士不学好,看马士就横眉立眼总来气。马士和王小女商量搬走,王小女要带上她的男人孩子。行走途中变了主意,马士回河南洛阳找亲戚帮忙,杀了王小女男人,一家三口搬到猗氏县高头村落户。这是1933年的事。
1948年猗氏县土改,马士分了房子分了地,满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可是15年过后,王小女的儿子已经长大,开始跟他妈要他爸。原来马士杀害王小女男人时,儿子已经9岁,记事了。马士惊惶不安,索性狠到底。他又一次和王小女商量,杀了她儿子。15年过去,小伙子24岁,马士哪里对付得了。马士又一次赶回河南,出30块大洋,雇用他的表弟侄儿,将王小女的儿子诱骗到闻喜县东镇的荒野里杀死。这是1948年了。
马士杀人残忍毒辣,理应惩处。可是今天我回忆这宗惨案,脑子里闪过的还有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农村乡野。那时的农民,活动范围够大。马士仗着年轻,多次奔走在洛阳、绛县、襄汾、猗氏几个县域,最后定居在猗氏县我们高头村,也不过是一种流浪中的栖居。如果允许,他还会迁移。他的一生在这样大的地域漂流,从晋南北沿到黄河南岸,几番脚步走过,尝尽了流浪的甜蜜。他也有他的卑微的爱情--我们经常嘲笑王小女的丑和病,为了这份爱情,他竟敢冒死出狠手。在黑黢黢的田野里,一双农民的脚步急匆匆穿过高密的庄稼地,鬼鬼祟祟的影子包着冲荡的血气,沉重的喘息在浓稠的暗夜鼓动着。一朵恶之花绽放。
倒是1949年后,农民被死死固定在合作社的土地上。马士中年以后,几乎不能出家门一步,最后一次出家门,是进了监狱。
告密这东西不能鼓励。马士一旦揪出,接着政治队长又举报,说贫协主任士忠士义兄弟也有命案。这两个老弟兄就在门边前。毕氏近几辈的辈分排的是“彦士天昌庭 ”,庭字辈我就得叫爷,士字辈老祖了。村里闹戏,年年士忠士义兄弟都要坐在台口,一个敲马锣,一个弹三弦。谁能想到他们能杀人,还是自己的堂妹。
早年士忠士义和叔叔一家同住。叔叔瘟疫死了,婶婶改嫁,留下一个堂妹当女。当女长大了,兄弟两个发落堂妹嫁了人。这个当女不好好过日子,整天东游西窜,胡乱勾引男人。1940年代农村时常过部队。日本人,皇协军,二战区,土匪杂牌军,要吃要喝。每当来了军队,当女就随了军,混吃混喝,晚上卖淫。1943年前后,当女最要好的野男人,是安邑县北相镇一带有名的混混子吕付吉。吕付吉干过皇协,当土匪,扛着枪走村过户,集市上吆五喝六,混得很神气,这一带没人敢惹这个地痞。当女名声太坏,士忠士义兄弟俩嫌她败坏门风,总想教训她,收拾了这个丢人败兴的家伙。也是命该如此。一天,吕付吉手持阎锡山七专署的介绍信,带着当女,到高头村催粮派款。自然要先到亲戚家坐一坐。士忠士义兄弟一看这一对男女就不顺眼,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两人都火气挺大,争吵之中带上了浓烈的火药味,士忠士义兄弟顿时起了杀心。在村公所,他们借故吵闹,说吕付吉介绍信是假的,抓过来一把撕毁,几个人当即把吕付吉捆绑起来。等到天黑了,兄弟俩又叫了两个大汉,说是押送到北坡七专署,质对真假。吕付吉没有起疑,六个人就这样上了夜路。1940年代乡村的夜,是真正的夜。没有灯火,没有声息。风吹芦苇,沙沙起伏。他们一行走过村路,攀上河堰,越过涑水河的小桥,终于来到高头村最北的地界,那里有一眼最偏远的浇地水井,叫赵家井台。四人提胳膊拽腿,抬起吕付吉,倒插了扔到井里。当女立刻明白自己活到头了,她哭着求饶:好哥哩,我再也不敢了。士忠士义兄弟不松口,指着井口说:不敢也不行。这就是你的最后地点。兄弟俩一人拽住头发,拉住衣裳,一人把住腿,后面两个大汉帮忙。当女和吕付吉被攒到一口井里。一桩杀人案从此埋压进高头村村史。抛尸,填井,乡野间农民式的暴力仇杀,多属于这类。
小队政治队长将这两宗杀人案秘密举报到大队,实在让大队又惊又喜。高头村的一打三反终于有了抓挠的。全国一打三反轰轰烈烈,农村也派了工作队。可是农村的“文革”,毕竟冷清得多。到哪里去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哪里去找现行反革命?工作队正在苦恼,有人举报,虽然是翻腾一堆干屎,总比两手空空强。大队乐得做出成绩交代上头。
高头村组成了专案组,开始内查外调。一干人马去了河南洛阳的王疙瘩村,去了马士学徒的绛县、闻喜县。马士的案子外调到闻喜东镇,当地一个70多岁的老汉只能证明:“1948年10月,我村东坡发现一具尸首,不知是谁,我叫人埋了。”士忠士义的案子就在身边,不用远走,可是目睹耳闻的当事人,也得了解周全。在兄弟俩的档案卷宗里,有当女他妈的证明:“9月25日和我说了,要26日在泓芝驿集上见面。就没来。往后再没见过。”关于吕付吉的身份,找几个高头村见过吕付吉的,他们说:“我问他,他说在解县七专署干着。”还有证明看到当女和杂牌军鬼混的。竟然还有一份证明自己和当女野地里交合过,“弄完了我给了她五块钱日本金票”。所有这些证明的效力都很差。
毫无疑问,“文革”中的案情侦查,主要靠口供。所谓的证明,效力都很差。主要还是依靠口供判案定罪。但是农村的档案,记载详细,留下了很多细节。依照常识判断,这两宗杀人案应该是实情。
“文革”中间的专案也不讲究什么法理。1970年距离马士第一次杀人,已经37年,距离马士第二次杀人,也已经22年。距离士忠士义杀人,也已经25年。依照法理,这些都已经过了追诉期。为什么又要大轰大嗡,高调处理呢?全因为他们赶上了一打三反。村里要呈报了显示成果。
但是“文革”判案,是典型的政治挂帅判案。“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办案”是当时的最高要求。马士杀人,纯粹是情杀。因情仇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丧心病狂大发作”,理当惩处。士忠士义兄弟,杀的是阎锡山军队,杀的是阎锡山七专署的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杀了就杀了。至于当女,她和坏人睡觉,和男人乱交,一个坏女人,杀了也罢。也不说她罪不当死。
两案处理结果,马士移交公安,判了16年徒刑,坐了十来年班房。老了病了,取保监外执行。
士忠士义杀人一案,因为杀的是坏人,士忠免于刑事处分,“在社员大会斗私批修”。士义免于刑事处分,“撤销大队常委,在社员大会斗私批修”。
其实这两起杀人,都属于刑事案。政治划线处理,区别很大。
想起来后怕得很,“文革”一打三反,一个村子的党支部,就能决定社员的生死命运。他们不懂法律,不懂执法,完全凭着高涨的政治热情来办案。一个时期几千人的生杀予夺,就由几个农民组成的支部确定了。这些案子,大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但是农民皮厚,冤枉就冤枉了,没人计较什么。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大抓阶级敌人,从北京到基层都在大力办案,想起来实在恐怖。
马士一个农民,坐班房也没有什么。在村里一个工分值两毛钱,他干一年不够交口粮钱。监狱里起码有三顿饱饭。士忠士义兄弟那个贫协主任,撤了也就撤了。他们最大的压力,还是乡亲们的鄙视。毕竟埋藏在心底的残忍,不愿意揭开曝了光。
今年五月我去成都见大哥,也是为了了解我们家族民国时代的旧事。在都江堰、在浣花溪,我们经常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哥长我20岁,民国时代的事情,他已经记得了。
一天大哥突然问我,你知道咱家40年代的血案吗?
这一时让我震惊。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这个家族,祖父一辈有堂兄弟5人。祖父早逝,父亲艰难长成。1942年,他35岁。祖父的兄弟三爷早逝,留下一个继妻,应该是我们的三祖母,我们叫他三奶。三奶守寡不久,忽然有一个男人进了家门。家里慢慢才知道,这个男人是国民党部队溃散的兵痞。他游手好闲,土匪一样,就靠打家劫舍过日子。这个散兵身上常装一支枪,当地人叫“折腰子”,折扳开枪膛,填上一颗子弹,能放一枪。村里人没见过枪,也够吓人。他到后院找三奶,要经过二爷的门前。一天他回来,二爷家的大狗,本来拿一根铁链子拴着。狗认生,见他就扑了过来,很凶猛。他拔出枪,当下一枪把狗打死,扬长而去。我们一家都很害怕。三奶找他的用意,也就是想仗势霸占了三爷留下的房产和土地。这个兵痞,白天在外杀人越货,晚上大摇大摆回来,在老院子里随意进出。我们家族都怕这个家伙说不定什么时候杀人放火,大家商量不如早除了这个害货。二爷找来我的父亲和三叔,要他们想办法。最后大家商量好,到邻村找了一家土匪股子,为首的叫永儿。说好日子,永儿黑夜带了十几个人来,父亲和三叔做内应,听到来人,悄悄开了门。永儿带人闯进去,砸破窗户,抓了人,捆上一块石头,扔到远地的井里。
永儿做完事,朝天放了两枪。表示有强人进村,土匪火并。鸡叫狗咬一阵,村庄重新平静下来。
以后,我们的三奶自觉无颜见人,回了娘家。
这一桩案子,当然不会这么平静就结束了。半年以后,永儿找到我家,说当初给的钱太少,他们兄弟没有打闹下什么,要追加报酬。明知他是要敲我们一杠子,那又有什么办法。家里都怕张扬出去惹事。为了筹钱,父亲把家里的粮食卖光,麦子、玉茭、谷子,凡能吃的都卖了。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全家吃糠。不等新麦熟了,剪了麦穗,搓掉麦衣壳,青青的麦粒子就拌着吃了。
父亲晚年给我们回忆过去,经常喜欢说一句话:那时是什么日子呀,白天防日本,夜了防土匪。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深切理解了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大哥给我说这些,一刹那我非常吃惊。毕竟以前所说打杀,总归是别人家的事。这一起杀人,就出在我们家族,就出在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之手。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年轻时他也能下了狠手,我万万想不到。
岷江就在身边汹涌流过,大哥的话像一条河流追溯到上游。旧戏里经常有面对大江,感叹历史:这不是江水,这是几千年的英雄血。乡间的血腥,何尝不是这样伴着岁月一路走来。1940年代以后,乡村的民间暴力,还是可以看到。乡村之外的暴力活动,也时常听到看到。
从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子看,1940年代,乡村的暴力打杀,比较随意,乡民之间有了恩怨,往往快意恩仇,打杀了事,求告官府的不多,大家习惯诉诸民间暴力。抗战时期,固然和地方政府无力管束领导有关,想一想,乡村民间不讲法治,率性打杀,随便结束人命,却也是有着悠久的传统。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中,考察了湖北麻城县从元末农民大起义到20世纪30年代700年的暴力史。他有个结论,在中国农村,民间对于暴力有一种可敬的、浪漫的甚至有趣的渴望。“暴力的规律,是在司空见惯的日常杀戮、残害和强制之上,添加了周期性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民间暴力文化内容极其丰富。麻城当地文献里,随处可见“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血洗”等标榜残忍的话语。这种暴力文化,通过史书编纂和集体记忆工具得以系统地再生产,再传播。在麻城,更加庞杂的集体记忆,在民间传说。它常常以诙谐的口气讲述过去的恶性事件,如宗族复仇土匪袭击等血腥行为。当地的地方戏也喜欢歌颂强烈的暴力和拼命精神。历史上的暴力活动实体纪念物遍布麻城各地,比如坟墓、石碑、堡寨、古战场遗址等,当地人讲起杀戮如数家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一种全面持久的暴力性地方文化。这说的是麻城,其实其他乡村也一样。
吴思先生最近提出了一个“暴力指数”“暴力浓度”的概念,他以常备军的比例为标准,测算出战国时代,社会的暴力指数是30%,到了晚清,就只剩下0.8%,很好地控制暴力,这是中国位于世界文明前列的基础。近世人们也越来越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暴力程度的减低。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一书开题的第一句话就大胆宣称,它“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这件事就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暴力呈现下降趋势”。作者进一步质问心存怀疑的人:“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算是进步?”的确,《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作者考察人类的历史的进步时,提出了以暴力下降作为度量这种“历史进步”的尺度。他强调人类社会处在不断“改善”之中,所谓“改善”并非指人类已进入某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减少使用暴力,减少个人所承受的苦难而已。
近代中国人饱受暴力欺凌,社会政治制度的迫害,家国苦难以及现实生活的种种折磨,却始终不曾有意识地把暴力的降低当作社会治理的成功的重要标志,把不施暴作为个人道德价值的明确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民间的暴力活动理应受到收敛和抵制。多数情况下,社会的暴力程度也趋向弱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清理暴力文化的遗产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暴力活动意识形态化,分为“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这就使得种种暴力活动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堂而皇之传承下来了。一旦气候合适,就会疯狂膨胀。“文革”中的全面内战,动用枪炮,大规模的武斗遍及全国,分明是1940年代暴力革命的回顾展。就是在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也可以时不时地发现民众的暴力迷恋症。上街游行,一语不合,拳脚相向。烧房子砸车殴打车主,见了日本车一律掀翻,说一句公道话就被扣上“汉奸”帽子。河南的群聚打架,北航教授怒打老人,都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平和不是常态,造反有理才是愿景。匪气、暴力和野蛮始终是不肯放弃的文化资源。社会治理中的暴力因素也日益浓厚。军队警察保安加上“朝阳区群众”的红袖箍,令人感到暴力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影随形,险象环逼。我们的制度、行为,仍然繁育着暴力的因子,这一点,值得警惕。
马士取保候审没几年,就死在家里了。而士义撤销大队常委、贫协主任以后,闷闷不乐,数年后也郁郁寡欢去世。
我们家族的那件命案,却是埋藏在历史深处,一直没有人提起。父亲和三叔在1990年代高龄去世。随着他们去世,这个家族也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巨大的秘密,被掩埋到了黄土层深处。
过去的那一页,大家并不希望看到,有意无意地,人们却还在怀恋旧日的打杀。
士忠老汉临死前几年,和我有过一次谈话。“文革”时代大演革命样板戏,旧戏一律禁绝。士忠士义老汉都爱闹戏,旧戏唱不成了,浑身难受。有一天见了我,他忧心忡忡地问:
你说这老戏就不能演了吗?
《打渔杀家》也不能演了吗?那可是杀财主的。
在他看来,只要杀财主,就能演出。杀财主,哪还有错?
他的家人我见过,问起那件杀人案,他们也是说得稀松平常,那号坏怂,还不该杀了?
“文革”中的杀人放火,这两年的冲上街烧车砸车,都打着一面辉煌的旗帜,呼喊着伸张正义的口号。我相信,种种暴力冲动驱动的人们,都有他们疯魔的理由。
民间暴力的基因还在,不知道何时还会犯病。
《随笔》总第221期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