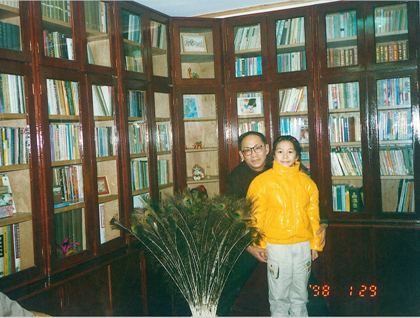知音梁炎武
林彪死后,出版界略有松动,我在郎溪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这套书还是1965年印刷出厂的,一直到1972年的春天,才准许在书店里出售。过去新华书店只有马列毛的著作,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历史书。这天,我刚领到四元工资,刚够买这套书,剩下的钱买了两只馒头充饥。
这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我以后一连九年几乎每天必看的书,里面的内容我基本上可以背出来了。
我走出新华书店,在路上碰到了梁炎武,我们原来在杨村是一个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碾米厂劳改。他见我捧着《中国通史简编》,也去买了这套书。
我问他:“你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还是对社会科学感兴趣?”
他手里翻着书,沉吟了一下说:“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社会问题不解决,自然科学也就不会用来造福人民。”他自称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他原是北大原子物理系的助教,广东人,身高一米八十以上,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他的祖父与黄遵宪是好朋友。
1957年,他与北大的谭天荣一起被打成右派,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与北大的林昭等人一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了七年刑,坎坷的命运激起他对社会科学浓厚的兴趣。
1967年春,我在杨村与他同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我很敬重他的人格和学问,为了交流读书心得,我常去他那里求教。
我去看他,他从冒着白色烟雾的厂门出来,头戴一顶蓝色的工作帽,脖子围着一条毛巾,满脸白色的粉,连戴着的眼镜上也蒙着厚厚的一层,眉毛上也像挂上了霜。他看见我很高兴,说:“你等一下,我干完就来。”
他喘着气对我说:“孔祥骅,你看看我这个搞原子物理的,现在成天在背包,这些简单劳动本来是一个文盲就可以做的。”
他陪我到他房间去,我看见他床头有许多书,有日本板昌田谈自然辩证法的书、有佛教禅宗的书和一些哲学著作。
1972年春夏之交,我去陶城分场看梁炎武,每当我对形势感到困惑时,就去找他,彼此交流对目前形势和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
他还在公路旁的一个碾米厂劳动,我带着借来的两册《资治通鉴》残本,转借给他看。
为了避免造反派的冲击,他刑满后一直不敢回北京探亲,等了五年才算等到回家的一天。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祥骅先生:
阁下惠赠的茶叶收到了。此次我回北京,见到了分别已有十三年的妻子和孩子,使我久已麻木的感情又重新苏醒了过来,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转眼又是妻离子别,悻悻然只觉得心碎而已!
人生在世,有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有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应该也可以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烦恼,但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
你借给我的《资治通鉴》,我看了觉得很好,我希望能再将唐末、汉末、宋末的那几本也借我一读,宋末的历史记载在《续资治通鉴》里,不知你能借到否?我看后一定如期奉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编写得非常好,很有司马光的风格,翦伯赞和范文澜齐名,但翦伯赞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于此可见范文澜先生读书比翦伯赞先生更通达一些,这一点我们是要学习的。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至于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精神境界,我看也只有他才能当之无愧!
然而此可与智者道而难与俗人言也!
梁炎武在这封信里提醒我读书要读通,宁静方能致远,只有读通了书才能避免一些麻烦的事,才可以明哲保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从那以后,我就更仔细地琢磨《资治通鉴》。
我在农场的朋友是不多的,也不可能多。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只能是“以心会友”!曹植有诗曰:“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需多?” 这年的秋天,我又去陶城碾米厂看他。我们在一起时,才谈得深一些。尽管我们处境险恶,但我们以读书人自许,有书相伴,自有一份超然。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从那时起,我们的心情开朗了,所谓“孟春三月,东风解冻”,中国的大地渐渐出现生机。不久,从陶城分场传来他平反回北大的消息。此后,我一直没与他联系。
知青忘年交
20世纪70年代,皖南山区有许多知识青年在此插队落户。
我们劳改的大田与知青劳动的田相连接,知识青年在地里采茶、锄草时,会好奇地走来闲聊。看到我休息时独自一人背靠大树读书,就向其他人打听:“这人是谁?怎么老是看书?”
农场里的人说:“大学生,臭老九,孔老二,书呆子,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读了书有什么用?”
但他们却主动跑到我这里来,与我聊天。
其中的三位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小冯、小齐、小蛮,他们当时在农村当民办教师。
一天我路过他们的住处,杨小齐见到我,就与我握手,叫我进去。
我一看,屋里木板的书架上有许许多多的书,这些书是我多年来想看而没看到的,有茅盾的书、巴金的书、雨果的书、诗歌,残本的《资治通鉴》、残本的《史记》《汉书》……
我大吃一惊,很兴奋,马上走到书架前开始翻阅,嘴里说着:“好书,好书。”
我与他并不熟,但这些书实在吸引我。
我说:“这些书你能不能借我看看?”
小齐不解地追问:“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看书?是什么动力促使你还看书?”
他诚恳地给我让坐,满眼的好奇,他真的很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只好简单地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
我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多书,他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都是红卫兵,抄家还收来许多书。两派武斗时,芜湖地委图书馆的书被拿出来修成工事,像碉堡一样,后来武斗厉害时要烧书,我们看看可惜,就拿了一部分书到家里,过了两年,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指示发表了,我们到农村来时就把这些书带下来了,当时要多少书有多少书,书扔在外面没人要。”
小齐很喜欢看书。他还看了很多古书,《诗》《书》《易》《礼》《春秋》他都通读过,他说看这些书不难,每天看一部分,一年到两年就能看完,我仔细地听他谈话,感到他很有思想。
月夜敲门为借书
几位知青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向他们借书,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那里,因为我是戴帽的专政对象。
农场规定,谁与知青接触,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可是他们老来看我,我跟他们讲:“我是戴帽子的,不能与你们接触。”但他们不顾忌这些,并对我说:“要看什么书,你就来借好了。”
劳改农场管得紧,场员不可随便离开六队,白天在地里劳动,不可以去周围农村,我要向知青借书,就只得在深夜里偷跑出去。我本是一胆小谨慎之人。但为了借书,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深夜十一二点,我躺在床上,听到周围鼾声四起后,就轻轻地从床上爬起,钻出蚊帐,把蚊帐关好,取出一双鞋子穿好下地,平时穿的鞋仍在床下,我装着去小便,偷偷地走出门外,经过四下打量,发现屋子里外没什么动静。
这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出了门就往西边急跑,一口气奔进松树林子里,我听见狗在我的背后叫,以为有人发现,劳改农场每个队都有守夜人,专门看夜里是否有人逃跑。我加快脚步在坟山堆里奔跑,突然我被绊倒在地,顺势我就在地上趴下,观察东边是否有人追来,见无人追,我又翻身爬起赶路。
我急急忙忙穿过坟山堆,又过了独木桥,到了蛇颈塘生产队。
到小齐住处我轻轻敲门。进门后与小齐对坐窗下,在黑暗中攀谈起来。窗纸在抖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突然站起,警觉地察看,担心有人跟踪而来。小齐听了听窗外的声音对我说:“不要紧,是风吹的。”
我的心慢慢定下来。小齐点起煤油灯,把我引到他的书架前,我向他借《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牛虻》及唐宋诗词,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还专门用报纸包好,交到我手上。
我对他说:“我是不能直接到你这儿来的,过些日子等我把书看完,我会向队部打报告去郎溪买衣物,路过你们这里时,我一定把书还给你们。”
小齐说:“别给你们的队长看到,他们会没收这些书的。”
我说:“请你绝对放心,他们就是拿刀架到我的头上,我也决不交出书来!”
于是我匆匆告别,按原来的路线赶回队里,再摸黑钻进蚊帐。
从此,我经常去知识青年家借书。一天下午收工后,其他人都在休息,我借来的书已经看完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我必须马上去还书。
我的心里着急,不知怎么的,突然胆大起来,借口有一样东西掉在田里,要找它回来,我向小组长请了假。哪知组里的王长发,怀疑我是借找东西去知青处借书,他报告队长说:“孔祥骅跑出去了,他报告东西掉了是假的,其实是到知识青年家去了。”
蔡队长一听说,就指示他们:“你们带绳子,把他捆回来。”
当我还了书朝六队走来时,正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绳子向我走来,我心里很害怕,他们恶狠狠地问我:“你老实交待到哪里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我去还书了。”
我迅速地跨进六队的地界,当他们用绳子捆我时,我突然大声一吼:“如果我在逃跑,你们可以捆我,但是我现在是站在六队的场地上,你们凭什么捆我?”
他们居然被我的吼声压倒,没敢再捆我。
蔡队长叫我去队部,他瞪着双猫头鹰般的黑眼向我嘶叫着:“站好,把头低下来!”
我连忙把头低下,这已是我多年来习惯性的动作,可是没等我把自己的脚站正,从蔡队长后面冲上来的张指导员,用他穿着的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朝我猛地一踢。
我差点被他踢倒,赶紧把双脚合并,站得笔直笔直。
“你到哪里去了?”
“我是去还书的。”
“还不老实,还要私跑农村,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还要去毒害知识青年?”
“我只是去还书的。”
“像你这种人,看书看得越多就越反动!到现在还在痴心妄想,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回去写检查!”
这是蔡队长最后的法宝,他每次对我训话后,就叫我写检查,所谓“检查”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蔡认为只要抓到我的不是,就叫我留下白纸黑字的检查,我的检查越多,就永世不得翻身。
我对写检查已无所谓了,反正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慌,死猪不怕烫,这类自我检查对我是一挥而就的,我是宁肯写检查,也不愿站在队部门口罚站……
我拖着被张指导员踢伤了的腿,一瘸一瘸地回去写检查了。
知识青年有时到农场六队队部打乒乓,几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与孔祥骅来往,他是戴帽的反革命,而且没有改造好,不要借书给他。”知青们不理睬这些,仍然借书给我。
知青中有位小冯还给我念过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来安慰我:
请坚持你高傲的忍耐,
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辛酸的劳动不会徒然,
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是我在中学时代语文课上学过的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普希金的诗,我听了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小冯认为我被打成反革命是不公正的,这些过去的红卫兵,现在的插队青年,由于生活处境的变化,他们也从造反的狂热中冷静清醒过来,插队农村后,过着清苦劳累的生活,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渐渐看个明白,因此懂得了真诚地与人相处,像朋友一样待我,自从认识他们以后,多了一些知青朋友,我的生活似乎变得有了些盼望。
假批儒读经
1972年春天,我从上海探亲后又买了一些书带回农场。
自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严峻斗争形势有所缓转。上海古籍书店又开放了,能买到一些线装书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许多书,但是,上海古籍书店保存的古籍书还是较多的。因为要搞批孔批儒,有些古书就可以买到了。在福州路书店,御批的《资治通鉴辑览》二十元一套,木刻本的《资治通鉴》五十几元。我用三元,买了一套小本子的《纲鉴易知录》,共十二本,字比半粒米还小,但刻得清楚,有批有注,皆历代名家高论。
我买了《王安石全集》,只花了三元。
还买了杜预注的《春秋经传集解》,还是一部线装书。
此外,还有北大的《论语批注》(这是批林批孔的产物,针对《论语》里孔子的话,进行批判),我把这些书带到农场里仔细地琢磨。
我看《论语批注》时发现,批判者在批判《论语》时都在原话中间加字,把意思改变了,再进行批判,比如林彪曾讲:“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们就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复周礼,又说是搞复辟,这种理解是完全不对的。
首先,这句话,有两个来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来源于《后汉书·李固传》的《与梁冀书》,李固为立嗣向梁冀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所谓立嗣就是指接班人问题。
“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和《左传·昭公十二年》。
由此可见,林彪所求与孔夫子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恢复西周政治家周公制定的礼乐文明制度,但也综合了三代礼乐文明的合理因素,注入了春秋时代“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至于林彪的“克己复礼”则是为了设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取毛主席的权力而代之。
我接触了“五四”以后一些学者批孔的集子,我的读书法是反面文章正面读,正面文章反面读,我发现钱穆、冯友兰 、郭沫若对孔子的评价是有价值的,他们对孔子的态度也是客观的,我觉得评价孔子不能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孔子是孔子,林彪是林彪,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不能把孔子与现代反动派联系起来,在这阶段,我又更仔细地研究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认为范文澜对儒家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为此我写了首诗:
简明通史说千年,
开我心胸洗我眼。
可惜范公乘鹤去,
宋元明清谁续篇?
求教朱先生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过一句话,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四件最好的东西,就是左史、韩文、杜诗、颜书。
左史,即左丘明的《左氏春秋》;韩文,即韩愈的文章;杜诗,即杜甫的诗歌;颜书,即颜真卿的书法。
所谓《左传》,乃春秋三传之一,从史学观点看,它是史中之经,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强。
我就集中精力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这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字句非常古奥,但如果慢慢地看,还是能够看懂一些,怎样可以研究透呢?
1973 年7月初,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求教,中文系将信转给朱东润先生,想不到朱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蝇头小楷的字写得密密麻麻,从笔迹上一看,可以肯定是一位老教授写的,我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
朱先生的信给我启发很大,他说:“《左传》这本书是儒家经典,它比《荀子》《孟子》,写得更好,更富有人情的抒写”。他将“人情味”的“味”字圈掉了,但还能看清这个字。可见朱先生是赞成儒家的,认为儒家要比法家具有人情味。当时批孔风起云涌,但他老人家能坚持真理。此后,我很仔细地精读《春秋左传》和《论语》,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我激动地给朱先生回了一封信:“我多少年来在农村读书(我不敢写在劳改农场),苦于无师指导,在自学的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您的来信使我在黑暗中找到了明灯,指引我读书的道路。”
我又向他求教如何读《二十四史》?此书是否买得到?研究先秦诸子应该从哪里入手?
不久朱先生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我对中国文学略知一二,至于诸子则知之更少,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有武汉大学的谭戒甫、山东大学的高亨、南京大学的罗根泽,《二十四史》正在校点,估计不久就可以出齐。”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专门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我读这部书,一共用了三年时间,从1973年一直读到1976年。
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求学。当我收到朱先生指点我如何读书的来信时,我是欣喜若狂的。
我在知青处找到了一本朱东润撰著的《左传》注本,我仔细地读了这本书,从1973年到1976年的三年中,我用功仔细琢磨着《左传》,我以为《左传》是“经中之史”,也是“史中之经”,我将《左传》里的典型史例与《二十四史》中与其或类似,或相近的史例进行比较,写了五六本读史笔记,这些读史笔记,我带到上海后,被母亲烧掉了。
我研究了《论语》,从批注中反推《论语》的原义,在批林批孔中,我的古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我还买了《二十四史文抄》,劳动休息时我就掏出来看。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