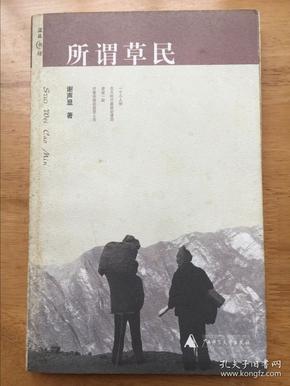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
一 看守所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川军将领杨森驻防万州时,曾在城北荒僻的山坡上建了座北山公园。后来因杨森败走,公园便逐渐荒废,有人就利用公园的部分地盘,修了一座小学。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大炼钢铁那一年,人民政府在紧邻小学的公园废址上,建了一座看守所。
如果站在城北的都历山上,随意向下一望,便能看到有一座好似“同”字形的灰黑色建筑依山就势地粘在市郊山腿上,只不过“同”字的外边两竖张开得象个“八”字。那就是万县市看守所。它外圈的“八”字形是架着铁丝网的灰色高墙,北边最上端的高墙内,有一座灯塔形状的了望塔,下面右边伙房外即是后门。“八”字内里的口字便是24间砖石结构的青瓦平房。万县市看守所每个仓的牢门都是朝室内开,除了门后那块约1.5平方米的水泥地外,室内都是离地80公分高清丝严缝的柏木仓板,人犯们吃喝拉撒都在上面。
我所在的16仓是个长方形,约18平方米。面临天井的那面墙上有一扇厚厚的牢门,门板中间有个约8寸见方,称为“风门”的了望孔。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还开有一个长约1.6米,高约0.4米,窗框内密密地装着姆指般粗细铁栅的透气窗,窗下靠墙放着土陶的马桶和夜壶。顺着稍长的两面墙,脚抵着脚地排列着两行铺位。由于看守所是依山就势地建在山腿上,不象在平地上的建筑,所以不那么规范整齐,天井北边就筑了两层台阶,有8个仓在两级台阶上。因此,房屋的面积也就难以统一,但全所除了两个单间外,其余的仓房也都在18-20平米之间,门窗仓板和马桶夜壶的安放完全一样。
修建这看守所时,当局者为了便于监管,曾特别要求设计者必需将所有牢房的木门和铁窗都一律朝向中间的水泥天井。这种设计确实方便了监管,里面的人们看不到背后的高墙和天空,就不容易胡思乱想。但由于空气无法对流,牢房里的气味常年便浑浊不堪。特别是夏天,由于不通风,关的人又太多,狭窄的牢房里就似蒸茏一样,闷得住在里面的人汗如雨下,经常有人中暑后被抬出去急救。文革时期,关在里面热得几乎晕倒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副市长就诚恳地感叹:“这监狱还是我当公安局长时主持修建的,当时我怎么就只考虑到要将人关得牢实,没想到住在里面会这么难受!”
监区最低处的南边也并非缺口,沉重的铁栅门外是一幢老旧的黑色楼房,三楼一底,百叶窗木楼板,还是修北山公园那个时代建成的万县市国立图书馆。“大跃进”后,就作了看守所的办公楼。万县市看守所的吊牌就挂在楼下的石门框旁。顺着坡儿下去10多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万县市中队的营房,市中队的主要任务便是警戒看守所。再下几十级石阶,便是公安局的后院了。前面抓,后面关,很方便。
虽然监狱和公园的性质相去甚远,但关在里面的和在里面关过的人却顽固地仍称此地为北山公园。进北山公园了;在北山公园里呆了多久。等等。
据说,各地看守所对牢房的称呼并不统一规范。或室或号或仓。各有各的叫法。
万县市看守所内称牢房为仓。
刘所长曾敞着制服双手撑在办公楼后墙的巡廊栏杆上,对排列在天井里的我们训斥:“老子就像个保管员,不问家伙们是什么案由进来的,也不管谁以后会被敲沙缶、谁要送去挖硫磺,还有哪些人会被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接回去;那些事儿都不该我管,老子只管收和发,进出数儿不错,就算完成了任务……”
看守所的牢房称之为仓,想来最确切。
文革一开始,我家便被官办的“红卫兵”抄了。不是因为作过资本家的父亲,被抄的对象是我这个青年工人。我20岁了,连共青团都入不进去的人,却被戴上一顶写着“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的高帽被多次批斗。
我17岁到贵州修铁路,文革爆发时,才回到万县市不满1年,又常在不同的工地上干活儿,能找到我什么问题?加之前几天我一看到城里有人被抄家,立即联想到读初中时自己那本日记引起的麻烦,当晚便将家里所有的书信笔记和一切写过字的纸都烧得净光,连纸灰都扔进了长江的激流中。因此,他们十几个人翻天覆地地搞了许久,结果除了拿走一堆国家办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新华书店卖出的小说,什么可以借题发挥的东西都没找到。
可见经验确实是最好的教师。
虽然抄家的人很失望,但运动初期各地的“文革领导小组”都是这样选取运动对象的。既然被上面内定了,我还是在劫难逃。说来现在的青年可能难以置信,由于从我家抄走的“罪证”只有小说,每次批斗会上的主题便是追查我读过些什么“封、资、修”的作品。
当年,全中国要求“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步子”。据说爱看书的人思想就复杂,就不好统一。有人就提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理论,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了“臭老九”,各地工厂农村,凡是平时爱读点书的人,无不跟我一样遭了殃。
我就只得每天交待几部自己读过的古典、现代、还有俄罗斯的小说,并简述一遍内容。因为当时认定,凡古代的都是封建主义,文革前的都是资本主义,而俄罗斯就是苏联,苏联的一切便是修正主义。连著作等身的郭沫若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自己以前写的所有书籍全是资本主义毒草,要求有书的人都将其烧掉。我那些买来借来的小说自然也全是宣扬封、资、修的毒草了。
每当我交待过后,主持人就煞有介事地翻弄一个本子,然后大弧度挥着手厉声喝斥我没有交待彻底。下面就喊口号:“打倒不老实交待的谢声显!”“顽固不化死路一条……”。第二次批斗时,我只得又交待读过的三两部古典、现代、俄罗斯的小说,还是简述一些内容。主持人又煞有介事地翻那个本子,厉声喝斥我没有交待彻底。下面又喊口号:“打倒不老实交待的谢声显。”“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虽然批斗会开得轰轰烈烈,其实我心里并不慌。哪些所谓毒素是我在人民政府开的书店和图书馆里弄来的,即使到了“运动后期”要对我进行处理,又能给我这个买书借书的人定个什么罪?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斗了四、五次。我每次都有新内容交待,有些参加批斗的革命群众也听得津津有味,在我简述毒草内容时还吼:“说详细点!说详细点!”后来,好象主持人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对之处,就宣布“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谢声显基本交待完了。”我还假积极地说:“还有,我还有中过的毒没清理完,要交待出来请革命群众帮助我彻底地消毒。”但主持人却不让我再交待了,要我老老实实在劳动中改造思想,等待运动后期的处理。
天凉之后,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肩负伟大领袖的嘱咐,纷纷南下串连,当时叫“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
万县市座落于长江三峡之首,自古川江不夜航。任何人由重庆乘船东下,都必需在万县港停泊过夜。因此,我们这临江的小城就天天有北京红卫兵上岸来。他们钦差大臣一样,大声教训地方官员,四处散发传单,在人群聚集之地宣传中共中央的《十六条》和10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小地方的人们就知道了官办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整我们这样的运动对象是“反动路线转移大方向”,“应当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地方官员们便被“中央精神”打闷了,惊惶失措不知咋办。干柴一般的群众便被北京来的火星点燃,纷纷响应号召,起来成立造反组织。很多当初被整的人都踊跃地投身进去,名正言顺地狠整那些刚整过自己的“形左实右派”。我却考虑到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敢去沾政治的边,就当了“逍遥派”,什么组织都没参加,一直老老实实地上班干活儿。后来在“牛棚”里,专案组内查外调地搞了几个月,竟惊奇地发现,我在文革中没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
武斗开始后,由于我天天还在木材公司工场里拉大锯改料,就被当时人们俗称为“保皇派”的人诬作“造反派”的暗探,抓进他们据点里几乎被活活打死。我侥幸逃脱后,就被逼上梁山,只好跑进造反派的地盘。为了能免费治伤和吃饭,就在派报《前沿炮声》里当了一名记者。8月份大规模的武斗告一段落,军队的支左小组要求搞大联合,3个本地区最大的组织就共同办了一个《江城战报》,我也被联合了进去。铅印的周二刊,邮局发行。
那时候真是运动不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我在文革中虽然自始至终目睹了所有武斗的经过,却从未拿起枪上过战场。我只写过一些通讯报导,后来又编过副刊。我虽然是一个身强体健的青工,在文革中却只搞过“文斗”而没有任何“打、砸、抢”的行为。但在1970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却在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被人们俗称为“牛棚”的集中营里面关了近半年。我的罪行是私下说过那位“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的尊容生得象奸臣。
通过多次批斗式的帮助,我充分认识到那句话的严重性,一旦落实,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也知道,这句话除了一个检举人外,专案组没找到任何旁证。当时我国虽然既无《诉讼法》也无《刑法》。但即使在那无法可依以言定罪的时代,仅一个人检举谁说了什么,而没有另一个人作旁证,除非被检举人自己承认,还是不能定案的。否则,人人乱咬一通,真要天下大乱了。因为没有旁证,为了逃避制裁,我就不管大会批小会斗,咬紧牙关抵死不认帐。还坚持说,我听那位检举人说过这句反动话。
在牛棚里的300多名“学员”中,我年纪虽轻,却是经历过几次风雨的“老运动员”了,以前几次又都被我侥幸滑脱。就自以为这次没被揪住尾巴,产生了骄慢之心,自然便有满不在乎的言语流露出来,就成了态度十分不好的一个。由于经常跟专案组唇枪舌箭,很多“学员”都暗中对我竖大姆指。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料此时上面又制定了一个司法原则叫“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也就是说,你不管犯了多大的事,只要掌权者说你认罪态度好,便可免于处罚。反之,不管你有无问题,只要得到一句态度不好的结论,就会受到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6日,在东方红广场举行的号称全市10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上,我作为“从严”的典型,在一片森林般举起的手臂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突然被推上台去反铐着双手,胸前还挂了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另有几个证据确凿的贪污、盗窃,武斗时杀过人的家伙,却因所谓态度好,被当场宣布“从宽”免于刑事处分。
“宽严大会”结束后,我和当天同台“从严”的18个人一起,被推上了驾驶台顶上支着机关枪的几辆大卡车,在刺刀雪亮子弹上膛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陪伴下,巡游了全城的主要街道。就直接被送进了北山公园的看守所,关进了第16仓。
我当时24岁,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
不知是由于当时抓人太多,办案人员忙不过来?或是因为我在牛棚里一直拒不认帐,认为我这案子还需补充证据?所以当我被抓进去后,就一直没人来提过审。我就象被遗忘了。
我进监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突然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我的罪行就自然不成立了。
那些年,北山公园内经常关有约200名人犯。除了那些流氓、强奸、盗窃、赌搏之类的刑事犯罪分子是随时在抓随时在判,判后即送往劳改的硫磺厂外,还有150多名“文革犯”被泡在里面。这常挂在办案人员和在押人犯口中的“泡”字真确切极了!泡菜坛里不是有10年20年的酸萝卜么?我进北山公园时,同仓有个朱必成,就已经被泡了3年多,他的卷宗内还是个拘留待审。
当时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风就吹得进去,雷都打不出来。”我就在北山公园里被泡了两年零10个月,直到1974年4月25日,才被无罪释放。
“文革”开后始,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击,然后就一直处于瘫痪。公、检、法机关自然也不例外,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一,由一个名叫“公检法军管会”的机构取代了。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切执法和司法的依据就是上面的文件和领导的讲话。说白一点,根本无法可依。
在无法可依的形势下,当年的司法界就有一句流行语:拘留无限期。
由于尚未定罪,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的正式名称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当年被称为“人犯”,而不叫犯人。拘留待审,就是说你还在等待审理。为了不妨碍侦查,你就不能享受劳改埸所的犯人拥有的劳动、通信、家属探视等权利。你得长年累月地被隔离在幽暗的囚室内,以免你与同案的家伙们串供。如果当时看守所内允许送进“红宝书”之外的书籍,那些什么都缺乏唯独时间富裕得难以打发的人犯中,很可能要出一些学问家。
在那特定的环境里,就因为无所事事的时间太多,就发生过许多特别的故事。
这里我讲一个我所在的16仓发生的故事,用一些草民的经历,来证明中共中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政策之英明。
二 16仓的早晨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2年初秋。
那天早上,开启铁栅门的哗啦声撕破了看守所清晨的宁静。胡管理员一跨进院内便照例一声大吼:“起床!”然后回过身去,仔细地锁好那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胡管理员沙哑的吼声刚传进16仓,王茂军便猛地从仓板上跳了起来。他匆匆将被褥靠墙叠好,飞快地在牙刷上挤了黄豆大小一粒牙膏,然后把毛巾和牙刷一起塞在盅子里,回身交给邻铺的高洁替他拿着。今天该王茂军倒缶子,出仓时他双手要提马桶。
动作更快的独眼铁开全这时已经跨下仓板,在门后那块狭窄的水泥地上趿上那双1年多从未洗过却并不见脏的解放鞋。他迫不及待地将脸塞进了厚厚的黑漆牢门上那8寸见方的风门洞,贪婪地用口鼻吸取天井外面清洌的新鲜空气。
“滚上去!”胡管理员从隔壁17仓大步走了过来。
独眼连忙跳回仓板上。
铁开全是个孤儿,自幼父母双亡。他与拾破烂为生的外婆在江边一间小木棚里相依为命,从小便跟着外婆在江边拾煤炭花淘破铜烂铁为生。独眼个头不高,浑身皮肤黝黑,结实得象个称砣。他没念过书,但特别爱听故事,他的学校就是码头边上那座临江的草棚茶馆。独眼一有空就蹲在茶馆角落里白听评书。他心目中最大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书人吴瞎子。他对吴瞎子的崇敬仅次于伟大领袖,经常挂在他嘴边的就是“吴瞎子说……”。吴瞎子的言论多年来几乎成了他人生的信条。铁开全将特别痛恨之人骂为淫贼,也是从茶馆书埸里形成的道德标准。1965年,铁开全刚满17岁,就被安排进一家内迁的军工厂去搞基建。那时他还没成独眼,双眼的视力都是1.5.
武斗时,铁开全的左眼被手榴弹的弹片炸瞎了,从此人们便叫他独眼。
1967年秋,大规模的武斗告一段落后,独眼这一派的勤务组在厂食堂里召集全厂职工开过一次“公审大会”。临散会时,顾司令在勤务台上庄严宣布:“……本厂勤务组,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杨京志,死刑,立即执行!拖出去!”
独眼就和另外两个“战士”一道,将前天俘虏的本厂对立派杨司令押到蓝球埸上,在几百人的围观下,立即执行了死刑。
进北山公园后,公检法军管会的代表曾在预审时问过他:“你为什么要杀人?”
“他被判了死刑呀!还出了布告,盖了勤务组的‘跺儿’(大印)的。”
军代表研究过独眼的裆案,对根正苗红困苦中长大的孤儿有几分同情,他不但没发怒反而面带微笑提了一糸列问题:“当时你左眼刚受伤不久还包着绷带,只剩一只右眼对不对?据目击者说,杨京志倒地之前连中两枪,一枪打在左脸一枪打在右胸对不对?你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打一枪后就必需拉枪栓退弹壳再上膛击发对不对?那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两枪都是你一个人打中的?一定有人打了另一枪?你不要傻乎乎地一个人兜着。”
独眼坐在预审室中间那半截埋于地下的水泥墩子上,他仰视着预审桌后面,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说两枪都是自己打中的。看军代表不相信,他竟然还提出借支枪来我表演给你们看。他这荒唐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
回仓后,他着实叫了半天屈。独眼不识好歹气呼呼地骂:“那家伙硬不相信老子出枪有那么快,他还说他是当兵的也在玩枪。他龟儿当的少爷兵打过了几发子弹?”独眼说,“当时,那两伙计虽然先开枪,但因为杨癞子面对我们站着,一对二瞳鼓得象牛卵子那么大,又扯着喉咙在喊口号,那两伙计就有点心慌手抖,两枪都打飞了。围在旁边看的人都还活起的嘛!老子头一枪打进他的膛子,趁了那淫贼朝前栽的时候,老子第二枪就打飞了他半个脑壳。当时好多人都给老子拍巴掌喝彩,顾司令还奖了老子一瓶五粮液。”
独眼就这么个家伙。在仓里连朱必成都从不惹他,说跟这样的浑人计较没意思。
他们的顾司令就关在第5仓,因“指使杀人”罪,后来被判了15年。独眼因“派性杀人”罪,同时被判了10年徒刑。许多受人指使犯了“派性杀人”罪的,杀一个人多数只判3年,还有判缓刑的。从同样是杀人犯们所判刑期的轻重,也体现了当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原则。
独眼刑满释放后,在长江边开了个小饭店,早已娶妻生子。他儿子不是独眼,听说在学校成绩还好。
胡管理员左手拎一大串铜钥匙,每走近一个仓门,便用右手的姆指和食指拈出一把,为了不让手指沾到牢门上那人犯们的脏手经常触及的大铁锁,他练就了一伸手便能准确地将钥匙插进锁孔的技能。“叭”地一声,弹簧跳开了。取锁和关锁的活儿是留给犯人作的,他又快步向15仓走去。
每天此时,各个仓内必定乱作一团。大家都在抖动和折叠被褥,那些经年未洗过的被褥散发出的臭味充满了狭窄而不通风的空间。然后,人们再用各人的卧具衣物等一切家当,仔细地靠墙摆设有坐垫和靠背能让人尽可能坐得舒适的土沙发,因为整个白天就要在那上面坐过去。
在等待出仓洗漱的时间里,许多人就在铺位上挥臂扭腰进行晨练。在北山公园里坐久了的人都知道健康的重要。轮到今天利用洗完脸后的残水的3个人,都蹲在放马桶的死角,用昨天节省下来的开水揉湿换下来的内裤,再擦上肥皂使劲地搓。
三 导火绳是马桶
这天早晨,王茂军在门后等得呲牙咧嘴地一脸苦相。他捂着肚子到墙角揭开马桶盖,里面的粪便已满得几乎溢出来了,根本无法再往里排泄。
“妈的×!王石匠,你放毒气么?盖上盖上。”朱必成在临门的铺位上怒气冲冲地叫。
王茂军无柰地盖上马桶,双手捂着肚子又回到门后的水泥上。他不停地跺着双脚焦急地等待着。
胡管理员在10分钟之内绕天井一周,开完了应开的仓门。他出了铁栅门,将巨大的铁锁仔细地锁好又检查一遍后,登上了办公楼后墙上能监视整个院落的巡廊。他双手撑在栏杆上,严峻地扫视了一遍空荡荡的天井,然后将头转向东边的一排牢房:“1仓、2仓、3仓、4仓、5仓,出来!”
5个仓的风门洞内迅速地各伸出一支手来取下已打开的大铁锁,粗重的铁练在厚重的牢门上撞出一片哗啦声。牢门开了,人犯们拿着盥洗用具蜂拥而出,迅速地在各自仓门外低头列成横排,拎马桶和提夜壶的人站在队尾。
“报数。”胡管理员发出命令。
1仓开始报数。人数正确无误。胡管理员吐出一声:“去。”
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太阳那最初几道光芒的温暖与正在消逝的黑夜的清凉交流在一起,细小的云片在浅蓝明净的天空泛着小小的白浪。
但在胡管理员值班时,从幽暗中出来的人们却被剥夺了抬头望天的权利。胡管理员颁布过一条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只要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场,你们就必须低头认罪。虽然其他管理人员都不严格执行这条规定,但在胡管理员面前,低头认罪的人们只好抓紧时间低着头吞咽新鲜空气。
待到我们仓开始报数,人数正确无误。巡廊上又一声:“去。”
我们便蜂涌到天井边上的水池旁,从杂役犯手中领漱口水和洗脸水。漱口水有一半盅子,洗脸水是3个人共用一半盆。此时,拎马桶的王茂军和双手各提一只夜壶的独眼早已转身向厕所飞奔,在与提着空容器走出厕所的邻居擦臂而过时,4个人行进的速度不减头颈不动,都轻声说了句“你好。”不同仓的人犯相互交谈是违反监规的,人们就只能以此来获得进行过社交的满足。
似王茂军和独眼之流,未进北山公园前,没有如此文明礼貌。在文革时代的看守所里,由于大多数在押人犯的文化素质高于正常时期的犯人,耳濡目染,他们也学到了这一套。
倒马桶和夜壶的人在厕所内的时间限制在1分钟之内,如有延误,便要倒霉。受罚的轻重视管理员当天的情绪而定。最轻的是罚那两个行动迟缓的家伙滚进仓去不准盥洗,在天井里跪上半天也是常见的。因为你可能在厕所里捣了什么鬼。
一进厕所,王茂军飞快地倒光马桶又去倒夜壶。独眼则疾步奔回天井,从发水的勤杂犯手中领了半脸盆水,旋风般跑回厕所。两人迅速地将水分配给3只容器,抓起两支秃得象3寸金莲的烂扫帚在里面搅了几下,然后把水倒进粪坑。最后,独眼将脸盆中存下的一点水倒进马桶,王茂军端着马桶涮了几圈,匆忙倾倒完毕,抓起马桶盖,跟着独眼跑出厕所。这倒马桶的整个过程体现出来之精确快捷,如果被用在工厂的生产线上,那效益不知要翻几翻。
奔出厕所时,王茂军内攻已急,路上再也不能与后来的邻居进行那文明的交际了。他急慌慌地将马桶拎进仓里,也顾不得再出去洗脸刷牙,一转身便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他臀部尚未触到湿漉漉的桶沿,桶内便发出了唏哩哗啦的响声。王茂军长舒一口气坐稳身子,脸上漾起了轻松的微笑。
王茂军坐在马桶上还未完事,巡廊上已发出“16仓,进去!”的命令。
第一个跨进仓门的是朱必成。
“二师兄,我拉稀,实在忍不住了……”王茂军连忙向朱必成解释。
朱必成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扭过头去,鼻孔里有意喷出嗤嗤的响声。
我们16仓当时关了11个大男人,共用一个土陶马桶和两支夜壶。每天早上最先使用刚刚涮洗过的马桶,是“红毛犯人”朱必成在仓内的特权之一。
四 二师兄
那年代,仓内没有“仓头”“小组长”之类的头头,全是阶级敌人。理论上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每个有人群的地方都有等级。在当年的看守所里,由于“文革犯”们人多势众,且又久关不决,便在里面占了绝对优势。那怕是新进来的,都会见到些在外面是“战友”的先来者,受到热烈欢迎细心照顾,便无人敢欺侮。而那些贪污、盗窃、强奸、赌博的刑事犯们,即使在里面关得再久,在仓里自然便低人一等,不光睡不到好铺位,平时多干杂活儿,有事无事地还要受些窝囊气。但即使在“文革犯”中,每个仓又还有享受特殊待遇的“红毛犯人”。红毛,老的意思,从螃蟹老了生红毛套过来的。
朱必成当年还不到30岁,身材瘦小五官端正,举手投足颇有几分文化人的气息。但因为他姓朱,同犯们当面就叫他“二师兄”,背后便称其为“猪八戒”。他就是16仓的红毛犯人。这故事发生时,他已在北山公园里“拘留待审”了5年多。被拘留了5年多,还在“待审”,你说这资格老不老?
在那幽暗的牢房中关久了,人的个性自然就会变得古怪。在这特殊的环境里,整人的功夫也就特别高明,仓内的同犯们大多数都受过他的气吃过他的苦头。就连在外面动辄便抡拳头的王石匠竟也畏惧朱必成,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二师兄”看谁不顺眼了,谁便防不胜防很快就会有苦头吃。
虽然仓里的人们都程度不同地嫉妒或羡慕朱必成在北山公园内的特权,但红毛犯人也有他深深的怨恨。他经常外表宁静地仰靠在土沙发上好似老僧入定一般,其实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涌动着不平和愤怒。
从1969年开始,朱必成他们那一派掌了权,他们被关押的人都陆续释放了,而另外一派的便大批地补充进来。当我进北山公园时,朱必成他们一伙的仅剩下10来个人,不是杀人太多就是被杀者身份特殊,当权者实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放将出去。这留下来的10来个人便占完了看守所内诸如炊事员、打扫卫生等好差使,真正整天关在仓里的,就只有朱必成等两三个身体实在太差的人犯了。当炊事员的老部下们曾多次告诉朱必成,通过在革委会掌权的几个“战友”们的努力,好几次本来都已决定释放朱必成。但每次都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福利院的全体残疾人便拥进了市革委和支左领导小组。被那些瞎子聋子哑巴不吃不喝地一闹,支左领导小组的军人便压市革委不准放人,释放他的事儿就皇了一次又一次。
朱必成心中便愤愤不平。他经常在仓里叫,我只杀了李卫国一个,就算他的身份特殊,我又不认识他,无冤无仇,只能定性为派性杀人嘛。只要不是报复杀人,那些只杀过一两个人的都放了呀。老子在看守所里都已经坐5年多了……
他曾无限悔恨地对我说过,如果那天不去检查执行情况就没事了!龟儿坐在台上的几爷子,被些残疾人一闹就虚了,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自在,就不想老子在里面有多难熬……
被朱必成杀掉的李卫国是个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抗美援朝战争时在上甘岭获得过一等功臣的荣誉。他本可以问心无愧地在省城的荣军修养院里安渡余生,但他却不愿躺在功劳薄上安渡时光,他还要为社会作贡献。经多次向上级申请,李卫国终于回到家乡万县市,在福利院担任了文化教员。文革前,李卫国就一直是本市历届的劳动模范、学毛着标兵。一个不愿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的“最可爱的人”。文革风暴初起时,这个多次被表彰为身残志不残的老战士从广播中听到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他就象听到了冲锋号的战士一样,连夜便在福利院成立了一个“志不残战斗队”。运动初期,这支由残疾人组成的战斗队在全市赫赫有名。在大辩论的高潮中,真令对立派伤透了脑筋。不管是在街头巷尾,只要一听到不同观点的人,他们就一定要揪住辩论,那怕不吃不喝,真是不胜不休。但他们全是残疾人,在运动中绝对是只搞文斗没搞过武斗。当运动发展到只动手不动嘴时,“志不残战斗队”就没战斗力了,李卫国被对立派抓了起来。
两个多月后,李卫国所属的那一派发动了大反攻。
打输了的一派在溃退出城之际大杀俘虏。但行刑队员中有几个人还在戴红领巾时就听过李卫国的报告,知道他的光荣历史。在那几个人的影响下,行刑队对李卫国不忍也不敢下手。在处决了其他俘虏后,独独将他一个人遗留在放弃了的据点内。
当时任总部委员的朱必成心血来潮主动去检查处决行动,这一去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朱是外地人,1965年由省里一个什么学校分来本市,在一家国有大企业作技术员。他来的时间不长,与企业外的社会接触不多,确实不知道李卫国其人其事。朱必成见那些被处决者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个浑身血污的人活着,只道是行刑队大意遗漏,便命令他的警卫员开枪将那瞎子打死。每当讲到这段案情他都要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他说警卫员是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怎么在击发时就炸了膛?半自动成了烧火棍,朱必成骂骂咧咧地拔出了手枪连开3枪。
那位在联合国军的炮火下捡回了一条命的功臣,最终惨死在朱必成的枪口下。
当进攻一方的人们发现李卫国时,他双手还抱着一本被鲜血浸透了的盲文语录,身上有3个弹洞。他的双手把语录抱得紧紧的,怎么也掰不开。收尸的人最后只好将盲文语录与他一起放进了棺材。这也就是朱必成虽然只杀了一个人,但由于这人的特殊身份,他就怎么也放不出去的原因。
多年来,朱必成一直固执地认为,如若警卫员的枪膛不炸,他就不会亲手杀人,那么,今天坐在16仓的就是那小伙子而不是他了。但旁听的人都清楚,若真是那种情况,由于李卫国的身份,你朱必成非但也跑不脱,罪责还比那奉命开枪的人大。
后来朱必成被判了8年刑。刑满后他又回到了原单位,直干到退休。
大慨是心里怨气太重,朱必成嘴头爱没来由地伤人。他因给人乱取绰号,本吃过大亏,但他没汲取教训。依然对任何人都不尊重,老校长被他称为“老头子”,我被他呼为“大个子”,这类中性的称呼还算是客气了。而对有些人,朱必成就没这么客气了,他就当面流氓、扒手地叫,全不管被叫者是不是真正的流氓和扒手,更不理会别人心里怎么想。他呼杀人犯余中富为“流氓”,除了因为余中富家里很穷,在全仓数他的衣物最少而且破烂之外,更主要的是,朱必成知道余中富嫌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中富”太俗,而喜欢别人称他“高洁”,便故意叫他流氓,来剌激他取乐。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朱必成太不了解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小知识分子。后来,他为这一方面的无知付出过昂贵的学费。
更何况余中富脸上还生着一双小小的常年通红的眼睛,麻衣相术中称之为蛇眼。古人曾告诫过,不要跟生蛇眼者结怨。朱必成缺乏传统文化修养,才敢无端地去激怒余中富,丝毫不把他的怨恨放在心上。
余中富常用闪着血光的双眼狠狠地盯着红毛犯人的后背。余中富会等待,对于知道怎样等待的人,一切都会来得恰是时候。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