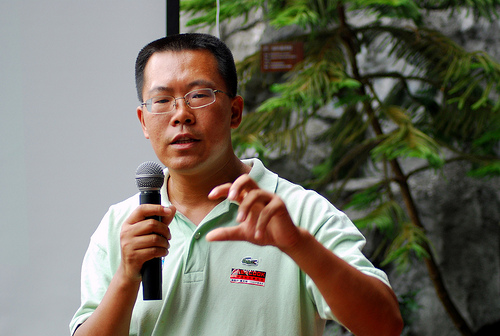2003年是中国的民权年,其中互联网起了关键作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
互联网为自由提供了机会,这个案件也为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点了题: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
2003年被称为民权行动年,或者公民维权年。民权行动并非从2003年始,何以2003年成为中国民权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观察家和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互联网络在维权个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SARS的讨论,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为李思怡的绝食,为黄静的呼吁,为刘荻的呐喊,为杜导斌的签名,都表现了网络在民权运动中的多重作用:反映民意的中介,对行动进行策划、梳理和反思的渠道,沟通信息的方式,而且直接作为行使权利的手段。比如2003年底的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BBS直接成为独立候选人发表演说、争取选票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几乎每个有影响的维权个案的背后都有互联网的影子。网络言论自由既是争取的目标之一,又是维护权利的重要平台;互联网的言说自身也是突破言论限制、打击新闻柯断的一种维权行动。每一个被关闭的网站、每一篇被删除的“敏感”帖子、每一个被捕的网络作者,都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史书写著“丰富的痛苦”。通过网络斗争的细节,可以窥见中国民权行动的某种隐秘的光芒。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每秒种都在进行:关键词的样式变幻,浏览敏感网站的软件,隐蔽身份的技术技巧,含沙射影的春秋笔法,版主与网友的心照不宣。自由与反自由的斗争是多层次的:技术上的、法律上的、知识上的、思想上的乃至灵魂上的。
孙志刚事件发生在SARS肆虐之时,我和我的两个朋友许志永、俞江在互联网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在BBS上进行讨论,通过电子邮件对违宪审查建议书进行修改,通过传真把建议书递交上去,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并发表那些在传统媒体上没法发表的东西,也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的挑战中尽管有不少遗憾,但仍被很多人称为民权行动和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互联网持续的关注形成了强大的道义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在“隔离时期”的这次维权行动,绝对是“不可完成的使命”。
始料不及的是,“三博士”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维权人士;更没预料到的是,本来极其宁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了:我们每天都收到很多群众的电话和邮件,反映他们遭遇的种种冤情。我马上意识到,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如果你做了一点为百姓鸣不平的事情,如果你的职业和法律、政治、新闻有关,只要你的名字在报纸电视上出现,就很快会成为上访材料接收中心。一次我和李健去看望名记者王克勤,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来了,头一句话就是:“满天下的冤情啊!”接著是长时间的叹息和沉默。
他说出了我的心情。我每天看到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的故事,体验著他们的困惑和绝望,体验著他们对司法不公的愤怒、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以及对正义的殷殷期待。在深夜里面对著这些材料,我常在心里流泪叹息,同时也真正犯了愁。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是能够扳倒收容遣送制度“三博士”,你是法学教师兼律师,这点冤情还解决不了吗?可我能做甚么呢?我无法跟他们说我是多么渺小和无力。我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权力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他们的案件几乎就没有希望。这些上访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人权遭践踏,法官被收买;判决已生效,上访没人睬;屡败而屡战,屡战又屡败。起作用的不是我的法律知识,而是权力、关系、政治或实力,“那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每个学过法律的人,都可以体会到我跟他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多么痛苦:“你可以找找媒体,或许能起点作用。”当司法无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媒体似乎成为被司法遗弃者的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司法不独立的社会里,新闻也不是独立的。谁敢报导他们的冤情呢?
好在还有互联网。我跟他们说,我帮你在互联网上呼吁呼吁吧,其实不过是把他们长长的上访材料砍成千把字在BBS上贴贴而已。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了。实际上也起不了甚么作用:帖子太多,几分钟就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而且冤情也太多,这个司法体制所产生冤情的速度远远超过它能解决问题的速度,或许就在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有某个人绝望地踏上了上访的征程。
尽管这样,几位老先生还多次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奢望——要是有这么一个网站,专门关注这些事件,反映他们的呼声,让他们有一个倾诉的地方,也对那些肆无忌惮的政法机关形成舆论和道义的压力,该有多好。要是再有这么一个人,能够专门关注这些事件,收集这些信息,该有多好!
可是真有这么一个网站,叫“公民维权网”(www.gmwq.com),也真有这么一个人,叫李健。2003年11月1日,他成立了这么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关注的案件有孙志刚案、黄静案、宝马撞人案、刘荻案、郑恩宠案等等,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案件。李健也在全国各地奔走,专门从事维权。他请我当顾问,我上网站看了一眼后立刻答应了,但也没顾上去多问。
当我被顾上问的时候,他的问题是:“网站被关了,怎么办?”——一个从事公民维权、声援弱势群体的网站开办了23天就被关了,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公民的权利状况。每天都有网站被关,不过“维权”网不同。他要维权。他到信息产业部、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去讨说法。这似乎是第一次,因为从录音中可以看出,部里的人和局里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答复时也是支支吾吾、前后矛盾。李健在交涉中还问出了涉及个人网站生死存亡的秘密:非经营性的个人网站要经过“备案”,但是“ICP备案登记表”又不允许个人填写——表上的栏目给“单位”预备的,也压根没有个人来填过!
可是李健非要填;因为法规上说,非经营性网站要在你这儿备案。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他在“单位名称”和“上级单位”一栏里填的是“李健”,在“工商注册登记号”下面,他填的是自己的身份证号!这样,李健又成了以公民名义来填这张表的第一人。不过像集会游行示威一样,法律在名义上保护你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公安部门永远不会批准你的游行申请;这个备案被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等于说中国所有的个人网站都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
李健还要去起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因为后者责令关闭网站的行政行为没有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第292号令)第19条所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的程序。(该条规定,对未履行备案手续的非经营性网站,由省级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网站”,而不能直接关闭网站。)李健又成了状告通信管理部门的第一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意义上,这都可以称为中国个人网站行政诉讼第一案。由“公民维权”网来打网络自身维权的第一案,也算是实至名归。
这个案件涉及到个人网站的生存,涉及到网络言论的自由程度,也关涉在以网络为重要平台的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人们不会否认,网络言论的自由度直接影响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是互联网在中国民主转型时期的特殊角色,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这个案件充满期待。
这个案件展示了个人网站的另一种斗争策略:不是一关就跑的游击战,而是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你为甚么关我?法律依据何在?有没有事先告知?执法程序有没有瑕疵?我来备案你为甚么不给答复?不给备案的理由何在?那么多黄色网站你不管,为甚么要关我“公民维权”?个人为甚么不能办“公民维权”,个人为甚么不能讨论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在体制的限度内,跟你抠法条,跟你讲道理,跟你拼证据,也跟你比道义力量。如果每个网站被关之后都跟他们去讨个说法,跟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那么个人网站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等于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胡适说得好:“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公民维权网状告通信管理局也是民权运动中运用“假戏真唱”策略的一个生动例子。《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说非经营性网站实行备案制,未必是真希望大家都来备案;可我偏把你的话当真了。你不按法规的程序来关网站,我就告你。要把法律用尽、把权利用足,既然条文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楚,你不按它办就得说个理由。《立法法》上说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未必料到真有人这么做,可我们就用这个不起眼的东西来挑战收容遣送办法;陆续有人用这个东西来挑战劳教制度、挑战各地的拆迁条例。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未必是真想保障言论自由;但是我可以用它来挑战《集会游行示威法》,说它违宪了。你写这一条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但是我偏要把这死戏给唱活了,把这假戏给唱真了。关于宪法有个著名的笑话:一个农民拿著《宪法》小本本去找乡长评理,乡长把宪法往桌子上一砸:“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那是给联合国看的!”——现在假如我是那个农民,就会一脸无辜而真诚的样子:“是吗?可我以为是给我看的,我得到法院去告你!”
这个案件也为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点了题: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我想,只有这样,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青春无憾,生命无悔——因为我们用血泪和汗水见证了自由中国的艰难历程,我们用智能和勇气参与了自由中国的美好事业。
初稿于2004年2月8日深夜。
注:本文的某些观点得益于与范亚峰、浦志强、张星水、许志永等人的讨论
(《人与人权》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