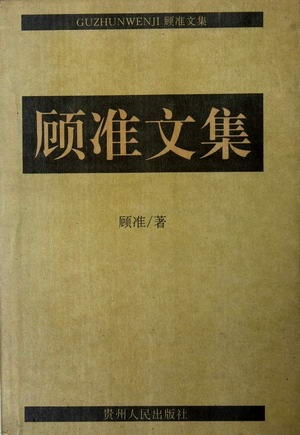一战、二战之间,全世界知识份子普遍左倾,只有少数真智者能对马克思主义保持清醒的批判头脑,雷蒙·阿隆是其中之一。他曾说,一个人,如果年少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没良心;当他成长后,如果还信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没头脑。这两句评论表明阿隆对马克思和他那一套华而不实的理论知之甚深。
阿隆说得够客气。直截了当的说法是:马克思好心办成大坏事,盖因其智能平庸。共产党如今遭人厌恶,实在并非因其邪恶——恰相反,那倒是一个最富于道德热情的人群;至于他们掌权后的恶政,则又当别论(其中一大部份正是愚昧招致的报应)——共产党要不得,是因其愚昧;由过分的道德热情与缺少教育二者相互强化所导致的愚昧。
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极端主义的情感立场和思维方式。这种极端主义从来不会是建设性的;更糟糕的是,马克思把他的极端主义精致化、理论化了,正好比穷人的耶稣基督加上知识份子的柏拉图,便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教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被过度的道德热情和富于欺骗性的理论所强化了的超级极端主义,真实的道德优越感配上虚假的理论自负,使得共产党人少有能够大彻大悟的;而且,越是真诚越难彻悟。
但凡事皆有例外。眼前就有一例:顾准,一九三四年即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曾官至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长;一九五二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罪名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又两度被划为“右派”;一九五六年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至一九七四年因肺癌逝世。
顾准是一九九五年中国思想界、读书界的一热,此热持续不衰,以至于不久前北京专售“畅销书”的小书摊上也纷纷摆出了《顾准文集》。尽管中宣部早就下令此书不得再版,《顾准文集》却已悄悄出至五版。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世间聪明的人多,有大智大慧者少;好人多,有大德大勇者少。而大智大慧与大德大勇兼备者,则少之又少;顾准却正是这极少数最优秀者之一。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思想专制的黑暗时代,其黑暗的程度,也许只能用“做梦都不敢做错了”来描述;其黑暗的程度,只有亲自从那个时代挣扎过来的人才能体会;而且,愈是优异者其痛苦会愈深。那个时代之所以尤其可怖,是因为它与前此一切专制时代不同,在它的“平等”和“为大多数”的旗号下,不仅集合了一批真诚的、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这旗帜确实受到大多数人的热情拥戴。它是多数暴政——被多数拥护和践行的暴政;它的专制刀斧,主要是用于砍杀一切敢于独特异见、不肯放弃真理的少数优异者——如顾准辈——的。因此,毫不奇怪,顾准一生历经坎坷磨难,他不曾死于牢狱流刑,倒是一大侥幸。
对于那个黑暗时代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封锁,信息闭塞而造成的孤陋寡闻和幼稚肤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顾准的“见解深邃、知识渊博”(王元化语)大为惊诧。即便是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顾准的见解之卓越超前,也仍然远远高出于当今大陆知识界的平均水准之上。这几乎是个谜,一个古希腊式的谜——凡倾心于古希腊文明的人,无不为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之难以解释的现代性而惊叹。读罢顾准,再读去年也曾热销一时的某位只能称之为“反动理想主义者”的作品,对于后者的毛泽东崇拜、宣扬暴力与仇恨,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泛道德主义的偏激热狂、毫无节制的浪漫与情绪化,多数暴政式的民粹主义……这形形色色汇聚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漂亮旗号之下,与人类进步的主流文明背道而驰、而且事实上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近二十年的惨重灾难的思想垃圾,面对这样一种极其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令人竦然心惊!从中隐隐然现出一个凶兆: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大概不会平坦易行。不铲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毛泽东思想即民粹化的列宁主义思想遗毒,就不可能在大多数人中牢固确立民主的信念与习惯,民主制度就会既难顺产,更难发育壮大;民主制即便侥幸建立,风浪稍大,就可能由多数人经民主程序将民主颠覆,演变为多数暴政,然后是无政府状态,然后是军事独裁或另一种独裁。
顾准曾热诚信仰过共产主义,并且为之舍身奋斗过。当他发现他曾拳拳服膺过的东西不但不是真理,而且距真理甚远时,他也曾陷入极大的内心痛苦。但他终于还是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思想反叛之途。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这段话写于一九七三年。我们今天从《顾准文集》读到这段话,都不禁为出版社的编辑们捏把汗,遑论当日?这话泄露出去,当年是一定杀头的!也许,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与无私,才使顾准达到彻悟的大智慧之境。反观今天中国许多“党内民主派”,之所以还在旧的思维框架中打转转,迈不出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一步,恐怕早已不是由于“过分的道德热情与缺少教育二者相互强化所导致的愚昧。”而仅仅是由于自私和怯懦。仅有的一些道德热情已经抵不住既得利益的侵蚀;开放十数年了,受教育的机会伸手即是,如果还缺少教育,那也是因为“自觉的约束”,即因为怕担风险而自动地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眼界之内,不读新书,拒绝接受新的思想,而理由仅只是软弱无力的一句反问:难道马克思就毫无可取之处吗?
顾准之超卓,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当今大陆两位学界泰斗吴敬琏、李慎之对此有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读书》、《改革》两刊一九九五年五月号),感人至深,颇值一读。
当然,顾准并非完人,他毕竟也要受限于时代与环境。他也许是中国大陆知识份子中最早系统批判了卢梭→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条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众民主”路线的一人,但限于历史条件,顾准对另一条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民主路线知之不多,因此,他的批判不会是很彻底的。我们今天纪念顾准,不仅仅是要推崇他的人格与智慧,更重要的是以之激励自己,超越顾准,更勇敢、更扎实地前行。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