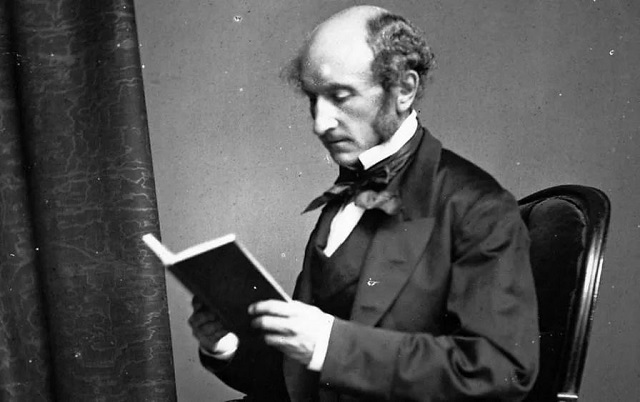密尔 火龙随笔 2022-04-16 00:18
这是约翰·密尔所著的《论自由》的缩译版本,之前的译本接近10万字,我缩译到了约1.8万字,差不多40分钟能读完。
这本书探讨了自由的边界和意义,是政治哲学的经典读物,是人类思想史里的明珠。尤其第二章,论证了我们对于“异议“应该采取的宽容态度。
第一章:引论
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19-05-31 22:50
本书讨论的是个体自由问题,或者说,群体对个体进行干预时,应该以何为界。
[1]
过去的历史里,自由与权威的斗争络绎不绝,通常发生在臣民和统治者之间,那时的自由是对统治者暴虐的防范。统治者通常被当作人民的对立面,他们通过继承或者征服来获得权威,而不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意愿。民众不敢对统治者的权威提出异议,甚至压根没有这个想法,顶多只是通过一些举措来防止暴政。
统治者的权力是必要的,同时也是高度危险的。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用来抵御外敌,也可能用来压制民众。因此,需要对权力设置一些限制。对权力的限制也就意味着给人民的自由。
有两种限制权力的做法:一,明确界定个体的一些权利不得被统治者侵犯,否则,民众可以发起正义之战;二,近代的一种做法是建立宪政制衡,要求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举措,必须得到民众或民众代表的同意。
第一种限权的做法,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但第二种宪政制衡的做法还远未实现,这是各地自由主义者的首要理想。只要人类还指望以一个统治者来替代另一个统治者,还祈盼一位承诺仁政的主子,宪政制衡就依然是我们的至高理想。
[2]
后来有一种新想法:如果统治者由人民选出,并可按民意更换,统治者就会与人民心意一致,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民众就可以把权力托付给统治者集中行使,而不必担心被滥用的权力侵害。
基于这个想法,大家开始寄希望于选举。各国的平民党派都把选举并限制任期长度作为首要目标。
大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关注限权,有人认为限权可能只适用于那些反人民的统治者。如今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主张限权的所剩无几。
终于,法兰西共和国呱呱坠地,民选政府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一个个美梦却开始破灭。
人们开始明白,行使权力的“人民”和权力实施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心意一致的;“自治”不是每个人自己治理自己,而是每个人受其他所有人治理;“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行使权力的“人民”渴望着压迫某一部分人民,造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防范人民滥用权力和防范统治者滥用权力一样重要。即便对一个代表民众(确切地说应该是代表民众中最强大的党派)的政府,限制其权力也是极其重要的。
[3]
“多数人的暴政”是自由的大敌。在政治学说里,“多数人的暴政”已经被当作需要戒备的祸患之一。
表面上看起来,“多数人的暴政”似乎需要借助公权力来施行。实际上,当社会集体凌驾于个体之上时,暴政的施行并不一定要借助公权力,这时社会本身就是暴君。
社会本身就能够执行自己的命令,如果这个命令是错误的,就会造成比政治压迫更可怕的社会压迫。社会压迫虽然不常带有严厉的惩罚,但却更深入地渗透在生活里,束缚着人们的心灵。
因此,不但要防范公权力的暴政,还要防范社会主流意见和大众情感的暴政。要防范社会将自己的观念作为行为准则强加给异议者,防范社会束缚与主流不一致的个性,防范社会用一个模子来塑造所有人。
集体意见对于个体的干预应有边界,找到这个边界并使它不被侵蚀,对于人类幸福,对于避免专制,都必不可少。问题是,这个边界究竟应该设定在哪里?在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平衡?
[4]
如果人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每个人的生活都将缺乏保障。因此,的确需要制定一些行为准则。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法律,在法律不适宜的事情上,则要仰仗社会舆论。
行为准则影响着自由,然而很多行为准则并无坚实理由。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行为准则各异。一个时代或国家的准则,会令另一个时代或国家的人难以理解。怪异的是,人们又总觉得自己身边的准则是亘古未变、理所当然的。习俗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群体对个体进行干预时,常以习俗的旗号来打消人们的质疑。以“亘古未变的习俗”之名,干预就显得理所当然,不再需要理由了。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行事,综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准则。如果你的行为准则没有缘由,那就只是个人偏好。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个人的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会受别人的影响。如果你的行为准则缘于“别人也这样”,那就只是众人偏好。
个人的行为准则可能缘于他的偏见或迷信,也可能缘于他的社会情感(比如爱慕或妒忌,尊重或傲慢)。人们的社会情感,受上流阶层的影响很大。王侯会影响臣民、贵族会影响平民。当这个上流阶层走向没落,丧失支配地位时,社会情感也将反转。
不但现实世界的上流阶层影响着人们,精神世界里的神灵也影响着人们。人们对神灵发自内心的奉迎,引发了对异教徒实实在在的憎恶,必须烧死他们方消心头之恨。
另外,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切,也影响着社会准则(尤其是道德准则)的走向。遗憾的是,这种关切,受感性的左右远大于理性。同情和厌恶左右着道德准则,然而它们对社会利益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5]
人类在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上不能容忍异议,这是天性使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只要力所能及,就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人。就这样,群体的偏好(或者说群体里强势者的偏好)变成了社会的规则,违规就要遭受法律和舆论的惩罚。
以宗教为例。异教总是受到主流教派的压迫,这时,他们竭尽全力请求社会允许他们的分歧。然而,当他们冲破束缚,变成新的主流教派时,也同样开始压迫其他分歧者。
伟大作家们笔下的宗教自由在现实世界里很少实现,除非那个地方的人们对宗教漠不关心。再宽容的信徒,对异议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有的信徒无法容忍无神论,而有的信徒甚至无法容忍对教义的不同解读。无论在哪里,只要信徒们的宗教情感是真实而强烈的,异议者面临的从众压力就不会小。
奇怪的是:那些思想上先人一步的精英,虽然会对一些规则的细节提出异议,却很少质疑为什么这个规则要成为每个人的律条。当自己的某个观点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压迫时,他们会竭尽全力为这个具体观点而战,而不是联合其他各类“异端”一起为广泛的自由而战。
[6]
基于英国政治的独特发展史,我们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不同,虽然舆论的枷锁可能更重,但法律的束缚却更轻。人们总是很敌视公权力对个体行为的干预,与其说是出于对个体独立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公权力的戒备。所以,一旦要把法律对个人的控制延展到那些还不受法律控制的事情上,大多数人在理性思考之前,就会在情感上直接反对。
实际上,对于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判断准则,人们只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支持还是反对。有些人,无论看到一件需要提倡的好事,还是一件需要禁止的坏事,都希望由政府来承揽;还有些人,宁可忍受各种痛苦,也不愿让政府再增加一件事。由于缺乏应有的判断准则,人们对于政府的干预,有时错误地呼唤,有时失当地谴责。
本书的目的是提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无论通过法律还是舆论,干预个人事务都应遵守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干预个体自由的正当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其伤害他人”。
其他的干预理由都不正当,例如“为了当事人的幸福”强迫他(或禁止他)做某事。哪怕他不这么做就会遭受不幸,也不能强迫,只能劝告。因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要对社会负责,而只涉及自己的那部分,他应该拥有绝对的独立权。毕竟,对于他的身体和心灵,他自己就是最高主权者。
当然,这条自由原则只适用于各项能力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那些还需要由别人照顾的人,我们不但要保护他们免受外来的伤害,也要保护他们免受自己行为的伤害。
这条自由原则也不适用于那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还没有能力通过平等的讨论来进步,自由也无从应用。对这种社会的治理,只要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状况,适当地专制也是合理的。一旦这个社会有能力通过讨论来进步,就不应该再“为了他们好而干预他们”了。
[7]
我所力主的是,只有那些涉及他人利益的行为,才需要遵从外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伤害他人的证据确凿,他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在不适合法律惩罚的领域,则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
个体的行动可能伤害他人,个体的不作为也可能伤害他人(比如拒绝出庭作证、拒绝防御外敌、不保护无力自卫的人等等)。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应该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负责,但后一种情况下应该更加谨慎,很多时候,个体的不作为可能是正当的。
在个体会影响他人的事情上,个体应该对他人和社会负责。那么,在哪些领域内个体享有完全的自由呢?
有以下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内,个体的生活和行为仅对自己产生直接的影响。即便看起来似乎影响到了他人,他人也是自由自愿且不受欺骗的。
•首先,意识领域。这是指对社会、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见与情感。在该领域,个体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这也包括发表和出版,因为发表和出版与意识本身同等重要,而且实际上无法分开。
•其次,品味和追求。只要不伤及他人,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自由地规划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承担后果。即使别人觉得这很怪诞、愚蠢或者错误。
•最后,个体之间的联合。由个体自由的原则可以推知,只要不伤害到他人,个体之间还可以自由地联合。但参加联合的人必须是不受强迫和欺骗的成年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这三个领域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个社会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8]
真正的自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心中的美好,同时不能阻碍别人的追求。无论身体、思想还是精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最佳监护人。让人们各自追求自己心中的美好,比强迫人们追求别人心中的美好,对人类的益处更大。
尽管这个道理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是当前观念与实际的走向却恰恰相反。从古到今,社会一直竭力迫使人们遵从它对美好个人和美好社会的定义。
古代的共和国认为政府有权管理个人的一切行为,古代的哲学家也认同这一点,理由是每个公民的身体和智力都和国家利益深切相关。
在现代,政教的分离,虽然防止了法律大面积干预个人精神生活,但是也加强了道德对个人精神生活的绑架。
宗教是左右道德情操的最强大的力量,可是,它要么被企图掌管人们一切行为的教阶集团所控制,要么被清教主义的精神所控制。一些积极引领宗教革新的现代改革家,对精神控制的强调一点也不比教会弱。尤其是孔德,在他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他主张通过道德而非法律,建立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专制社会体系。这个想法甚至比古代哲学家中最严酷的纪律主义者还严酷。
当今世界日益倾向于,借助舆论和法律,让社会权力越来越多地侵犯个人。同时,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在加强社会的权力,削弱个人的力量。看起来,社会权力对个人的侵犯不但不会自然消失,而且会日益增长。除非在人们的道德信念里树立起一道有力屏障,来阻止这一危害,否则我们只能看着它继续坐大。
下一章将专门论述意识领域的自由,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言论、写作与出版的自由。尽管这些自由在那些自由政体的国家里已经成为政治道德的一部分,但其背后的道理,人们并未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