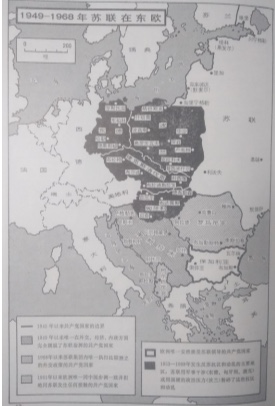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1)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4)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第六章《处于危机的一体化》中先以“苏联‘无国籍的人’”为题叙述了鞑靼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在苏联民族一体化中的悲惨遭遇:
苏联每个公民都随身携带说明自己所属民族的身份证。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苏联制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某些民族虽然是合法存在的,但却与其他民族的处境不同。从他们的身份证上可以看出,人们拒绝他们要求拥有的第一祖国。这些长期保持沉默的“无国籍的人”几年来成了苏联最爱闹事的公民,因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忍无可忍了。这些人有鞑靼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固然不同,但想成为拥有自己祖国的、单独的“民族”的一致愿望把他们联接在一起了。他们的怨恨表现不一: 鞑靼人想返回自己的家园——克里米亚。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不再认为苏联是自己的故乡,希望离开苏联。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如此强烈地表现出异议,以致于不顾其人身安全和自由而坚定地提出这种异议呢?
先看看鞑靼人。“鞑靼”一词对于喀山的鞑靼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在莫斯科以东拥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生活在苏联之外的人不大懂得为什么塔吉克的鞑靼人抱怨没有祖国。苏联的统计材料在“鞑靼”的专栏中把这两部分鞑靼人混为一谈。把这些鞑靼人加在一起,在1970年共有近600万人之多,成了苏联的第五大民族。
但实际上,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一个在语言上和文化上与喀山鞑靼人迥然不同的民族。他们的人数大约在30一50万左右。苏联政权1921年承认他们在克里米已居住了上百年,承认他们的民族特性和俄罗斯过去对他们的统治;它使他们拥有一个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把它并入了俄罗斯联邦。鞑靼人在俄罗斯联邦曾经享有了几年的得到承认的民族权利: 语言、学校和自己的文化。之后,战争一下子使他们变成了一个有着异乎寻常的、特别严酷的命运的民族。1944年4月,德国占领军一撤走,他们被列入斯大林武断地编制的“与敌人合作的民族”名单里,这个民族的全体居民被迫对此承担集体责任。1944年5月18日,所有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几个小时内都被放逐到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有20多万人遭到这一厄运,其中大多数被送往乌兹别克定居。1946年6月25日,苏联颁布一项法令宣布,由于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居民与德国人合作,该共和国(还有车臣和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宣布取缔,其居民“被安置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他们在那里得到土地和政府的帮助”。
鞑靼人在他们的流放地经常受到监视,同时,苏联政权在克里米亚竭力消灭鞑靼居民遗留的一切痕迹。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移民源源而至,并取消了所有鞑靼人的地名,有计划地拆除了他们的住宅。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今后不可能返回家园。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1944年的流放列为斯大林一系列罪行之一;但在列举被放逐的民族时,他没有提鞑靼人。所有被放逐的民族都恢复了名誉,于1957年1月重返家园,并恢复了他们的民族地位。而鞑靼人只得到了秘密范围内的有限宽大措施。
1956年4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所有鞑靼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享有正常的地位。但是此法令一方面没有公布于众,另一方面还明确规定,鞑靼人不能收回以前被没收的财产,也不能返回克里米亚。此外,他们原先的领土已被赫鲁晓夫在1954年划归乌克兰。这样,鞑靼人不得不留在他们当时的所在地(除了克里米亚,可以在苏联任何地方定居的权利都不符合他们的愿望),不得不作为拥有很小文化权利的少数民族而生活下去。
当时,在苏联呈现着非斯大林化和为被迫害的人恢复名誉的欢欣景象,而鞑靼人却感到被大家所遗望和被排斥在开始发生的变化之外。对鞑靼人采取的限制性和无理损害其返回家园权利的规定表明,该民族仍然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这不仅关系到在此情况下鞑靼人在道义方面的地位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它能否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下去的问题。鞑靼人由于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和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势必逐渐被相邻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所同化。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民族那么勇猛地进行着反对苏联政权的艰巨战斗。它所希望的是政治上恢复名誉,有权返回克里米亚,把克里米里归还给鞑靼人,重新成为民族领土,并且鞑靼人能够拥有与其地位相应的一切权利。
鞑靼人从1957年起开始了为生存而展开的合法斗争,因为那时,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政权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动归还对鞑靼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当时,在整个苏联都相信请愿和上告能解决问题。苏共在二十大之后提出的口号不是要恢复法治吗?由于要考虑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政权所提出的合法的原则,他们只能求助于苏联政权。从1957年7月到1961年10月,他们向党和国家机构递交了六份请愿书,每份请愿书签名的人数为六千到2.5万人不等。这些请愿书都只有一个要求,即要求得到与其他被流放的民族平等对待,恢复该民族的政治和民族权利。苏联政府对这些集体联名的要求不置不一词,却指责最活跃分子煽动“种族仇恨”,并对他们进行镇压。所有这一切都很快激起鞑靼人寻求新的活动手段,但仍是合法的手段。
鞑靼人深信,要使苏联政府听取他们的呼声,就必须接近它。于是在1964年,他们决定向首都派驻一个常设代表团。鞑靼人在居住的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这些代表用集体的经费千里迢迢去莫斯科。他们的使命是设法让当局听取他们以受委托的名义提出的申诉,向当局递交请愿书,并登报广为宣传。苏联当局的申诉程序是有欺骗作用的,所有的申诉渠道都由苏联当局所控制。但是这种程序符合鞑靼人的处境: 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因而便丧失了民族的代表;谁都没有权利作为民族来代表他们。这种程序也符合当时的精神状态。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建立“全民国家”时,号召他的同胞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于是,在苏联展开如何使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讨论时,鞑靼人认为他们是顺应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他们曾因为这种表面的解冻而感到欢欣鼓舞。身负委托并带着请愿书的鞑靼代表们,在1965年8月受到了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的接见,1966年3月,又受到主席团秘书格奥尔加泽的接见。这一切似乎是奇迹,但很快就令人失望了。1966年初,在苏共二十三大前夕,有一个为数125人的鞑靼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向握有实权的所有负责人发去了具名的1.5万封信件和电报;最后,还准备了一份递交给代表大会秘书处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2万人。实际上所有的鞑靼成年人都签名了。在六十年代的苏联,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具名的请愿书,而整个鞑靼族能这样一致采取行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但是却不见任何动静!鞑靼人大失所望,但毫不气馁,他们在1966年3月到6月的三个月里又征集了11.5万人在新的请愿书上签名,还发出了近二万份信件和电报,派出新的代表扩大了驻莫斯科的代表团。直到这时,苏联政权还企图无视这个运动,避免直接接触。或许正是由于看到鞑靼人这么迅速地重新动员起来,这才促使苏联政权作出了反应。莫斯科的各旅馆受命不许鞑靼人居住。6月28日,到苏共中央递交请愿书的一个鞑靼人小组遭到逮捕,并立即被驱逐出莫斯科城。
在乌兹别克,迅速得悉这个消息的鞑靼人被激怒了,他们接连不断地示威游行,到每家每户和各公共单位寻求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但苏联政权选择了强硬的手段。它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这件事的前景使它感到不安。10月18日是克里米亚共和国成立45周年纪念日,鞑靼人打算通过纪念活动来扩大游行示威,以便引起大家对他们的注意。1966年,在苏联还没有人懂得,要迫使苏联政权让步,就必须让国外听到他们的声音。对一个民族而言,应当做的是要让莫斯科听到他们的呼声,让自己的同胞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了解他们。苏联政权所要制止的正是这种国内的运动。它迫不及待地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刑法中列入了两项条款,旨在阻止传播关于鞑靼人命运的消息。根据这两个条款,原先最符合法律的行动变成了非法行为,从而为实行镇压开辟了道路。
由于斗争的合法性越来越有限,他们便放弃了合法斗争而选择了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那怕这些方式不合法。鞑靼人虽然被被剥夺了在莫斯科住旅馆的权利,但他们到莫斯科去的人却日益增多,1967年夏天达400人。他们公开宣布将在红场举行集会,以便让大家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时在莫斯科正值旅游旺季,于是鞑靼人第一次产生了这种主张: 举行外国人能看得见的示威游行,让外界了解他们的运动。这种主张是明智的,急于保持控制局势的苏联政权不得不决定作出妥协。1967年7月21日,双方进行了会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答应恢复鞑靼民族的政治名誉,赦免那些因进行申诉活动而受到惩罚的人,但对他们返回克里米亚却持保留态度。至于恢复共和国问题,根本只字未提。安德罗波夫保证还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但过了一个半月未见任何行动。鞑靼人怀疑,这次会议是否像前两次那样,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对他们进行报复。因而在塔吉克,到8月底时骚乱愈益迫近,警察不停地驱散示威群众,逮捕那些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的人。
1967年9月5日,鞑靼人获悉他们取得了胜利,因为当局颁布的一项法令说: “在克里米亚解放后,克里米亚的整个鞑靼族居民不公正地被指控与敌人合作,而实际上只有一些人通敌。这种对于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民族全体公民的不加区别的指控应予以取消。”
这项法令使鞑靼人重新拥有他们的一切公民权: 居住自由和文化权利。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们达到了目的,即给他们洗掉了叛徒的罪名,他们重新成了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民族。然而他们感到的满意仅此而已,他们并不完全与苏联其他民族一样平等。虽然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但是对此是严加保密的。只有他们所居住的几个共和国的报纸刊登了这一法令,其他地方长期以来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可以去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并被承认拥有某些文化权利。但实际上他们早在1956年以来就有迁居自由和有限的文化权利。另一方面,这项法令中只字未提可能恢复他们的共和国问题。法令虽然确认他们是“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但是却取消了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确定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准之一。这项法令把他们过去居住在克里米亚和现在移居到中亚相提并论,说他们既是中亚人,也是克里米亚人。苏联政权认为,用恢复鞑靼人的名誉换取的这种保留态度显然会使鞑靼问题销声匿迹。苏联政府和党准许鞑靼人在各公共场所举行正式集会,以便让他们表示出满意的心情。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证明了苏联当局的尴尬处境,也证明了它意识到鞑靼问题仍悬而未解。
此后过了十年。在这十年中,鞑靼人不断努力在他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争取胜利,这就是返回克里米亚。为了获得成功,他们通过三条途径开展活动。一条是合法途径,即向苏联当局递交大量请愿书,特别是在苏联政权庆祝其民族政策取得成就的各种纪念活动时,更要这么做。第二条是准合法途径,即把鞑靼人的权利要求与苏联民主运动的权利要求结合起来。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不怎么关心民族运动,但以1970年以后注意听取鞑靼人的呼声,把他们的要求列入了保护人权的总纲里。第三条途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这条途径从此成了鞑靼运动的康庄大道。被禁止在故乡居住的鞑靼人无视禁令,纷纷向故乡迁移。然而,只有少数人成功地冲破了准许定居的重重繁琐限制。许多鞑靼人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抱着能被克里米亚接收的一线希望,秘密地长途跋涉向故乡迁居,但却被遣送回中亚。在争取恢复名誉的战斗取得胜利之后,鞑靼人在重建正常的民族生活的战斗中吃了败仗。他们在中亚仍是外来人,这并不是因为当地不接收他们(相反,都很亲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放弃返回失去的故乡的梦想。鞑靼人像生活在异地的其他民族一样,如果不能重返故乡,就宁愿继续成为无国籍的人,成为叛逆者。对于这种挑战,苏联政府熟视无睹,企图否认把鞑靼人和克里米亚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情况。关于这个民族,官方的论点是: 居住在克里米亚的有包括鞑靼人在内的各种民族的居民;而代表这块领土多民族性的,是现存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命名与其他民族共和国命名的一般规定相反,用的是地理名称,而不是某个民族的名称。这就明显地否认了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居住的历史性权利,从而也否认了鞑靼民族的存在。为什么这样苛刻地对待如此弱小的民族呢?事实上,使苏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30万鞑靼人,而是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鞑靼的民族主义,它在革命前后对俄国的穆斯林的影响是巨大的。鞑靼人提出的许多主张会震撼俄国的穆斯林。斯大林1944年成功地削减了鞑靼人占据的地盘,把他们赶出了克里米亚。他的继承者不想重新扩大鞑靼人的天地。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继承者还要进行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通过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的斗争,也将会收复所失去的领土。如果承认失去了故乡的30万鞑靼人的正当权利,就等于为这种民族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这种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土耳其——穆斯林民族主义。
1967年9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第36期刊登一项法令,全文如下: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法令:
在克里米亚于1944年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后,曾经把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人中的一部分同德国侵略者积极合作的事实,毫无根据地加在全体克里米亚鞑靼族居民的身上。这种对克里米亚鞑靼族全体居民不加区别的判决应予撤销,尤其是已经有新的一代人进入社会的劳动和政治生活。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一、废除各国家机关关于对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不加区别的判决的相应决定。
二、指出,过去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现在已定居在乌兹别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上,他们享有苏联公民的一切权利,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的代表,在苏维埃、经济和党的机关的重要岗位上工作,还为他们进行了无线电广播,发行本民族语言的报纸,实现着其他的文化措施。
为了进一步发展鞑靼居民区,委托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一如既往地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给予鞑靼族公民以支援和协助,并要考虑其民族利益和特点。
1971年三、四月间,六万名克里米亚鞑靼族人给苏共二十四大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返回克里米亚,恢复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释放因此而被判刑的代表。
1972年8月16日,克里米亚鞑靼人把一份有二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交给勃列日涅夫,要求返回家园;同时将另一份有一万八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成员,要求“结束对克里米亚鞑靼族人的政治恐怖和民族歧视行为”。
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苏共中央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1987年7月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乌克兰方面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补贴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哈萨克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应该是中央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
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安德烈•格拉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
不知这时候戈氏还记得他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吗?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