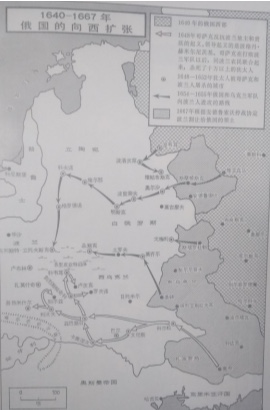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5)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8)
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1965年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以大量事实控诉了苏联当局对乌克兰人的迫害。他写道:
对1965年逮捕的人(久巴为此不得不写这本书)进行了一系列的审讯。1966年1月22日头两次审讯的方式,同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的人们熟悉的审讯差不多,罪名也是反苏宣传。其他九次审讯(虽然罪名类同)是三、四月和九月秘密进行的(应当指出,这是违反苏联法律的)。判刑八个月到六年。其中有五名被告到1970年10月,仍被关在严格管制的集中营或监狱里。
在最近两三年里,可以举出几十起这样迫害的例子。已经有几十人由于参加或牵涉到被任意恶毒地定为“民族主义”性质的某些事件而受到惩罚,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逐出高等院校,有的受到党的或共青团的纪律处分。必须指出,最近两三年来,几乎没有一次诗歌朗诵会能逃过这种或类似的“反响”,虽然大部分朗诵会是作了准备并出了通知,但到头来还是由于种种借囗而干脆被禁止(取消)了。这真是荒唐可笑!(例如,按照一项官方指示,没有市党委的批准,不准举行诗歌朗诵会;作家协会的会员要举行诗歌朗诵会,除市党委批准外,还必须经过作协的批准。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种极端官僚政治的命令,理论上还说“艺术属于人民”,值得我们想一想!)
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这些事实都说出来。我在这里只提几个最突出的,带有集体性质的事件: 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俱乐部的解散;1963年7月31日在中央文化公园举行纪念利西亚.乌克兰卡晚会的事件;1964年3月,基辅大学谢甫琴柯彩色玻璃窗饰的被毁,和事后对制造这个窗饰的青年艺术家进行的追捕;1964年和1965年5月22日禁止在基辅谢甫琴柯纪念碑前举行集会,和事后对那些到纪念碑前去的人进行了处分;1965年3月,禁止在自动机床厂举行谢甫琴柯纪念晚会,使这个晚会不得不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举行,而参加晚会的人事后又遭到了制裁(晚会的组织者、青年技师尼古拉丘克由于衣着单薄在户外停留过久和精神上受到打击,两天以后去世了);1965年初春,几十个青年新闻工作者、基辅大学毕业生由于在抗议以“民族主义”为名开除很受欢迎的大学副教授谢斯托帕尔的声明上签了名而受到惩罚;还有1964年4月27日,由大学生组织的有几万名青年参加的、讨论乌克兰文化现状的团体遭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驱散(名符其实的“驱散”);以及诸如此类的案件。
从那些第一批逮捕事件(虽然只是短期的)发生的时候起,穿着便衣的人就一直在小声地散布着关于“美元”的故事,这些故事神秘地煽动着这些“会议”(真的,要一个不负责任到了疯狂地步的官僚去想出一个比这更聪明的办法是困难的!他懂得并知道怎样去做这一件事,就是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因此,他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其他别的动机)。由于要加紧镇压青年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目前的逮捕事件和关于武器、印刷所以及那些一定会有的“美元”的神话,都是这一镇压政策的当然的发展。不管那些执行镇压的组织要不要,他们总是采取“恐怖”的形式。但是,恐怖——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或是肉体上的——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会产生新的问题。
今天,一个大国主义拥护者的非共产主义观点可以得到原谅(只要他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不管是什么色彩的),而一个乌克兰共产党员对本民族表示一丁点儿的关心也不能得到原谅,他将立即被扣上异端派的帽子。
这方面的一个最新例子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基辅大学讲课的谢斯托帕尔副教授的遭遇。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专家、有成果的研究员和模范的共产党的,员,但他还是被解除了职务,因为据说他在谈话中对民族政策的某些方面表示怀疑。必须知道,当局是怎样残酷地和顽固地要求给予他处分,尽管全体学生提出了抗议。
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己民族的命运深感不安,这一点并不奇怪,也不令人惊讶,而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在我们的许多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痛苦而且经常是矛盾的思想。许多人和集体写信给各种机构、编辑部等。大量的、未出版的、大部分是不具名的诗歌和政论文章在辗转流传(群众的写作往往是朴素的、不讲究技巧的,然而表达了内心的呼声)。人们组织了各种文学晚会和讨论会,但是,遭到禁止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党的机构为禁止这些晚会通过了多少决议,多少人为此受到惩罚啊!)乌克兰各地的青年中已感到了一种潜伏的、尚不明显的动向和觉醒。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地扩大机构,增加猖狂的活动,这就间接说明了这一令人不满的状况。由于某种原因,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在乌克兰执行民族政策。
美国《华盛顿邮报》1977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苏联当局对一位乌克兰诗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和长期迫害。
又一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苏联监狱网的深处向我们呼唤。他就是34岁的持不同政见诗人约瑟夫•捷列尔瓦。此人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信念,已在苏联监狱和精神病医院渡过了14个年头。
他最后于去年年底获释,然后在今年6月再次被捕。他现在到了苏联一个可怕的机构。然而在他获得自由的那短暂的几个月里,他生动地描写了他所受到的折磨。他写的文稿被偷送给我们。
克格勃在捷列瓦尔19岁时开始找他的麻烦。他犯了冒犯克里姆林宫的双重罪。首先,他是一个乌克兰人,是这个拒不放弃自己古老文化的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骄傲子孙。第二,他是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虔诚教徒。这个教把上帝置于国家之上。然而可能是捷列瓦尔的雄辩之才,以激动人心的语言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能力使苏联政府惊恐万状。
捷列瓦尔最初是在1962年入狱的。那时他还年轻力壮。他逃跑出去了,顶着假名过了几个月。后来他又被抓住,并被囚禁起来。
他写道: “我写的诗、笔记,甚至连我的思想都成了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乌克兰的罪恶活动的证据。”
捷列瓦尔的一天怎样生活?这位诗人回忆道: “他们让我把花岗石板搬起来堆积好……给我三根树枝来打扫地板上泼过水的单人牢房。我们被强行在一个位置上站立几天。”
毒打成了家常便饭。“宗教犯”被用电话线捆在他们的椅子上,当作羞辱嘲弄的对象。
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捷列瓦尔经常受到克格勃的折磨。克格勃要他承认他是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然而这个团体早在他三岁时就已经解散了。
“他们把我在单人牢房里关了15天。里面的气温每小时都在变化——热一小时,冷一小时。我在这儿得了甲亢病和痔疮。”
克格勃的官员对捷列瓦尔说,如果他予以合作,“他们就会在一年之内让我自由,并给我一个女人和好吃的食品。”然而继续进行的人身虐待造成了伤害。他的脊柱麻痹,鼻、嘴和耳朵开始大出血。他被转移到一家精神病院。由于他想写东西,他的手指被折断。
一天夜里,在这位不屈的诗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后,他被绑上十字架,堵上嘴,遭到看守的毒打。后来又强迫他喝厕所便池里的水。
捷列瓦尔在另一所名叫“西乔夫卡”的精神病医院里也遭到苛刻的待遇。
他于1972年被关在那里。他到后不久,“十来个人——看守人和勤杂工——就闯入牢房。他们叱责我,打我,把我绑在床上,自始至终想要知道我曾计划杀害谁。”
“我被绑在床上整整两个月,遭受看守人和勤杂工们夜间给予的拳头待遇。”
他回忆说,监狱当局极端虐待犹太犯人。“他们强迫病号吃活青蛙。他们强奸病号。一切都是为了取笑!”
捷列瓦尔控诉说,从1963年至1973年。在“西乔夫卡”共有475名难友“被杀害或折磨致死”,他们的名字在医院的病历上被注上“病亡”的字样。
捷列瓦尔从他的牢房向全世界讲话。他问道: “一个人对凶手能釆取什么态度呢?一个精神病患者能够动摇苏联国家的基础吗?当一个国家把一切有自己见解的人不是当做‘精神病患者’,就是当做本国敌人时,它必定对自己是何等没信心啊!”
哪里有大大小小的压迫,哪里就会有程度不等的反抗。乌克兰人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反抗持续了多年,外国媒体对此一直有星星点点的披露:
1966年12月,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说,据可靠人士说,在利沃夫、基辅、敖德萨、切尔诺贝利和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克进行的秘密审判中,已经对70多名大学教授、教师、学生和新闻工作者判处了长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是撰写和散发要求捍卫乌克兰文化和把乌克兰语当作乌克兰共和国的正式语言的小册子。基辅、敖德萨和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克有群众举行示威反对俄罗斯的统治,要求宪法中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平等的保证付诸实现。
1969年5月1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报道说: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强烈的。例如一个人对我说,利沃夫大学的学生是‘很乌克兰式’的。他们由于拒绝使用俄语,有时遇到麻烦。(78%左右的学生是乌克兰人,教学的主要语言是乌克兰语)
1970年4月20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说: “在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人统治的不满情绪在慢慢沸腾,就要爆发起来。在利沃夫大学,乌克兰青年拒绝在教室使用俄语。”
1971年1月14日的英国《外事报道》刊登文章指出:
继犹太人之后,乌克兰人对苏联当局来说是最严重的民族主义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乌克兰人口多(3700多万)。不断有消息说,基辅、哈尔科夫、利沃夫、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和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克等许多城市都有不满情绪。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公开参加反对派运动,但是,看来他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可能反映出,乌克兰官员们暗中对他们有某种程度的同情。
……俄国对于前波兰城市利沃夫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情绪比对乌克兰首府基辅的这种情绪更担心。
1971年12月,英国《冲突研究》杂志1971年第30期在题为《苏联的种族压迫》专辑中报道,“乌克兰民族阵线”在1971年散发一份传单,说该组织是“由包括乌克兰马列主义者在内的乌克兰爱国者组成的……它以争取乌克兰独立为目标”。这份传单谴责“俄国新沙皇”,指责“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搞种族灭绝,强迫乌克兰人迁移……等等。传单强调乌克兰有分立权,这种权利必须实现。
英国《外事报道》8月26日曾报道该组织散发的传单主张“建立乌克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传单还号召苏军中的乌克兰人在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掉转枪口,对准奴役他们的人或者“向社会主义国家投降”。
1972年5月,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文章中说: “乌克兰人在种族上、语言上虽然同俄罗斯人相近,但却有比俄罗斯更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经济上也富饶,而且是仅次于俄罗斯人的‘大民族’,所以对俄罗斯的对抗意识也很强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969年5月19日刊登文章报道说:
今天,这种民族情绪正是使苏联领导领导机构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因为这种情绪可能被那些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或者——更为现实一些——企图从莫斯得到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自由的外国的或苏联的乌克兰分子所利用。
利沃夫——乌克兰人称之为利维夫——早已是政府认为危险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中心。三年前,这里掀起了一个审判的浪潮,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由于和在西方的乌克兰移民团体有牵连而被判处苦役。
西德《播种》杂志1973年第四期披露了一条消息: “1972年4月,乌克兰利沃夫市群众起来炸断了(自来)水管,列宁大街被淹,五一节游行被迫停止。”
英国《东西方文摘》1972年第11期一篇文章披露: “1972年6月25一26日,在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几名乌克兰青年指责一个士兵,说他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结果被捕。此事激起了乌克兰人的愤怒,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砸了州的党政军办公大楼和克格勃大厦,撕毁了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打死十人,打伤多人,许多人被捕。”
同一期杂志还报道: “1972年9月19日,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包围了州委会,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民族自由。”
1973年1月4日,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报道,乌克兰作家伊凡.冈恰尔被开除出党,乌克兰哲学研究所的两名成员因为写信反对俄罗斯化而被捕,还有几名知识分子因抄写或拥有伊凡.久巴的书《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而被判刑。
另据苏联媒体报道,1961年5月16一20日,苏联当局在利沃夫进行了对“乌克兰工农同盟”的审判。其领导人分别被判处10一15年徒刑。
同年12月16一23日,苏联当局又在利沃夫进行了对“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的审判。被告均被判处重刑。
1972年4月18,《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作者、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被捕。他的罪名是: “制造和散发反苏反共材料”,“诬蔑苏维埃制度和党及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
美国历史学家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中,美国密执安安阿伯大学历史学教授斯鲍拉克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文中,开篇以《俄罗斯必须与“乌克兰”联合》为题论述了如下一个问题,可以给俄乌关系的纠葛给予解释:
英国社会学家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认为,苏联是一个“控股公司的联邦”。他们指出,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很早就发现,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更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充分利用了“控股公司的原则”。即“在一个有许多子公司的母公司中持51%的股份,其51%的股份会使帝国缔造者拥有更为有效的控制力”。
他们认为,俄罗斯人在苏联贯彻了此项原:俄罗斯人在母公司——俄罗斯联邦中占多数,而俄罗斯联邦反过来又控制了苏联。再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具有支配性的影响。1970年俄罗斯人占俄罗斯联邦人口的82.3%,居绝对支配地位。“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非俄罗斯人口占总人口的71.2%,占苏联人口的46.6%,但谁是有效的操纵力量已是无庸置疑的了”。
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与上面两位社会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一篇很有特点的题为《苏联世界大国的灾难性困境: 新类型帝国的局限性》的文章中写道: “苏联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大俄罗斯人支配着这个拥有2.7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苏联;而且他们通过国家政权和对苏联资源的占有,进而控制了一大批在地理上与之毗邻、人口达1.15亿的国家。实际上,1.35亿的大俄罗斯人从政治上控制了累积达3.85亿人口,占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
考虑到俄罗斯人只勉强构成苏联人口的多数(1977年为52%),可以说俄罗斯人要想在数量上保持对苏联的控制,那么乌克兰人在一定程度(包括白俄罗斯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学者都承认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著名的苏联政治地理学家波克希舍夫斯基认为,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地区,如在中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扮演着俄罗斯人“旅伴” 或“伙伴”的角色。美国学者阿姆斯特朗把这两个民族视为俄罗斯人的“小弟弟”。他在60年代就预言:“苏联民族政策主要的方向是要将小弟弟们(特别是乌克兰人)变成居支配地位的俄罗斯人不可分离的‘小伙伴’ ”。
自谢列斯特(前乌共第一书记)1972年倒台之后,苏联实行了乌克兰俄罗斯化的政策,这完全证实了阿姆斯特20年前所作的预言。对莫斯科而言,苏联穆斯林人口的大爆炸和波兰的政治及社会动乱(团结工会的兴起)再次证实了与“乌克兰联合”的重要性。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存在的所有帝国(英国、法国、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和俄国)中,只有俄国存在至20世纪末。这里的原因何在呢?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简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俄罗斯人设法保住了其属地,因为“其他帝国并没有做到”(他们用希特勒在二战中对乌克兰完全错误的管制为例解释了其他帝国失败的原因)。而苏维埃帝国在1991年底崩溃的重要原因是乌克兰在最后一刻拒绝加入新的苏联——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叶利钦无法设想没有乌克兰,苏联还怎么运转,于是毅然下决心步乌克兰的后尘。
以上文字让我们可以多少理解俄乌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