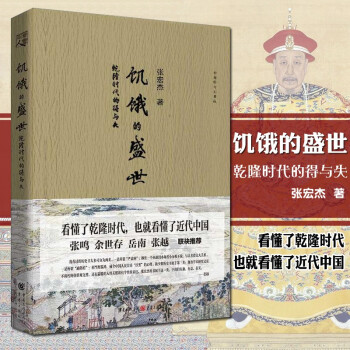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历史学家们认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实际的人口数比政府统计的还要多。乾隆晚年中国人均耕地的乐观估计是3.5亩,而同时期的英国,人均占有耕地10亩,是中国的3倍。此外,当时英国还有800万英亩荒地,也就是说,全英国每人尚能拥有1英亩(合6亩左右)的土地储备。整个欧洲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中国的耕地紧张状况如此惊讶了。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到北上的领航员。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群金发碧眼的怪物出现在东方小城的街头,我们可以想见其轰动的程度。“无数好奇群众争先恐后地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庙宇里去躲避群众。”巴罗的描写总是更生动:“人人都想把头伸到轿窗前来满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声:红毛!”(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这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国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将要来临的灾难。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英国人马上被迎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拍了个跟头。副使斯当东说:“(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者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巴罗的记载则更加详细生动: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全为商铺和货栈,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
……流动的匠作如补锅匠、剃头匠、鞋匠和铁匠,卖茶、水果、米饭和其他吃食的摊贩,以及商铺门前展示的货物,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只剩中央一线。
……一切都在移动。大路两侧也塞满了巨大的人流。或买或卖,或以货易货,各取所需。众声喧哗,既有小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捧货筐的小贩、演杂技的、变戏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医生、说相声的和卖唱的,挤成一堆。(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国人是有着商业天才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虽然英国是商业大国,但乾隆时代中国国内商业的繁盛仍然令英国人大开眼界。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轻商主义,但中国人的商业本能从来没有被熄灭过。事实上,每当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国各地的商业都会迅速勃兴。乾隆时期的商业繁盛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不过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财富基数,却肯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目睹并见证了乾隆盛世的一个侧面。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以至于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国后,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免费而且极为丰盛的供应。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他们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中国人从来都是十分勤劳的。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进行精耕细作。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郑鸣谦《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
与传说中一样的是,英国人看到的中华帝国的政治秩序确实十分井然。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
“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华帝国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极深。英国人原来担心自己带来的数量众多、体积巨大的礼品在陆地运输过程中一定会损坏几件。然而,在清帝国官员的有力组织协调下,整个运输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我们的包裹总共有六百多件,形状大小不一,尽管有多次装卸、转驳,到达京城时却没有丢失或者损坏一件。”“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甚至是兴高采烈地执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巴罗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须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国百姓。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英国人发现在暴力威胁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与传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就变了: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从翻译到欧洲的《通鉴纲目》到传教士们的《中国丛刊》。不过,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显然给了他最大的震动。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很显然,黑格尔的许多结论直接来自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记载和判断。比如他说,在欧洲,鞭笞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西方人对这种侮辱十分敏[gǎn],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的教训”。
黑格尔也认为弃婴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权利的漠视:“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黑格尔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在马戛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是远远优越于自己的,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戛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周宁《野蛮与文明:中华帝国的“东方性”黑暗中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