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我吧,不要救我”:严歌苓以名妓扶桑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避免了“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些理论所指出的偏颇与谬误
严歌苓是1989年去了美国的。她在美国获得非常广阔的视野,生活的,文学的,思想的。
她拥有关注华人移民海外生存经历的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写了若干此类小说。其中:《无出路咖啡馆》就是取材于自己与美国丈夫的真实经历,描述中国女留学生邂逅一段与美国外交官的恋情,却招来联邦调查局的盘查和骚扰。这种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异国生存困境的作品还有《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和《吴川是个黄女孩》等;描写“美国制造”的第二代土生移民的有《风筝歌》《大陆妹》与《红罗裙》等,揭示他们试图超越中国基因融入主流社会,但“他者”身份的迷思并非容易摆脱;而《扶桑》、《乖乖贝比》、《魔旦》等则讲述早期为生存漂洋过海的华人移民,在“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中以隐忍方式求生,甚至以弱胜强。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发表于1995年的《扶桑》。它讲述一百几十前一个中国女人扶桑,为寻找从未谋面的未婚夫被拐卖到旧金山,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并与白人贵族少年少年克里斯产生了一段纠结凄美的爱情。期间,她与已经成了唐人街领袖和江洋大盗的未婚夫大勇相遇,却彼此不知情。故事结尾,扶桑发现真相。在大勇为了维护扶桑的尊严,甘心为警方所俘,即将被处死之际,俩人在刑场上举办了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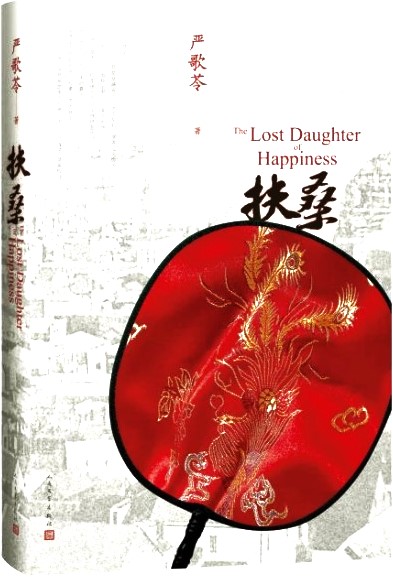
严歌苓怎么想到创作《扶桑》呢?就是被一张照片打动。1993年的一个中午,严歌苓等丈夫劳伦斯吃饭时,在附近的楼下看到一个箭头指引“中国移民博物馆”。那是一个在地下室的陈列馆,在那里严歌苓看到一幅巨大的画像,其中焦点就是一个盛装的、身形较为高大的中国妓女,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严歌苓说她深深地被这个带有某种秘密的、象征性的女子身上的气质打动了,给她极大冲击,于是便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寻找的过程中,严歌苓对中国移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44年才解除的“排华法案”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务工的华人不准带家属到美国。于是妓院就应运而生了,开在唐人街和各种修铁路的沿线,大概有三千个女孩被贩卖到那里。上述移民史博物馆照片中的“名妓”就是这三千女孩中的一员。这些妓女在解决华人的生理问题之余,还吸引了很多白人的小孩。严歌苓觉得,“这是一场东西方的大邂逅”,决心要写出来。结果成就一部杰作。
说起来,这部严歌苓早期的重要作品差一点就不见天日。当时,她患有抑郁症,在近乎疯狂的写作中自我搏斗,《扶桑》完稿之后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1995年第十七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这部手稿也许会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里。
后来,《扶桑》英译本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于2002年出版,并获评当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评价非常高。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它是严歌苓“历次获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巧妙运用素材展现新意,“叙情状物,流畅娴熟”,可读性极高。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怪异而震撼的小说。严歌苓如同一位镜头简练而丰富的导演,不动声色地为人们展开一幅幅既柔情又惨烈的生动画面。英国《观察家报》称赞严歌苓精湛的故事描写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有关永恒的不屈不挠的爱情故事。英国另一家媒体《出版新闻报》指出,这是一部大胆、性感而令人激动的有关禁锢与爱情的小说。作者以极为独特的语言,表现了生动的历史场面。美国《纽约时报》盛赞《扶桑》是一部以丰富感性书写的令人难以平静的作品。说它呈现错综复杂的种族间情爱,是对神秘莫测的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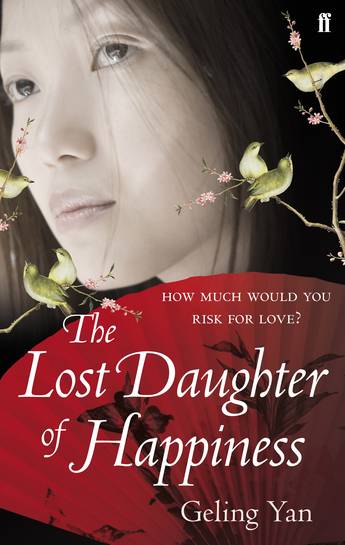
但是也有人指责说,严歌苓在对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上是表现“东方主义奇观”。指责者认为,严歌苓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立场对“东方主义”和种族“奇观”进行颠覆,而相反的却似乎深深自恋于这种“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再次言说,因而《扶桑》表现出一种“自我东方主义”,成了她勤奋多产的创作中“一部令人遗憾的讨巧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指责是需要驳斥的。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在他富有争议的名著Orientalism里专门另立特别定义,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或认识体系。于是,“东方主义”就是西方对于东方一种构建的无知和有意的自欺,在这种无知和自欺中,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进步所作的一种构建,这样的无知和自欺被适用于文学、艺术、思想的任何领域,然后投射到东方,使东方沦为西方满足西方优越感的工具。“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便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所谓“东方主义”,一定有它的对应物,不妨称之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而所谓“西方主义”,是指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包括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的认同、误解和有意的歪曲,也包括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还包括了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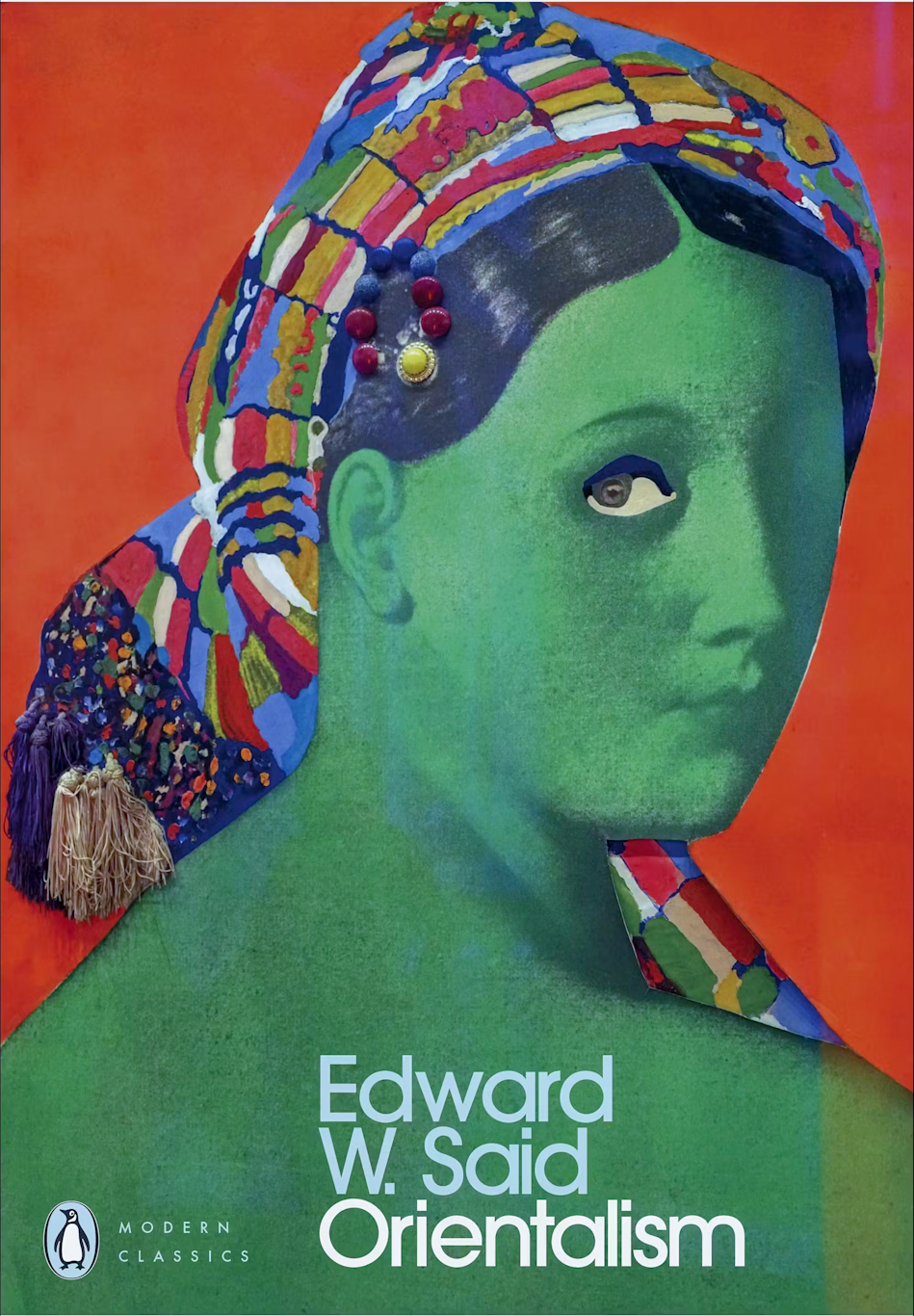
也许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不会特别理会“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些理论。我想指出的是,正好和对她的指责相反,严歌苓正是难能可贵地以名妓扶桑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避免了这些理论所指出的偏颇与谬误。
首先,对扶桑以及围绕这个文学形象对一百几十前美国的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是否真实?是否是对“东方文化”的“藐视”和“任意虚构”?这是关键所在。而任何认真阅读此书的人都会否认上述的指责。
其实,指责者自己已经为严歌苓“解套”了。他说:
一方面,作者采用了一个十足的“东方主义”的观看情境,书中扶桑的种种魅力展现,都是通过一个十二岁的白人小嫖客克里斯的眼睛看到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恋爱中的人神化了的东方女神的形象……另一方面,以严歌苓的聪慧,她并不是没有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建构毫无意识,她甚至有意识地在本文叙事中对这种凝视/观看的权力关系和与此相关的“阐释结”进行一种“元叙事”或者说“解构”式的呈现。
既然有这样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那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如指责者说的构成“一个吊诡的困境”,更不“令人遗憾”。
扶桑的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爱我吧,不要救我”。可以来爱我,只是平等地来爱就好;不要来救我,我也不需要谁来救。这就是扶桑内心的潜台词。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扶桑其实是很“存在主义”的。这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总是微笑,可以吃所有的苦,她的不反抗并非逆来顺受。“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扶桑身上的带有神性的“古典式的善良与隐忍”与“母性的光辉”,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的确,东方弱女子扶桑“谜一样”的魅力让白人少年克里斯深深沉醉。他受诱惑,他想要拯救扶桑,他像许多基督教男性具有一个“我要救你”的理想。但他无从真正了解扶桑,懂得扶桑,于是他的“拯救”,必然是一个荒谬的悲剧。还有另外一个华裔男人大勇,这个可称之为“东方恶霸”的人,他虐待宽容忍耐的扶桑,最终却为了扶桑去对抗白人而失去性命。这又另一个荒谬的悲剧。如论者指出,严歌苓以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邃的思想观念,让扶桑分别与克里斯和大勇的情爱故事在性别、种族、身份方面具有多重的文化象征意义。扶桑以她东方式的“地母”形象征服了西方的拯救者、东方的男权者以及具有优越意识的现代人,使“弱者不弱”焕发出东方文化内涵的神性光辉。这部小说没有简单地描写血仇,恰恰是通过扶桑这位女性所表现的爱与宽宥,来呈现不同文明与种族间的差异性、矛盾的复杂性、人性的多重性。《扶桑》初版至今近三十年,不但没有因时光的逝去被人遗忘,而且置于视野更为广阔的今天,显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无论是对于西方或者东方的读者来说,《扶桑》均成为一种超脱于读者既有文化语境、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的完美体验。
关于《东方主义》之类的理论,我还想多说两句。我曾在其他文章指出,如果说萨义德的大著《东方主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其新颖以及某种合理的批判性吸人眼球,那么,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发生过而且仍然存在伊斯兰恐怖主义全球性的威胁,又出现中共习近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想及其以空前力度在全球特别在非洲的推进,在世界局势业已大大改观的状况下,此书总体观点的可疑越来越为人看清了。今天,萨义德原来就争议甚大的观点常常沦为某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严肃的学术讨论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未完待续)
(2024年7月28日完稿于悉尼,经严歌苓女士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