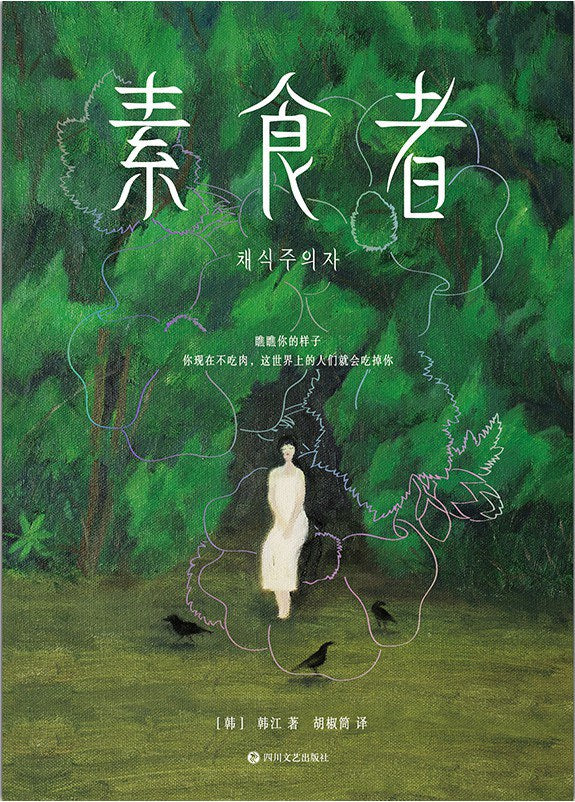他对小姨子产生异样的感情,是在妻子提及胎记之后。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他对小姨子从未有过半点非分之想。如今,每当他回想起小姨子住在家里时的一举一动,便会有一种刺激性的快感贯穿自己的全身。她坐在阳台张开双手做出各种手影时的入迷表情;帮儿子洗漱时宽松的运动裤下露出的白皙脚踝;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半开的双腿,以及散乱的头发……每当想起这些,他的身体都会不由得发烫。但在这些记忆之上,都印有那块别人早已退化的、从身体上消失的、只存在于儿子屁股和后背的胎记。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触摸到新生儿屁股时,柔软的触感带来的喜悦。那种喜悦与这些记忆重叠在一起,使得那从未见过的臀部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散发出了透明的光亮。
如今她不吃肉,只吃谷物和蔬菜。这让他觉得与那块如同绿叶般的胎记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幅最完美的画面。从她的动脉喷出的鲜血浸湿了他的白衬衫,然后又凝固成了红豆粥色的血渍,这些都让他觉得是一种无法用命运来解释的、令人震撼的暗示。
她住在位于D女子大学附近的小巷里。按照妻子的嘱咐,他双手提着满满的水果来到一栋公寓的门口。济州岛产的橘子、苹果和梨,还有不是当季水果的草莓。虽然他感到提着水果的手和胳膊阵阵酸痛,但还是站在原地犹豫不决起来。因为想到等下走进她的房间,将要面对她,一种近似于恐惧的紧张感便油然而生。
结果他还是放下了手里的水果,然后掏出手机拨打了她的电话。在铃声响十次以前,她是不会接电话的。他重新拎起水果开始爬楼梯,来到三楼的转角处,按了一下画有十六分音符的门铃。如他所料,没有人来应门。他转了一下门把手,门意外地开了。为了擦拭满头的冷汗,他摘掉棒球帽,然后又立刻戴了回去。他站在门口整理好衣服,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开门走了进去。
十月初的秋日阳光照进朝南的一居室套房,光线一直延伸至厨房,带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也许妻子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小姨子,所以他才觉得地上的衣服很眼熟。虽然地上有几团手指大小的灰尘,但整间屋子没有凌乱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没什么家具吧。
他把双手提着的水果放在玄关处,脱下皮鞋走进了屋里,屋内没有任何的动静。人去哪儿了呢?难道是知道自己要来,所以出门了?房间里没有电视,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两个插座和一旁的电线,卧室兼客厅的一侧放着妻子安装的电话,另一侧有一张床垫,上面放有一张蓬松成洞穴模样的被子,像有人刚从里面钻出来似的。
他觉得房间里的空气有些浑浊,正把阳台的窗户开到一半时,突然察觉到背后有动静。他吓得屏住了呼吸,转过头去。
只见她正打开浴室的门走了出来。因为没有听到流水声,所以他根本没想到她在里面。但更让他吃惊的是,她一丝不挂赤裸着身体。她似乎感到很意外,呆呆地站在原地,赤裸的身上没有一滴水。几秒后,她弯腰捡起地上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她表现出的不是害羞和惊慌,而是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有的从容态度。
她没有转过身去,而是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穿起了衣服。按理说,他应该转移视线或是赶紧离开房间,但他却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她。此时的她不像最初吃素时那么干瘦了,住院期间体重有所回升,住在他家的时候饮食也调整得很好,因此胸部又跟从前一样圆润饱满了。她的腰部呈现出惊人的凹形曲线,那里长着适当的体毛,大腿连接小腿的线条虽谈不上饱满,但仅凭没有赘肉这一点已经足够迷人了。那是吸引人静静观赏,而绝非引诱性欲的身体。当她穿好所有的衣服以后,他这才意识到没有看到臀部的那块胎记。
“对不起。”
他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我看门开着,还以为你出去了。”
“……没关系。”
她用一贯的口吻回答说:“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很舒服。”
如果是这样……他迅速调转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画面。这也就是说,她在家的时候都是光着身子的。想到这,他突然意识到当下比刚才看到她裸体时还要紧张,而且那里也开始膨胀了。为了遮掩勃起的状态,他一边摘下棒球帽挡在那里,一边弯腰坐在了地上。
“家里什么也没有……”
就像刚才看到的那样,她没有穿内裤,只套了件深灰色的运动裤转身走进了厨房。他望着她那没有肉感的臀部左右摆动时,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喉结咽了一下口水。
“别麻烦了,就吃那些水果吧。”
为了争取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开口说道。
“那吃水果?”
她走到玄关拿起苹果和水梨,然后又走回洗碗槽。他听着流水和盘子碰撞的声音,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墙上插座的洞口和电话的按钮上。但适得其反的是,她的阴部和画有绿叶的臀部,以及反复构思的交合体位更加鲜明且重叠地充斥着他的大脑。
当她端着放有苹果和梨的盘子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时,为了掩饰自己那双猥琐的眼睛,他低下了头。
“……不知道苹果好不好吃。”
短暂的沉默过后,她开口说:
“姐夫没必要专门来看我。”
“嗯?”
她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你们不用为我操心,我已经找工作了。医生说不要再做一个人埋头苦干的事,所以我打算去百货公司上班,上个星期还去面试了呢。”
“……是吗?”
这真是出乎意料。记得有一次,妹夫趁着醉意在电话里对他说:“如果是你,你能忍受一个疯疯癫癫,要靠吃精神科开的药,一辈子只能寄生在老公身上的女人吗?”但妹夫搞错了,她似乎没有疯到那种地步。
“不然去你姐的店里怎么样?”
他斜眼看着地面,终于说出了此行来的目的。
“你姐觉得那么多钱与其给外人,还不如给自己人。况且,都是一家人也信得过。我们还能就近照顾你,你姐也能安心。再说,店里的活儿可比百货公司轻松多了。”
渐渐恢复平静后,他说出了这番话。当他可以直视她的脸时,才发现她的表情犹如修行者一样平静,平静得让人觉得她像是经历了百般沧桑和磨难。那平静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他不禁自责起来,只因她没有穿衣服就把人家当成一幅春宫图来欣赏。但无可厚非的是,自己用双眼录下的短暂画面成了那条随时可以引爆火花的导火线。
“吃点梨吧。”
她把盘子推向他。
“你也吃一点。”
她没有用叉子,而是直接用手拿起一块梨放进了嘴里。一股冲动油然而生,他想拥抱她的肩膀;吸吮那沾有梨汁、黏糊糊的手指;舔舐那甜甜的嘴唇和舌尖;用力拉下那条宽松的运动裤。他对这股冲动感到惧怕,于是慢慢地把头转了过去。
“等一下。”
他边穿鞋边说:
“跟我出去走走吧。”
“……去哪儿?”
“我们边走边聊。”
“姐夫刚才说的事,我会考虑的。”
“不是那件事……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他望着她犹豫不决的表情。眼下只要能从这无时无刻不在折磨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中解脱出来,只要不待在这个危险的空间,去哪儿都无所谓。
“那就在这里说吧。”
“不,我想走走,你也在家待了一整天,不觉得闷吗?”
她最终被说服了,于是脚踩拖鞋跟着他走出了家门。他们默默地走出小巷,沿着大路继续往前走。直到看到一家冰激凌连锁店,他这才开口问道:
“你喜欢吃冰激凌吗?”
她跟做作的女朋友一样,朝他微微一笑。
他们坐在店里靠窗的位置,他默默地看着她用小木勺舀起冰激凌,然后用舌头舔舐。他觉得仿佛有电线把自己的身体跟她的舌头绑在了一起,每当她伸出舌头,自己就会像受到电击一样颤抖不已。
那时他觉得或许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让自己从地狱中解脱出来,那就是实现这个欲望。
“我想拜托你……”
舌尖上沾着白色冰激凌的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单眼皮下不大不小的眼睛隐隐地闪烁着光亮。
“我想请你做模特。”
她没有笑,也不显得慌张,仿佛看穿了他内心似的以安静的眼神凝视着他。
“你来看过我的展览吗?”
“嗯。”
“就是类似的影像创作,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不过……必须得赤裸身体。”
他察觉到自己变得有胆量了,而且不再流汗,手也不再抖了。仿佛头顶放了一个冰袋,脑袋也变得冷静了。
“脱光衣服,然后在身上进行彩绘。”
她依旧以安静的眼神凝视着他,然后淡淡地开口说:
“……然后呢?”
“只要这样一直到拍摄结束就可以了。”
“在身上……画画?”
“会画一些花朵。”
他看到她的目光动摇了一下,但也有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不会太累的,只要一两个小时。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他觉得自己把要讲的话都说完了,于是不抱任何希望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那份冰激凌,上面撒着碾碎的花生和成片的杏仁。冰激凌在慢慢融化,静静地流淌着。
“……在哪里?”
就在他入神地盯着融化的冰激凌时,突然听到了她的提问。她正把最后一口冰激凌送进嘴里,没有血色的嘴角沾了一点奶油。
“我打算借用朋友的工作室。”
她的表情十分冷漠,根本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
“嗯……你姐那边……”
他觉得讲出这句话多余,但又不得不说,于是结结巴巴得像是丧失了信心地说:
“你姐那边……要保密。”
她没有给出任何肯定或是否定的反应。他屏住呼吸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脸,试图从她的沉默中找寻出答案。
阳光从宽敞的窗户照射进来,M的工作室因此变得很暖和。与其说这是工作室,还不如说更像是一百多平方米的画廊。M的画挂在醒目的地方,各种画具整理得井然有序。为了这次创作,他也做了全方位的准备,但还是忍不住想试试这些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画具。
为了寻找有自然光的工作室,他只好去拜托关系并没有那么熟的大学同学M。三十二岁的M可以说是同届人里最早在首尔市内的大学里任教的人了,如今他的面相、服装和态度都散发着大学教授的派头。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找我帮忙。”
一个小时前,M在工作室给他沏了一杯茶,递过钥匙时说道:
“像这种事,随时跟我说,我白天都在学校。”
他盯着M比自己更显凸起的小腹,接过了那把钥匙。他心想,M肯定也有自己的欲望和欲望导致的烦恼,只是他没有表露出来罢了。看着M难以掩饰的烦恼——凸起的小腹,他得到了一种猥琐的心理安慰。对M而言,至少存在着对于啤酒肚的烦恼和些许的羞耻心,以及对于年轻体魄的怀念吧。
他把M那些看起来俗套且稍稍挡住了窗户的画清到了一边,然后在阳光直射的木地板上铺了一张白床垫。他躺在床垫上,事先确认了一下她躺下去时将会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高高的天花板上的木纹、窗外的天空。虽然有些凉,但还是可以忍受的硬床垫,以及背部柔软的触感。他翻过身趴在上面,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M的画、另一侧地板上的阴影和没有使用的壁炉的煤灰。
他准备好带来的画具,取出PD100摄像机确认了电量,然后将出于担心拍摄时间过长而准备的照明器材架在了一旁,最后翻看了一眼素描本,跟着又塞回了包里。他脱下夹克,挽起袖子,等待着她。临近下午三点,差不多是她抵达地铁站的时间了。他抓起夹克,穿上皮鞋,呼吸着郊外新鲜的空气,朝地铁站走去。
这时手机响了,他边走边接起电话。
“是我。”
是妻子打来的电话。
“我今天下班可能有点晚,打工的孩子又没来,可七点得去幼儿园接智宇。”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也没空,九点前脱不开身。”
话筒里传来妻子的叹气声。
“知道了,那只能拜托709号的阿姨帮忙照看孩子到九点了。”
他们没有再多说一句废话,直接挂断了电话。近来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仅靠孩子连接的、不存在其他任何牵绊的同志关系。
几天前,从小姨子家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以无法控制的冲动在黑暗中抱住了妻子。那种新婚时都未曾有过的强烈欲望令他大吃一惊,妻子也被他的举动吓坏了。
“你怎么了?”
他不想听到妻子的鼻音,于是用手捂住了她的嘴。面对黑暗中妻子若隐若现的鼻梁、嘴唇和纤细的颈线,他想象着小姨子的样子蠕动起了自己的身体。他咬住妻子硬起的乳头,扒下她的内裤。当脑海中那又小又绿的花瓣若隐若现时,他闭起双眼抹去了妻子的脸。
当一切结束时,他才察觉到妻子正在哭泣。但他不知道这是因为激情,还是某种自己不晓得的感情。
“好可怕。”妻子背对着他喃喃自语道。不,他听到的似乎是——“你好可怕”。但那时他已经昏昏入睡了,所以无从确认妻子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话,也不知道她抽泣了多久。
但隔天一早,妻子的态度跟往常一样,刚刚通话时的口吻也毫无异常。关于那件事,妻子非但只字未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感。偶尔妻子充满压抑的语气和一成不变的叹息声总是令他心情不悦。为了打消这种不悦的心情,他加快了脚步。
没想到小姨子提早到了地铁站出口,她歪斜着身体坐在台阶上,看样子已经从站里出来很久了。她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搭配着一件厚厚的褐色毛衣,就跟独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一样。他没有立刻走过去打招呼,而是像着了迷似的呆呆地望着她擦拭汗水的脸和长久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轮廓。
“把衣服脱掉。”
面对愣愣地站在窗边张望着白杨树的她,他低声说道。午后寂静的阳光照得白床垫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没有转过身来。就在他以为她没有听到,准备再讲一遍时,她抬起胳膊脱掉了毛衣。当她脱掉里面的白短袖后,他看到了她没有穿胸罩的背。接着她脱下那条破旧的牛仔裤,两瓣白皙的臀部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屏住呼吸,盯着她的臀部。一对名为“天使微笑”的酒窝镶嵌在那两座肉乎乎的小山丘上方。那块拇指大小的斑点,果然印在左侧臀部的上方。他百思不得其解,那东西怎么还会留在那里?那显然是一块近似瘀青般的、散发着淡绿色光的胎记。他忽然意识到,这让人联想到太古的、进化前的或是光合作用的痕迹,与性毫无关联,它反而让人感受到了某种植物性的东西。
过了半天,他这才抬起头把视线从胎记上移开,打量了一遍她赤裸的身体。她根本不像是第一次做模特的人。考虑到小姨子和姐夫的关系,她那种沉着冷静的态度反而令他很不自在。眼前的画面让他突然想起,她之所以被关进封闭式病房,是因为她在割腕后的第二天赤裸着身体坐在医院的喷水池前,以及经常在医院里脱光衣服晒太阳,出院时间也因此延迟了。
“坐下来吗?”
她问。
“不,先趴下吧。”
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她趴在床垫上,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对赤裸的身体,他感到自己的体内有某种冲动的情绪在横冲直撞。为了解读那是怎样的情绪,他紧锁起了眉头。
“等一下,不要动。”
他把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调整了一下支架的高度。当找到能拍摄到她全身的角度后,他拿起了调色板和画笔。他希望从人体彩绘进行拍摄。
他先把垂在她肩膀上的头发撩开,然后从后颈开始下笔。紫色和红色半开的花蕾在她的背后绽放开来,细细的花茎沿着她的侧腰延伸下来。当花茎延伸到右侧臀部时,一朵紫色的花朵彻底绽放开来,花心处伸展出厚实的黄色雌蕊。印有胎记的左侧臀部留下了空白,他拿起大笔在青色的胎记周围上了一层淡绿色,使得那如同花瓣般的胎记更为突出了。
每当画笔撩过她的肌肤时,她都会像怕痒似的微微抖动一下身体。他感受着她的肉体,浑身充满了触电般的感觉。这不是单纯的性欲,而是不断触碰着某种根源的、高达数十万伏特电流的感动。
最后当他完成从大腿到纤细的脚踝的花茎和树叶时,整个人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画好了。”
他说道。
“以这个姿势再趴一会儿。”
他从三脚架上取下摄像机,开始进行近距离的拍摄,他拉近镜头捕捉着每一朵花,然后用特写镜头拍摄起了她的颈线、凌乱的头发和紧紧按在床垫上的双手,以及长着胎记的臀部。最后拍摄完她的全身,他关掉了摄像机的电源。
“好了,可以起来了。”
他略感疲惫地坐在了壁炉前的沙发上。她感到手脚有些发麻,勉强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你不冷吗?”
他一边擦汗一边站起身,把自己的夹克披在了她的肩膀上。
“累不累?”
她露出了笑容,那是一抹淡淡的,却蕴含着力量的微笑;是意味着不会拒绝,也不会畏惧的微笑。
他这才醒悟到,最初她趴在床垫上时,自己感受到的冲击意味着什么。她拥有着排除了一切欲望的肉体,这是与年轻女子所拥有的美丽肉体相互矛盾的。一种奇异的虚无从这种矛盾中渗了出来,但它不只是虚无,更是强有力的虚无。就像从宽敞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以及虽然肉眼看不到却不停散落四处的肉体之美……那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复杂感情涌上心头,过去一年来折磨着自己的欲望也因此平静了下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