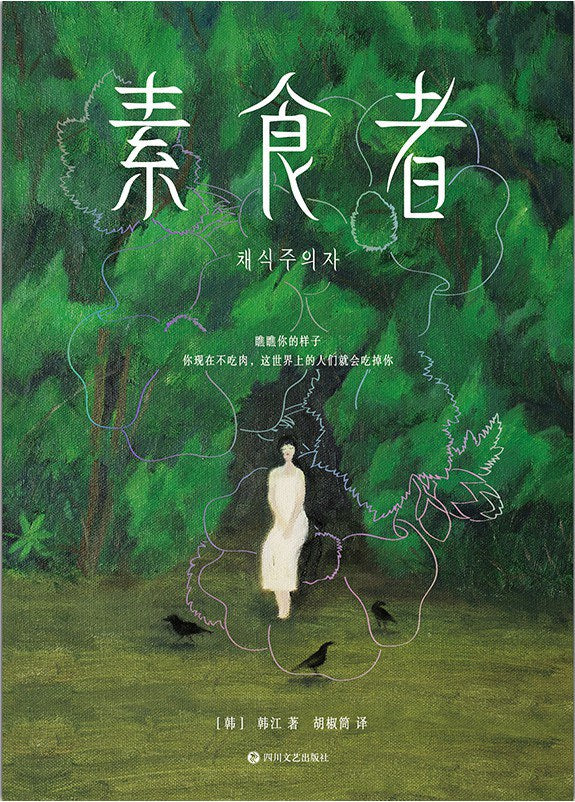时间流逝。
医生给她的三十分钟并不长。不知从何时开始,窗外的雨变小了。从挂在窗户蚊帐上的雨滴可以看出,雨似乎停了。
她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打开包从里面取出大大小小的保鲜盒。她望着英惠呆滞的眼神,打开了最小的保鲜盒,顿时一股清香在充斥着湿气的病房里弥漫开来。
“英惠啊,这是桃子,你最喜欢的黄桃罐头。夏天产桃子的时候,你不是也跟小孩一样爱买这个吃吗?”
她用叉子叉了一块软乎乎的桃子,送到英惠的鼻子下面。
“你闻闻……不想吃吗?”
第二个保鲜盒里装着块状的西瓜。
“还记得小时候,每次我把西瓜切成两半,你就会跑过来要闻一闻。有的西瓜刚一下刀就裂开了,那股甜味很快就在家里散开了。”
英惠丝毫没有反应。如果人挨饿三个月,就会变成这样吗?怎么连头都变小了。英惠的脸,已经小到看不出是成年人的脸了。
她小心翼翼地用西瓜碰了一下英惠的嘴唇,然后试着用手指扒开妹妹的嘴唇,但英惠依旧紧闭着嘴巴。
“……英惠啊。”
她小声唤了一下。
“你倒是说句话啊。”
她压抑着想要摇晃妹妹肩膀、扒开她的嘴巴的冲动。她恨不得贴在英惠的耳边大喊大叫,哪怕是震破她的耳膜。“你这是做什么?听不到我讲话吗?你想死?真的不想活了吗?”她茫然地感受着自己体内像是炙热的泡沫在沸腾着愤怒。
时间流逝。
她转过头看向窗外,看来雨真的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被雨淋湿的树木仍保持着沉默。透过三楼病房的窗户,祝圣山郁郁葱葱的休养林尽收眼底,就连山脚下的那一大片树林也在保持着沉默。
她从包里取出保温瓶,把木瓜茶倒进准备好的不锈钢杯里。
“英惠,喝一口吧,泡得很入味呢。”
她自己先喝了一口,舌尖上的余味散发出甘甜的香气。她把茶倒在手帕上,然后润湿了英惠的嘴唇。但英惠还是毫无反应。
她开口说:
“你想这么死掉吗?你不想吧,你不是说要成为树吗?那得吃东西啊,必须得活下去啊。”
话说到一半,她突然屏住了呼吸。因为一种不想认可的怀疑涌上了心头。难道是自己理解错了吗?英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寻死呢?
不会的,你不是想寻死。她在心底默念着。
在英惠彻底不肯开口讲话以前,也就是一个月前,她曾对姐姐说:
“姐,让我离开这里。”
那时的英惠已经瘦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有气无力,很难讲出一句完整的话,所以只能断断续续、喘着粗气说:
“他们总让我吃东西……我不想吃,可他们硬是逼着我吃。上次吃完我就吐了……昨天我刚吃完东西,他们就给我打安定剂。姐,我不想打那种针……你就让我出去吧。我讨厌待在这里。”
她握着英惠骨瘦如柴的手说:
“你现在连路都走不了,多亏打了点滴才能撑到现在……让你回家,你肯吃饭吗?你答应我肯吃饭的话,我就接你回家。”
那时,她注意到英惠眼中的光熄灭了。
“英惠,你倒是讲话啊,如果你肯答应姐姐……”
英惠转过头没有理她,跟着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原来你也跟他们一样。”
“你这是什么话。我……”
“没有人能理解我……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都一样……他们根本不想理解我……他们只会给我吃药、打针。”
英惠的声音虽然缓慢、低沉,但却十分坚定,语气也冷静得令人惊讶。最终,她忍无可忍,歇斯底里地喊道:
“我这不是怕你死掉吗?!”
英惠转过头来,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她。片刻过后,英惠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为什么不能死?”
我为什么不能死?
面对这样的问题,她要如何回答呢?是不是应该暴跳如雷地质问她,怎么能讲出这种话?
很久以前,她和妹妹曾在山里迷了路。当时,九岁的英惠对她说,我们干脆不要回去了,但那时的她未能理解妹妹的用意。
“你胡说什么呢?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快找到下山的路。”
多年以后,她才理解了当时的英惠。父亲总是对英惠动粗,虽然英浩也偶尔挨打,但至少他还能靠欺负街坊邻居家的小孩发泄一下情绪。因为身为长女的她要代替终日辛劳的母亲给父亲煮醒酒汤,所以父亲对她多少会收敛一些。然而温顺且固执的英惠却不懂看父亲的脸色行事,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但如今她明白了,那时身为长女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早熟,而是出于卑怯,那仅仅是一种求生的生存方式罢了。
难道说自己无法阻止吗?阻止那些无人知晓的东西渗透进英惠的骨髓。她始终没有忘记,夜幕降临后,英惠总是一个人站在大门口的孤独背影。那天,她们走到山对面,拦到了一辆开往村子的犁地机。黄昏时分,犁地机驶在陌生的路上,虽然她安心地松了一口气,但英惠并不开心。一路上,英惠只是默默地望着暮色中的白杨树。
如果那天晚上真的像英惠说的那样离家出走的话,就能改变结局了吗?
那天的家庭聚餐,如果在父亲下手打英惠以前,她能死死地抓着父亲的胳膊不放的话,就能改变结局了吗?
英惠第一次带妹夫回家时,不知为什么那个面相冰冷的男人就没给她留下好印象。如果当初她反对这桩婚事的话,就能改变结局了吗?
她有时会潜心思考这些左右了英惠人生的变数,然而在英惠的人生棋盘上,无论她如何举棋不定,都只是徒劳无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停止思考。
如果她没有跟他结婚的话。
当她思考到这个问题时,脑袋迟钝得快要麻痹了。
她不确信自己是否爱他。明明在下意识里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嫁给了他。也许她是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价?虽然他从事的行业没有经济来源,但她欣赏婆家人大多是教育者和医生的家庭氛围,她努力配合他的言谈举止、品位、口味和睡觉习惯。最初他们也跟普通的夫妻一样,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但没过多久她便对一些事情死了心。但这样做真的只是为了他吗?共度的八年婚姻生活,正如他带给自己绝望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让他倍感挫败呢?
九个月前,在临近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他打来一次电话。话筒里频繁传出投硬币的声响,她由此猜测他应该是在很远的地方。
“我很想智宇。”
那令人熟悉的低沉、紧张、故作淡定的声音,如同一把钝刀刺进了她的胸膛。
“……能让我跟儿子见一面吗?”
果然是他讲话的风格,他没说一句对不起,更没有恳求原谅,只是提到了孩子,就连英惠怎么样了也没问一句。
她知道他有多敏感,也知道他是一个自尊心容易受挫的人。她更加清楚的是,如果当下拒绝他的话,那么他就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再打来电话。
她明知道会这样,不,正因为知道会这样,所以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深夜的公共电话亭,破旧的运动鞋,褴褛的衣服,一脸绝望的中年男人。她摇了摇头,抹去了他在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但很快眼前又静静浮现出了他以鸟的姿势想要冲出英惠家阳台栏杆的画面,他那么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翅膀,可当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飞起来。
她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双眼,那张充满恐惧的脸是如此陌生,那不再是自己想要尊敬的人的脸,不再是心甘情愿去忍耐和照顾的人的脸。她终于醒悟到,自己所了解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罢了。
“我不认识你。”
她放下紧握的话筒,喃喃自语道。
没有必要原谅和恳求原谅,因为我不认识你。
听到电话再次响起,她直接拔掉了电话线。隔天一早,她重新插好电话线,但正如预料的那样,他再也没打来过电话了。
时间继续流逝。
英惠闭上了眼睛。她是睡着了吗?她能闻到刚才那些水果的味道吗?
她望着英惠凸起的颧骨、凹陷的眼窝和双颊。她感到自己的呼吸在加速,于是起身走到窗边。暗灰色的天空渐渐转晴,四周出现了阳光,祝圣山的树林终于找回了夏日应有的生机。那天晚上发现英惠的地点,应该就是远处山坡的某一处。
英惠打着点滴,躺在床上说:
“我听到了声音,我听到有人在叫我,所以去了那里……但到了那里,声音消失了……所以我才站在那里等。”
“等什么?”
听到她这样问,英惠眼里顿时闪现出了光芒,她伸出没有打针的手一把抓住姐姐的手。那股握力的强度令她惊讶不已。
“融化在雨水里……一切融化在雨水里……我要融入土壤。只有这么做,我才能萌芽新生。”
熙珠激动的声音突然闯进了她的脑海。
“英惠怎么办,听说她会死掉。”
她的耳朵嗡嗡作响,就跟飞机一飞冲天时一样。
她也有一个无法向人倾诉的秘密,也许未来她也不会对任何人讲。
两年前的四月,也就是他拍下英惠的那年春天,她的阴道出血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洗被血浸湿的内裤时,她都会想起几个月前从英惠的手腕喷出的鲜血。她害怕去医院,所以一直拖着不肯就医。她担心如果是得了不治之症,那还有多少时日可活呢?一年?六个月?或者,只有三个月?那时,她首先回想起了与他共度的漫长岁月。那是一段没有喜悦与激情,彻底靠忍耐和关怀维持的时间,也是她自己选择的时间。
那天上午,她终于决定去生智宇的妇产科看病了。她站在往十里地铁站等待着迟迟不来的换乘地铁,遥望着车站对面临时搭建起的、破破烂烂的简易房屋和毫无人迹的空地上长满的野草,她突然觉得自己仿佛从未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但这是事实,她从未真正地活过。有记忆以来,童年对她而言,不过是咬牙坚持过来的日子罢了。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这种确信促使她从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她为人老实,任劳任怨,因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眼前颓废的建筑和杂乱无章的野草,她竟变成了一个从未活过的孩子。
她隐藏起紧张和羞耻心,躺在了检查床上,中年男医生把冰冷的腹腔镜插入她的阴道,然后切除了像舌头一样黏在阴道壁上的息肉。刺痛使得她不由自主地扭动起了身体。
“原来是息肉引起的出血。现在已经都摘除干净了,未来几天的出血量会变多,但过几天就会止住了。卵巢没有异常,您大可放心。”
那瞬间,她感受到了意外的痛苦。活下来的时间无限地延长了,但这一点也没有让她觉得开心。过去一个月里忧心忡忡的不治之症,竟然只是一个无谓的小烦恼。回家的路上,她站在往十里的站台上,感觉到双腿发软,不仅仅是因为刚才手术部位的疼痛。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地铁驶向站台,她倒退几步躲在了铁质座椅的后面。她很害怕,因为内心总觉得有一个人正要把自己推下站台。
她该如何解释那天之后所经历的四个多月时间呢?出血又持续了两周,直到伤口愈合后才停止。但她始终觉得体内存在着伤口,而且那个深不见底的伤口仿佛比身体还要大,就要把自己彻底吞噬了一样。
她默默期待着春去夏来。来买化妆品的女生穿着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单薄了。她跟往常一样笑脸迎客,热情地推荐产品,适当地打些折扣,大方地送客人试用品和赠品。她会把新产品的海报贴在醒目的位置,并且毫无差池地更换顾客评价差的美容师。但是,等到晚上把店交给店员,自己要去接智宇的时候,她就会像一座死气沉沉的孤坟。即使走在充溢着音乐和情侣的街道,她也始终觉得那个深不见底的伤口正在张着大嘴要把自己吞噬掉。她拖着汗流浃背的身体,穿过人潮拥挤的街道。
闷热的夏天早晚开始转凉了。经常连续数日不回家的他,在某天凌晨跟做贼似的抱住了她,但她推开了他。
“我累了,真的很累。”
但他低声说:
“你就忍一下。”
她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切。她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听到过无数次这样的话,所以她觉得只要熬过那一刻,就能换回几日的宁静,而且假装昏睡可以抹去痛苦与耻辱。一觉醒来,吃早餐的时候,她总是冒出想用筷子戳自己眼睛的冲动,或是把茶壶里的开水浇在自己的头顶。
他入睡后,卧室里变得静悄悄的。她把侧躺着的孩子放平,黑暗中,她依稀发现这对父子的侧脸相似处竟然少得可怜。
事实上,生活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就像现在一样,未来也会这样生活下去的。因为除此以外,她别无选择。
睡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压迫着颈部的疲惫感。她觉得全身上下的水分已经蒸发掉了,干燥的肉体变得摇摇欲坠。
她走出卧室,望向阳台漆黑的窗户,昨晚智宇玩过的玩具、沙发、电视、厨房的橱柜和煤气灶的油渍。她就跟初次到访的客人一样环顾着四周。突然胸口一阵莫名的痛楚,那种压迫感犹如房子在缩小,渐渐挤压着自己的身体。
她打开衣柜的门,拿出那件在智宇吃奶时期她就很喜欢的紫色棉T恤。由于她在家的时候经常穿那件衣服,所以已经洗得褪了色。她只要觉得身体不舒服,就会找出那件T恤来穿,不管洗了多少次,还是能闻到上面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奶味儿和婴儿的气息。但这次却丝毫没有效果,胸痛反倒越来越严重了。她感到呼气困难,只能不停地做着深呼吸。
她斜坐在沙发上,试图盯着转动的秒针来稳定呼吸。但这也不过是徒劳,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仿佛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瞬间。这种对于痛苦的确信似乎存在已久,它就像等待着时机一样在此刻显现在了她的面前。
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再也无法忍受了。
再也过不下去了。
不想再过下去了。
她再次环视房间里的物品,那些东西都不是她的,正如她的人生也不属于她自己一样。
那个春天的午后,当她站在地铁站台误以为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时,当体内不断流出的鲜血证明着死亡正在逼近时,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她知道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现在不过跟幽灵一样,孤独的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戏。死神站在她身旁,那张脸竟然跟时隔多年再次重逢的亲戚一样熟悉。
她浑身颤抖,打寒战似的站了起来,然后朝放有玩具的房间走去。她摘下上个礼拜每天晚上跟智宇一起组装的吊饰,解开绑在上面的绳子。因为绑得很紧,指尖略感疼痛,但她还是忍耐着解到了最后一个死结。她把装饰用的星星彩纸和透明纸一张一张整齐地收好放进了篮子里,然后把解下来的绳子卷成一团揣进了裤兜。
她赤脚穿上凉鞋,推开笨重的玄关门走了出去,沿着五楼的楼梯一直走到外面。此时的天还没亮,只见四周的高楼公寓只有两户人家亮了灯。她一直走,穿过社区后门来到后山,然后一直朝阴暗、狭窄的山路走去。
黎明破晓前的黑暗把后山衬托得比以往更加幽深。这个时间,就连那些平日起早上山打泉水的老人都还没有起床。她垂着头,一边走一边用手擦拭着不知是被汗水还是眼泪润湿的脸。她感受到了一股仿佛要吞噬掉自己的痛苦和剧烈的恐惧,以及从痛苦与恐惧中渗透出的、匪夷所思的宁静。
时间没有停止。
她回到椅子上,打开了最后一个保鲜盒。她抓起英惠硬邦邦的手,让她触摸李子光滑的果皮,然后把那骨瘦如柴的手指圈起来,让她握住一颗李子。
她没有忘记英惠也很喜欢吃李子。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英惠把整颗李子含在嘴里转来转去,说自己很喜欢李子的触感。但此时的英惠丝毫没有反应,她察觉到英惠的指甲已经薄得和纸一样了。
“英惠啊。”
她干涩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病房里。没有任何回应。她把脸凑近英惠的脸,就在那一刹那,英惠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英惠啊。”
她盯着英惠空洞的瞳孔,但黑色的瞳孔上只映出了自己的脸。一时间的失望使她彻底泄了气。
“……你疯了吗?你真的疯了吗?”
她终于说出了过去几年来自己始终不愿相信的问题。
“……你真的疯了吗?”
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她慢慢地退回到椅子上。病房里一片寂静,连呼吸的声音也听不到,她的耳朵仿佛被吸满了水的棉花塞住了一样。
“也许……”
她打破沉默,喃喃道:
“……比想象中简单。”
她迟疑片刻,欲言又止。
“她疯了,我的意思是……”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把食指放在了英惠的人中上,微弱且温暖的鼻息有规律地触动着她的手指。她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当下她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失眠,正是英惠在很早以前所经历的一个阶段。难道说,英惠已经步入了下一个阶段?所以她才会在某一个瞬间,彻底放弃了求生的欲望?在过去失眠的三个月里,她总是胡思乱想,假如不是智宇,不是孩子赋予自己的责任,也许自己也会放弃的。
唯有开怀大笑可以奇迹般地止住痛苦。儿子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都会逗笑她,也会让她突然愣住。有时,她不敢相信自己在笑,所以会故意笑得更大声。每当这时,她发出的笑声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更接近于混乱。但智宇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
“这样?这样做妈妈会笑吗?”
只要看到她笑,智宇便会一再重复刚才的动作。比如:噘起小嘴,把手放在额头上比作犄角;故意摔倒;把脸夹在两条腿之间,用滑稽的语调叫喊“妈妈,妈妈”。她笑得越大声,孩子的动作越是夸张,最后还会把全部好笑的动作都重复一遍。面对孩子的这种努力,她感到很内疚。智宇不会知道妈妈的笑声最后变成了哽咽。
笑到最后,她突然觉得活着是一件很令人诧异的事。人不管经历了什么,哪怕是再惨不忍睹的事,也还是会照样活下去,有时还能畅怀大笑。每当想到或许他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时,早已遗忘的怜悯之情便会像睡意一样无声地来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