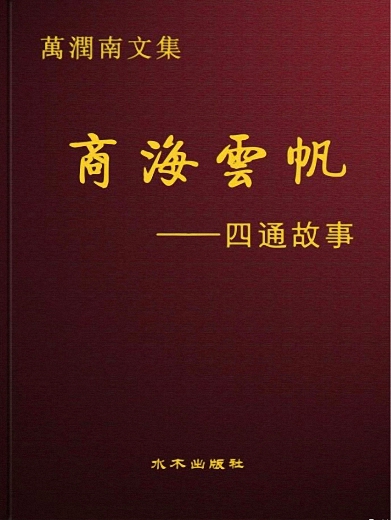第七章 逆境崛起
(45)张旋龙
通过1985年的“清理整顿”,我们经受住了严苛的考验。四通在人们眼中,成为一块“捶不扁、炒不爆、砸不碎、煮不透、响当当”的大石头。从此,我们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发展的势头像脱缰的野马,想收都收不住了。当年,四通完成的销售额是3100万元;1986年,超过了1亿元;1987年,3.3亿元;1988年,超过了10亿元……年均增长300%。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们起家时只有四季青乡的2万元人民币,怎么能做到如此大的销售额?我曾总结过:做生意,要善用OPM——Other People’s Money:一是银行的钱;二是客户的钱;三是供货商的钱。
首先是银行贷款。全世界的银行,都有一个通病——嫌贫爱富。他们奉行的是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多多的给;没有的,连他最后的一分钱都要夺走。”四通在连续四个月还贷1500万元之后,在银行界被传为一个神话。工商行、农行、中行纷纷要求我们去开户,还在屁股后面追着要给条件优惠的贷款。最后,这阵势成了我们要谁的贷款,反倒是给了谁面子。1986年5月,在调查组撤走六个月后,我们把公司的注册资金从二万元变更为一亿元人民币。两年的时间,注册资金提高了五千倍,这就是四通故事。
按照国家的信贷政策,我们的贷款余额可以到2亿元人民币。不管其他银行的贷款条件多优惠,我们始终在海淀信用社保持2000万元左右的贷款余额,尽管他们的利率高。这是为了报恩,说明我们不忘本。
银行对我们的信心,还来源于对四通超一流行销能力的叹服。有一天,海淀信用社的老祁来电话,说有家公司从他们那里贷款100万元,进了一批电脑却卖不出去,贷款到期还不了。现在,信用社派人去封了这家公司的仓库。老祁问我能不能帮个忙。
我把这件事交代给崔铭山。小崔拿起电话,联系了几个客户。当天客户就把电脑从对方公司的仓库直接拉走了。老祁回笼了100万元贷款,四通赚到了销售利润。这件事让老祁激动得逢人便夸:“四通都是神人哪,马路上的土疙瘩,都能卖出黄金价。”老祁说错了,这些电脑,本来就是金疙瘩,是因为不会卖,所以才变成了土疙瘩。
二是客户的钱,就是让客户先付钱,我们后给货。有人会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有,而且让四通碰上了。是政府愚蠢的预算核定办法,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机会。国家单位每年年初要报预算,在核定时要参考上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如果上一年度的钱没有花完,本年度的申请就要打折扣。所以,这些国家单位每到年底都要突击花钱。花钱要有去处,四通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四通的货供不应求,没关系,他们会把钱先汇过来,只要我们给他们开一张往来款收据,货可以年后慢慢给。销售完成之后再开正式发票。这就方便了他们在第二年争取到更多的预算。
方便了顾客,更方便了我们自己。这实际上是帮助四通得到了一大笔零利率的短期融资。每年年底,仅这一部分,估计就能到账数千万。
所以我在前面说:“到年底,四通账面上已经相当宽裕,我们非常从容地还了新兴公司330万元。”
三是供货商的钱,就是先拿货,后给钱。这样的供货商,也让四通碰上了,他就是香港金山电脑公司的张旋龙。张后来被誉为中关村最成功的商人。他不仅身段柔软,而且独具慧眼:一是慧眼识四通;二是慧眼识裘伯君;三是慧眼识方正。
1984年11月,张旋龙一脚踏进中关村的时候,四通才刚刚创办六个月,只有十几个人,但张旋龙认定四通是当时最好的公司。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段往事:“四通人很努力,因为我过去主要和国营单位谈生意,所以,能切身感受到四通人和国营单位的人完全不一样。”出于对四通人的欣赏,张旋龙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让四通代销他们组装的金山电脑,机器卖完了,再收款。代销在今天是习以为常的商业行为,但在当时,作出这个决定却要冒相当的风险。“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像四通这种个体户,谁都害怕。我跟国营单位做生意,都是要先开信用证的。为这,万润南老记我这个情。”
-1-600x636.jpg)
是的,我一直记他这份情。后来,我们和张旋龙在天津开发区成立了合资企业,四通派了一位超级战将刘勇在天津坐镇。据说,这一部分在四通普遍萧条之后还一枝独秀。
1989年我离开四通,他真心感到惋惜。若干年之后,我们还有过一面之缘。记得是在纽约法拉盛,一大早,我到喜来登饭店旁边的一家“人人小吃”去吃早点,那里的油条炸得又大又松又脆,那里的豆浆又浓又香又甜。我刚坐下,边上马上有一位客人也同步坐下。我转过头,他也同步转过头,几乎同时:
“啊,万总!”
“啊,旋龙!”
当时,他已经是方正集团的总裁,但他依然是谦和有礼,身段柔软,说话贴心得体。当年我在四通,经常举他为例,要求销售人员以他为榜样,学习他那种柔软的身段。一般人,可能学得了他的身段,却学不到他的眼光。他识人、用人的眼光,非常人所能及。
很幸运,四通初创时,就遇到了张旋龙这样的合作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