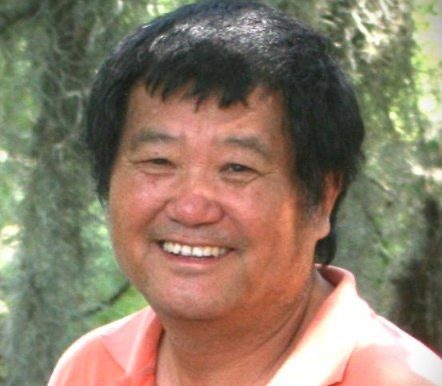前记﹕
91年﹐我去波兰﹐途经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近两星期﹐结识了柯洛别夫和娜佳–两个俄国社会变革中的小人物。以后的年月中﹐我常常想起他们﹐甚至还回俄国寻找过他们。但小人物的消失像他们的存在一样﹐无声无息。我知道柯洛别夫是一定不在了﹐娜佳流落到何处﹐只有上帝才知道 ﹐而我清楚﹐在哪儿她的处境都一定不好。世界变来变去﹐但有些事情千古长存﹐只是那不是什么业绩﹐而是人们周而复始的不幸。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有激情。一晃﹐文章还未曾见光﹐已经过了十几年。年青时绝想不到﹐生命竟是这样卑微易逝。我们这一生经历的都是大事﹐由中国到东欧变革﹐到纽约911﹑伊战﹐就是以后﹐也还有各种大事在等待在排队。可我渐渐明白﹐那些大事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果再一场飓风中﹐你能看清那旋转的微粒﹐那是好目光。
2005年9月1日于伊萨卡
1
走前朋友给了我柯洛别夫的地址﹐嘱我去看他。他是汉学家﹐五十年代到过中国﹐翻译过艾青的作品﹐也翻译中国的古诗。他在中国比在苏联更有名﹐长期在莫斯科电台工作﹐撰写对华广播稿﹐中国的俄语界都知道他。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汉语说得不好﹐我觉得奇怪。在他约定的地点﹐我等了一个小时﹐他没来。再打电话﹐方知错了地方﹐莫斯科地铁有一站叫“飞机场”﹐是二战旧址﹐但我则去了莫斯科飞机场。
下午﹐他来旅馆看我。柯洛别夫﹐一位瘦小的老人﹐戴着旧式礼帽﹐脸上的皱纹很重﹐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镜片后面的眼神有些茫然。他不谙世事﹐衣着随便﹐像世纪初的诗人─他的确是一个诗人。旅馆不方便﹐于是我们去他那里。
柯洛别夫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按照苏联的习惯﹐离婚时丈夫把房子留给妻子。柯洛别夫现在孤身和另外两个独身女人合住一套房子﹐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女工。三个人﹐三个家庭﹐每人一间房间﹐过厅收拾得很干净﹐柯洛别夫的房间则不太整洁。一张单人床﹐两张长沙发﹐一个柜子﹐一架旧钢琴﹐一个书架─不多的书籍﹐中间有一张方木桌。房间缺少收拾﹐陈旧而冷落﹐想是主人孤身生活很久了。
我来﹐他很高兴﹐他三十年没说汉语了﹐况且他很孤独。他过了六十岁﹐已经退休﹐而现在他不仅孤独且而贫穷。他算作家﹐没有著作就没有收入﹐而现在苏联出版社没钱出书﹐他的几部书稿都压在那里﹐其中有一部是《红楼梦》的译诗﹐他大约断断续续花了十年的时间。他说﹕“一平同志﹐你应该看看苏联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没有钱﹐不能工作﹐他们的书不能出版”。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和他们差不多。
我带来几瓶酒和一些食品﹐他快乐起来﹕“一平同志﹐我们吃一点吧﹐喝一点吧。祝贺中国的节日。”再有二﹑三天就是中国的国庆日﹐我们边喝边谈﹐他的汉语恢复得很快﹐忘失的发音﹐陆续记忆起来。他的汉语的确很好。当然﹐谈话中还要不断停下来﹐我给他提示。他年轻时写诗﹐后来学汉语﹐见到了戈宝权﹐戈宝权鼓励他翻译中国文学﹐于是他搞上了汉学。五十年代他在中国住了四年﹐一个女儿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翻出她的照片─海岸上一个著泳装﹐晒日光的中年女人。柯洛别夫曾任俄中高级翻译﹐参加过中苏重要会谈﹐认识周恩来﹐他很有兴致地提起周和他的谈话﹕“柯洛别夫同志﹐你说… …”﹐他骄傲﹐他喜欢在中国那段时间的生活﹐那是他一生最好时期。他在中国爱过一个女人﹐他们相爱﹐“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他参加了她的婚礼﹐她哭了﹐他也哭了。几十年﹐他一直想着她﹐打听她。柯洛别夫热爱艾青﹐说他是伟大的诗人。去年中国召开艾青作品讨论会﹐艾青邀请他去参加﹐但是他买不到去中国的火车票﹐车票都被被票贩子控制着﹐他又悲哀又气愤。他为我背诵了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反右中国批判艾青﹐他听到广播的第二天﹐便愤愤回国了。他愤恨毛﹐说﹕“毛泽东有什么权力批判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不喜欢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写文章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他说﹕“中国都知道﹐我﹐柯洛别夫反对毛泽东”。今年初(91年)﹐新华社的一个官员─他的老朋友─到苏联﹐邀请他到中国去工作﹐他非常高兴﹐一直盼著。但他又很担心﹐因为他批判过毛和中国﹐中国可能不欢迎他。我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中国在变化﹐他说﹕“是过去的事”。他像有过失的孩子﹐仍不放心。
柯洛别夫热爱中国文化﹐总是说中国的“礼貌”﹐“苏联人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礼貌﹐他们不知道”。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带来的食品﹐这使他想起中国的美食﹐他邀请邻居过来品尝﹐给她们讲中国。我带来的一瓶酒﹐包装盒画的是大观园。我随手想把它扔掉﹐他拦住了﹐欣赏了半天﹐“啊﹐多美啊﹗”他把它恭正地摆在钢琴上。柯洛别夫羡慕中国的改革﹐“中国什么东西都有”。他认为现在苏联搞得一塌糊涂。“一平同志﹐你到苏联有什么感想﹖”“我是坐火车过来的﹐我看到了俄国的辽阔和富饶。”“不﹐我不想听俄国辽阔富饶。你应该看一看现在苏联的可怕生活。没有肉﹐没有黄油﹐没有伏特加﹐什么都没有。现在俄罗斯没有酸黄瓜﹐这不可笑吗﹖”“柯洛别夫先生… …”﹐“不﹐不要称先生﹐我喜欢‘同志’和‘朋友’。我们称朋友好吗﹖”“一平朋友… …”。他热烈地拥抱我﹐我感到他瘦小个子里燃透的热情﹐酒热熏暖了房间﹐他成了少年。
他也谈到了﹐五十年代他在中国看到的缺少衣食的人们﹐在北京﹑上海﹑南京﹐他不止一次遭遇围追他乞讨的孩子们。为什么﹖他现在还在为此难过﹐他知道中国﹐中国曾经饿死过许多人。他谈到苏联夏季的政变﹐“啊﹐他们没成功﹐如果他们成功… …”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厌恶。
他又高兴又快活﹐喝得很多。他有些摇晃了﹐说话的音节开始拖长﹐苍老的脸在灯光下泛出红色﹐额前垂下来的花发像酒精升腾的诗意。他不断拥抱我﹐讲述伟大的中国。“我要去中国”﹐“我要到中国去了”﹐“我的朋友﹐请你帮助我”。快十一点了﹐我要回旅馆﹐他一定要送我﹐我再三推辞﹐没用。“一平同志﹐你不知道莫斯科的阿飞﹐很多﹐我一定要送你回去﹐你是我的中国朋友”。我无法拒绝﹐他不允许我说话﹐再说﹐就要打架了。他摇晃着穿上衣服﹐换上鞋。在深夜的街道﹐就著朦胧的灯色和天上的星辰﹐我们像少年人那样搭著肩膀哼唱着﹐趟着落叶﹐迎着雾水。没有年龄之别﹐国界之别﹐我们是诗人兄弟。穿过大街﹐乘上地铁﹐路人奇怪地瞧着我们。他一直把我送到车尔尼雪夫大街。我又去回送他﹐看他瘦瘦的﹐一个人走入茫茫夜色。
2
次日下午﹐我再去看他。屋里混乱﹐地上到处是烟蒂。他没穿鞋﹐两只脚﹐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露著后脚跟﹐暗红色的领带耷在胸前晃来晃去。“一平同志﹐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吧﹐为中国的节日”。昨夜他送我回来﹐没睡﹐一直在喝﹐两瓶白酒﹐一瓶红酒精光。他的手插在裤袋里﹐流浪汉般在屋里晃来晃去。我收拾屋子﹐他制止了﹐拿起小条帚﹐趴在地上扫地上的烟头和杂物。他忽然大笑起来﹐跪在地上昂着头望着我﹐手像爪子一样把脏物抓进簸箕里。我理解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我在他的笑声和发狂的灰蓝色眼睛里﹐看到了俄罗斯的血液。
他熟悉俄罗斯文学﹐喜欢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为我朗诵俄国诗﹐硬朗光丽﹑起伏流动的俄语音节﹐有寒冬大理石的质感。一会儿﹐他打开旧钢琴﹐双手像兽爪一样在琴键上猛砸下去﹐但忽然之间─他的手指又像水波般柔软﹐优美地在琴盘上弹动﹐乐声像溪水流过卵石和落叶。啊﹐俄罗斯的残暴和优美﹐在他身上体现得这样丰富和完整。他大笑﹐又变得平静﹐像一束蓝色燃烧的酒精─蓝色燃烧的灵魂﹐我理解了俄罗斯的诗歌精神﹐从普希金﹐到勃洛克﹑曼斯杰塔姆﹑茨维塔耶娃。
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是知识分子﹐他不喜欢政治﹐“我无党无派﹐最好”﹐他很骄傲他作为一个纯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的钢琴台上有一张苏联三十年代的报纸﹐报纸已经黄了﹐第一版有一幅公审合的照片﹐人们在声讨一个“罪犯”。我清楚那个可怕的恐怖时代﹐我奇怪﹐这张报纸怎么会保存下来﹐怎么会放在这里﹖我问他﹐他说﹕“那是可怕的﹐可怕的。你不懂。”他没有说得更多﹐那个时候他大约只有十几岁﹐我觉得他痛恨过去的制度。记得昨天我们在地铁里﹐经过一座雕像﹐从神态上看像革命英雄﹐经过那里﹐柯洛别夫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眼角充满轻蔑。而当我提到“共产党”的时候﹐他又张著嘴巴﹐怀有恐惧﹐仿彿身边就有克格勃﹐他尽量避开这个话题。苏联权力给人民留下的精神阴影是漫长的。
柯洛别夫的汉语越来越流利﹐几天的功夫﹐我们已经能随兴交谈。一次我们谈到俄国文学﹐我问他是否喜欢契柯夫。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但以后就不喜欢了。“为什么﹖”“他拿人开玩笑﹐那个套子里的人﹐是个可怜的人。他是一个人﹐一个孤立的人﹐为什么拿他开玩笑﹖”我是第一次听到人这样谈论契柯夫。柯洛别夫的批评有些严厉﹐但他的判断准确﹐契柯夫的嘲讽有市民气﹐他观看小人物的悲剧﹐有时像看杂耍﹐这是契柯夫的渺小之处﹐他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类那样广博的爱和怜悯。但是契柯夫依然是伟大的﹐他的作品贯穿着人道精神。在柯洛别夫谈话中﹐我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精神﹐这就是道义﹑人性﹑灵魂﹑怜悯﹑爱﹑罪恶﹑忏悔… …生活的真理。在今天后现代风潮中﹐俄国还有人还保存着古老精神和理想﹐像现代城市中尊严的堂﹐这使我感动。当然﹐这只是我在柯洛别夫的身上看到的﹐我不知道﹐在俄国的变化和现代的冲击中﹐这座教堂会不会塌毁。我也不知道俄国年轻一代的文学家﹐他们的想法和道路。也许﹐文学的的确确应该和过去告别﹐也许我们的面前的的确确是另一番世界。但是如果文学中没有人性﹑没有爱﹑没有生活真理的发问与追寻﹑没有道义﹑没有痛苦﹑没有尊严﹑没有同情﹑理想﹐没有灵魂﹐那么我将放弃它。在现代都市任何一个街头﹐我都能找到消闲和娱乐﹐无论是脱衣舞或时装表演都比文字更娱悦。
有时﹐我和柯洛别夫一起出去﹐小雨时停时落﹐秋日萧瑟﹐略有寒意﹐零乱的风卷著河岸和树木。道路正翻修﹐我们踏着泥泽和废石﹐三﹑两的乌鸦落至树脚﹐飞过长椅﹐湿漉漉的桦树叶翻卷著﹐片片飘落街心。柯洛别夫穿着一件褐色的短大衣﹐旧礼帽遮住目光﹐他使我想到俄国旧时代的人物。
一天﹐他带我到俄国旧街去喝啤酒。他告诉我过去这是俄国贵族的住宅区﹐我有些失望﹐没有感到古老的气氛﹐倒是有些破旧和混乱。沿街商店破落﹐有的地段已被外国人抢占﹐围着围挡在翻修﹐巨大的广告格外醒目。他告诉我他过去工作过的出版社和朋友们的住所﹐特意指给我一家饭店﹐过去苏联作家经常光顾这里﹐相聚﹑喝酒﹑闲谈﹐类似于作家沙龙。他很留恋过去的日子。我们在酒馆等了好一会儿﹐它才开门﹐喝酒的人很多﹐需要排队。不大的屋子﹐两张长条木桌﹐没有座位。十几个酒杯﹐人们轮流等候﹐酒馆里一股臭咸鱼的味道─俄国人喝啤酒喜欢吃咸鱼。我们等了又等﹐柯洛别夫很有耐心﹐但我们还是走了﹐因为等不到杯子。离开时﹐我挺庆幸﹐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那一长串人用过的酒杯﹔而他望着黄澄澄冒着泡沫的啤酒﹐颇有遗憾。
3
柯洛别夫的生活一塌糊涂﹐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喝酒﹐他总是醉熏熏的﹐神情恍惚。他不正经睡觉﹐也不正经吃饭﹐床上﹑地板四处是烟头的烙痕﹐我担心有一天会失火。柯洛别夫对什么都不满意﹐不喜欢过去﹐但也不喜欢现在﹔憎恨专制﹐也愤怒俄国的分裂﹑混乱﹑没钱没食品。他说大街上的年青人是阿飞﹐就知道搞姑娘。他指著报纸上的裸体照片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成了这个样子﹐这些人在中国会被处死的”。他的严酷令我惊讶﹐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让我欣赏他画的裸体素描。他不是虚伪﹐只是矛盾﹐巨大的俄罗斯精神的混乱与分裂。这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体现得都很充份。有一夜我留住在他那里﹐他的年轻女友娜佳也住下了﹐早上他拉着我﹐掀开娜佳的毯子﹐“啊﹐娜佳﹐让我们看看吧﹐让我们看看吧”。他笑得又狂野﹐又天真﹐他很迷恋娜佳。娜佳不在的时候﹐他沮丧之至﹐“娜佳没有来﹐小妞没有来。”他不说别的﹐只重复这句话﹐带着哭腔。但他有时对娜佳又很粗暴﹐凶狠地骂她﹐把她赶走。在女孩子﹐这一般是不能接受的﹐但过后娜佳又来了﹐彼此仍然亲热﹐像没事一样。
柯洛别夫很同情娜佳。娜佳没有父母﹑亲人﹐没工作﹐在莫斯科也没户口﹐她总是缺少衣服和食物。柯洛别夫说她可怜﹐应该帮助她﹐她在世界上是“一个人”。他讲述了娜佳许多不幸的生活。他待她像父亲﹐但又说救不了她﹐嫌她身上有不好的东西﹐他为之悲哀。娜佳想嫁给他﹐和他一起去中国﹐他犹豫是否该答应。他也是救不了自己的人。他们之间不是爱情﹐我想是一种彼此的怜悯和依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写过这个故事﹐但在真实中﹐他们还有彼此的怨恨和伤害。
柯洛别夫酗酒﹐每天喝醉。走前﹐我给他介绍了个工作﹐在一家中国公司教俄语﹐待遇不错﹐可以使他过上很好的生活。但我懮虑他干不了﹐他失去了正常﹐酒和生活已经毁了他。他整日迷迷昏昏﹐我走的时候﹐他没去送我﹐许是喝醉了。列车开了﹐我还在想着他﹑他和娜佳。他去不了中国了﹐谁也救不了他﹐像他救不了娜佳。我对他们充满怜悯﹐以后我给他写过几封信﹐都没有回信。我很想念他﹐想再去俄国看他。
4
一次我去柯洛别夫家﹐忘了路﹐向人打听路﹐恰好问到她﹐我不并认识她。她看了地址﹐非常兴奋﹐高兴地为我带路。她的身材不错﹐细高﹐走路轻快﹐盘起的头发露出修长的颈子。她穿着旧运动装﹐上衣带有帽兜﹐裤子膝盖处磨得很薄﹐有一点已经破了﹐缀着白钱。她边走边踢路边的积叶﹐有时她走快了﹐便回身等我。她不拘束﹐不停地叙说﹐说得很快﹐而她的俄语我一句不懂﹐可她竟不在意﹐我有点奇怪。她黄色的眼睛目光亲切﹐不大的鼻子﹑嘴角灵巧﹐但有点贫气。她不漂亮﹐但也不难看。她像一个农村丫头﹐大约有二十六﹐七岁。
她一直把我带到柯洛别夫的家中﹐于是我知道她是他的女友。我们拥抱在一起大笑﹐柯洛别夫说过﹐有一个年轻姑娘想嫁给他﹐和他一起去中国﹐没想到就是她。我送给她一个刺绣挎包﹐一件京剧脸谱的圆领衫。她很高兴﹐竟拉开衣拒门做遮挡﹐即时就换上了。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当着陌生男人换内衫呢﹖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跳着拥抱我﹐吻我﹐说着飞快的俄语。她的热情让我动心﹐中国姑娘不这样。她称我“yi”﹐洋腔﹐她反复讲述我们的“奇遇”﹐柯洛别夫像父亲那样微笑。我请他们到饭店去吃饭﹐娜佳垂下了头﹐似乎是落了泪。她和柯洛别夫说话的语调悲哀﹐她悲伤的时候比她快乐的时候要温柔﹐要美﹐让人想到秋日小雨中的桦树﹐难怪有的男人喜爱悲伤的女人。悲伤使人有对美的幻想。柯洛别夫告诉我﹐娜佳不愿去饭店﹐因为她没有好的衣服。我这才感到衣服对女人之重要。娜佳似有歉意﹐手指在膝盖那块破处抚动。我很不安﹐仿彿不该提这个建议。的确﹐男人应该照顾好女人﹐使她们安定﹐温暖﹐有好的衣着和家庭。我们都不再说话﹐娜佳默默地帮助柯洛别夫收拾房间。
柯洛别夫告诉我﹕娜佳有芬兰﹑捷克﹑俄罗斯三种血统﹐但却没有一个亲人﹐她的身份证也丢了。“你知道﹐在苏联没有身份证多么可怕”。“她是‘黑人’﹐找不到工作。她有时到莫斯科郊区帮农民捡土豆﹐有时也给画家当模特。她常常挨饿。”娜佳是一位少有的姑娘﹐现在的姑娘喝酒﹑抽烟﹑要漂亮衣服。娜佳不喝酒﹑不抽烟﹑不化妆﹐甚至不吃肉﹐她去教堂。娜佳总是祈祷﹐给柯洛别夫讲上帝﹐这让柯洛别夫厌烦﹐他讨厌上帝﹐他说她脑子有毛病。娜佳脸色不健康﹐苍白﹐她有受难的气质。哪里都有不幸的人﹐不幸的命运﹐被生活和人群所抛弃。柯洛别夫不满意她去教堂﹐但是不去教堂她去哪儿﹖她依靠什么活下去﹖我为娜佳难过。
5
下午﹐我和娜佳出去买食物。走前她找隔壁老太太要了一点白面当做脸粉﹐对着镜子梳饰。哦﹐俄罗斯的贫穷和美。她高兴和我出去﹐带我乘了很远的地铁。我们去了阿尔特街﹐那里的食品要多一些。路上我给她买了束鲜花﹐她一直握在手里﹐不断低头闻嗅﹐很珍爱。
莫斯科大多数商店没东西卖﹐有东西的地方都排长队﹐有时要排几个小时。在一家食品店﹐娜佳很耐心地排队﹐能像女主人拿着钱大方地排队买东西﹐她很骄傲。我没有耐心﹐不断地跑出去逛街。我隔会儿回来看看她﹐她微笑地向我示意﹕“队很快”。最终我们买了蛋糕﹑点心﹑葡萄﹑李子﹐黄瓜─娜佳没有买肉食。
回到柯洛别夫的家﹐娜佳很激动﹐给柯洛别夫看她的鲜花。她说得很多﹐十分兴奋﹐柯洛别夫告诉我﹐娜佳说从来没有人给她送过鲜花﹐她一直是一个灰姑娘。娜佳一年多没吃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天像过节一样。我没想到﹐这样一点事情给她带来这么多快乐﹐这么多感激﹐我颇不安﹐像有欠于她。晚饭大家吃得很高兴﹐但过后却很不愉快。娜佳说男人应该有钱﹐应该使女人快活﹐这些话让柯洛别夫不快﹐伤了他的自尊。他开始骂娜佳﹐责她不该让他的中国朋友买这买那﹐骂她是下贱。我很尴尬﹐不知该怎样劝解。一个美金换四十个卢布﹐其实这是很少的一点钱。娜佳哭了﹐说再也不做柯洛别夫的朋友。但过会儿﹐二人又和好了﹐“父亲”不断向“女儿”道歉。大家又开始说笑。
太晚了﹐于是我和娜佳都留住在他那里。两张沙发﹐一张床﹐三人各占一端。熄了灯﹐我合衣躺下﹐想将就几小时吧。而娜佳站在她的沙发上﹐窗前﹐脱去长裤和外衣﹐外面的月光透过婆娑的扬树﹐照进窗子﹐她长长的双腿和光滑的脖颈﹐笼上一层淡淡的月色。她挺起的乳房罩着薄薄的背心﹐短裤在大腿根部投下一条暗影。她钻进毯子﹐很快地睡了。和一个年轻女人睡在同一房间﹐很难入睡。很多作家描写过夜晚的女人﹐我尤其记得托尔斯泰记述娜塔沙和她的女友夜晚俯窗谈论爱情的那一情节﹐她们的下一层是留宿的保尔康斯基。当时他也难以入睡。柯洛别夫没睡﹐他不断抽烟﹐自言自语﹐“上帝帮助我去中国”﹑“去中国”﹐在他含糊嘀咕的俄语中夹杂着汉语。我想他大概每晚醉后﹐都会折磨自己。
早上﹐娜佳出去﹐拿着她昨天留下的一份食品﹐想是去见朋友。她告诉我们两个小时回来﹐但是到了晚上也没见到她。柯洛别夫和我都有些烦躁﹐他说娜佳常常说谎。他说的可能是真﹐但我不愿这样想。
6
我和娜佳一起出去过几次﹐买东西﹐发电报﹐去红场。在莫斯科街头常有乞丐﹐每次从他们面前经过﹐娜佳都从我这拿几个卢布给他们。在一家商店门口﹐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衣着破旧﹐旁边有一块纸牌﹐写着乞讨原由﹐她大概是孤儿﹐娜佳在她的纸盒里放了五个卢布﹐一个人低着头匆匆地向前走去。待我赶上她﹐她的眼睛有些红﹐她刚才落泪了﹐我想小女孩大概和她有类似的身世。人的同情大致都和自己有关﹐但人能有同情这也就是善。在我们这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嘻皮﹑诅咒﹑破坏成为时尚﹐善﹑同情﹐美德成为可笑的字眼﹐其近乎傻瓜的行径﹐对此种种能有什么言诉﹖我默默看看娜佳﹐感到酸楚。街上行人匆匆。
娜佳的生活的确很糟﹐一直穷困﹐一支冰激凌﹐一杯可乐﹐都会使她快乐满足。她像小女孩一样﹐会站一个小时的长队去买两支冰激凌﹐她对那淡绿﹑粉红﹐乳黄的冰激凌球怀有贪婪的渴望。一日﹐从红场回来﹐天已经黑了﹐她特意带我去普希金广场﹐那是美国在俄国的第一家麦当劳店。汉堡包﹑可乐﹑冰激凌﹑炸薯条都是非常简单的食品﹐但对莫斯科人来说却是时髦和侈奢。几百平方米的餐厅﹐人挤得满满的﹐门外有数千人排队﹐有警察看守。每隔十几分钟放一批人﹐好在还是快餐厅﹐从队尾到入口﹐要站近三个小时。莫斯科人很有秩序﹐没有人拥挤﹐这让我尊重。但是花三个小时﹐吃个汉堡包﹐买杯可乐﹐难能接受。莫斯科人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况且这是高价餐厅﹐一份套餐大概需要他们一星期的工资。的确是太缺乏了﹐缺乏才使人们的要求才这样低廉。
娜佳从最后一个排起﹐望着前面曲折的队伍﹐我从心底发愁﹐暗示她我们该离开。娜佳固执地翻著字典告诉我“很快”“很快”﹐我几乎动怒﹐但还是没有。娜佳很有耐心﹐站队像她的生活。我坐下﹐站起来﹐又坐下… …到邻处去逛街… …。终于入了门﹐总算感到轻松。娜佳挤上柜台﹐虽然不是自己的钱﹐她算得还是很仔细﹐和售货员小姐计较了几番。我在旁边颇难为情。
我们端著托盘几乎转了二十分钟﹐终于找到了座位。娜佳的主食吃得不多﹐一份汉堡包─她不吃肉﹐夹的奶酪﹐一份薯条﹐但她的冷饮吓人﹐三大杯可乐﹐一大杯冰激凌﹐我担心她的胃受不了。最后带给柯洛别夫的那一份冷饮﹐她也毫不犹豫地喝掉了。娜佳举著美国可口可乐的纸杯﹐不断挑起大姆指﹐这让我不快。但我又感到自责﹐怎么能责怪她呢﹖难道我会责怪一个法国贵族﹐挑起姆指赞赏百年的陈酿吗﹖娜佳无非是贫困﹐由高度欠缺而导致的对生活微小需求的过度渴望。这是卑微还是悲哀﹖
7
娜佳和柯洛别夫曾热烈地讨论﹐我走时他们怎么去送我。他们说﹐一定要去送我﹐要看着我上车才好。但我走的前两天﹐娜佳就不见了踪影﹐不知去向。柯洛别夫电话中说﹕他把她赶走了﹐接着又哭丧著说﹕“娜佳没有来”。
我走的时候没有见到柯洛别夫﹐也没见到娜佳﹐我给他们准备的一些衣物和一笔钱也无法交予他们。他们没有去送我﹐我不责怪。在这个社会中﹐他们都属于不能自存﹐被生活所抛弃的人。人类的生活中﹐总是要有些人被淘汰﹐以保证人类生竞争﹔这和动物世界中﹐弱质生命将被淘汰的道理是一样的。上帝也好﹐道德也好﹐都无法掩饰这一生存的“大真理”。适者生存﹐它像铁一样坚定残酷。
列车驶出了莫斯科﹐进入了黄昏辽阔的旷野。别了﹐莫斯科﹔别了柯洛别夫﹔别了﹐娜佳… …。我能够想到他们的结局﹐我想到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救不了谁﹐于是《圣经》说﹕“人只有自己拯救自己”。我得到赦免﹐人不仅有怜悯。列车向前疾驶﹐我的头探出车窗﹐我远远地望到列车拖着长尾划过黄昏的原野。
首发《今天》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