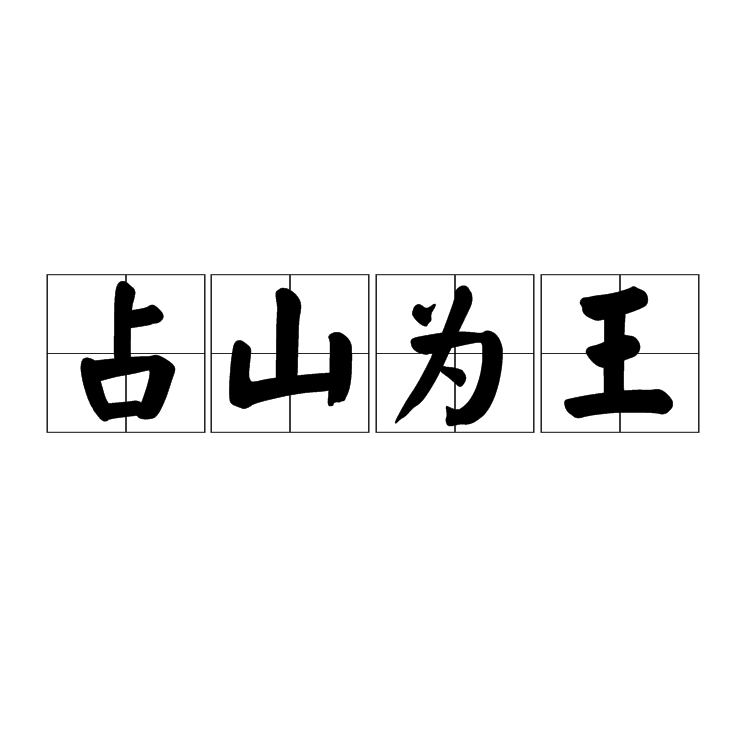一群男孩子,围着一个土堆,玩占山为王的游戏。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谁力气大,谁能把站在山头的那个人拉下来或推下去,谁就是山大王。山下边的人,个个都想当山大王,于是一波接一波的“冲顶”围着土堆就展开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新上任的“王”还没站稳脚跟,就被另一位后来者取而代之了。这群男孩子个个玩得兴奋异常。
看这群孩子玩了一会,我忽然隐约有种发现:这游戏不就是我们成人社会权力转换和官民关系的一个缩影吗? 在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成人社会流行的岂不就是这群毛头小子玩的把戏?然而这套把戏在孩子们那里是娱乐,在成人世界却是没完没了充满血腥的权力之争和胜者对败者的公然压迫。
这游戏的要害是:
一,它预设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结构,它提供的是一个不平等的舞台,它把好端端的“人”撕裂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做统治者,一部分人做被统治者,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尽情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一部分人老老实实给人当奴隶,任人欺凌任人摆布,过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
二,公共权力彻头彻尾私有化家族化了,公共权力完全掌握在了一小撮“强人”手中,甚至完全落在了某一个家族的手中,掌权者视天下为自家之私产,视百姓为自家之奴仆,公共利益公共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甚至完全消失了。
三,最高权力的获得和转移完全凭借“暴力”和“阴谋”,凭借充满血腥的“你死我活”的争斗来实现,谁有实力,谁心狠手毒,谁杀人不眨眼,谁能搞阴谋诡计,谁就有望成为统治者,每一次“改朝换代”往往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人民横尸遍野的悲剧。
四,在这一游戏中,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你要么是治人者,要么是被治者,要么为主,要么为奴,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作为一个人,谁又愿意过任人欺凌任人摆布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日子呢?谁又愿意处在一个不平等结构的最下层呢?既然社会给人搭建的是一个非君即臣的平台,既然上天给人安排的是一种非主即奴的关系,那么人们自然而然选择的就是“往上走”,就是想办法做“人上人”。于是来自被统治者、来自“臣奴”的反叛(“冲顶”)便成了历史的必然和常态。而坐上王位的人,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为了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则发明了种种残暴狠毒阴险血腥的手段来对付下面的“不安分”和“图谋不轨行为”,极端的做法甚至把治下当战俘,当牲畜对待:想怎么使唤怎么使唤,想怎么虐待怎么虐待,甚至想杀就杀,毫不顾惜。
难怪我们中国人缺少平等观念;难怪有人指责中国人,说中国人与人交往,要么雄赳赳气昂昂一副统治者嘴脸,要么缩头缩脚战战兢兢一身奴才气;要么傲慢地两眼向上目中无人,要么自卑地两眼向下不敢正眼看人,而就是不懂也不会与人平等交往平等相处。中国人怎么可能懂得平等呢?中国人从哪里去了解平等学习平等?几千年了,中国人玩的游戏里自始至终就没有半点平等的影儿,中国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又有谁见过平等,又有谁被人平等地对待过?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人一开始作为政治动物出现在华夏大地,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裹挟,渐次分裂为利益完全冲突的两部分,分裂为等级森严、地位悬殊,在享有资源、权利、自由等方面极不平等的两部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从有了国家的雏形那一天起,就建立在了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要么“主”要么“奴”、要么你压迫我,要么我压迫你这样一个“平台”之上。几千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无不在这一平台摸爬滚打上下沉浮或生或死或荣或辱;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观念、智慧、才华,被这一框架牢牢地给“框”住,走不出半步,结果在上发达的是统治艺术斗争哲学,在下盛行的是逆来顺受奴隶主义。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平等是什么东西;男男女女,所追求的无不是“做人上人”这一终极的人生目标。“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这句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教子格言,从一个侧面生动诠释着中国社会人与人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
今天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野蛮的游戏,非常恶劣的游戏,同时也是内耗非常严重、频频对社会基础造成毁灭性破坏的游戏。想想看,同是万物之灵,同是天之娇子,同是炎黄子孙,却硬要分个你尊我卑你上我下你主我奴两重身份,却硬要取“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压迫你”、“不是你统治我,就是我统治你”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结果呢,统治者每天把心思都用在了怎样管束被统治者,怎样从被统治者身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利润”,怎样防止被统治者“谋反”这样一些事情上了;而被统治者每天本能的想法则是:怎样挣脱统治者的管束,怎样能减轻或暂时逃避一下这种管束,怎样少给上面交点“税”——上上下下,心里面想的全是如何作对如何欺骗如何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 一个社会取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它能“万众一心,劲往一处使”吗?它能“多快好省”健康向上地发展吗?它能不时时被各种矛盾、冲突所困扰,能不经常面临“炸锅”的危机吗?结果是在上在下哪一方也活得不轻松、活得身困体惫心力交瘁,社会也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对抗中大量内耗着自身的能量,使发展呈现出忽上忽下忽进忽退忽冷忽热的态势,使好不容易获得的社会积累常常因底层民众的“一声吼”而灰飞烟灭。
几千年非主即奴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社会动荡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另一方面,这一结构也严重毒化了中国人的心灵,使中国人具有了一种罕见的狡猾和狠毒,使中国人的人性——至少在统治者身上——时常完全丧失或彻底扭曲。
几千年来,也不是没有人站出来对这一“平台”进行质疑;几千年来,这一“框架”也不是没有被推翻过、砸碎过。但推翻砸碎之后,搭建起来的仍是一个君臣结构的框架,主奴关系的平台。昨天的奴隶做了主人,但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的事实没有变;今天的主人大喊“翻身”了,但他的脚下,很快又围满了向他叩头膜拜的奴隶。中国人,时至今日翻来覆去改头换面却万变不离其宗玩的、还是前述那群毛头小子玩的把戏。
当然,延绵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亲民”的甚至“爱民如子”的皇帝,但这些“好皇帝”无论怎样“亲民”、“爱民”,第一,从人格上讲,他们与百姓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从法律上看,他们与百姓的地位就更加不“对称”了。况且他们的“亲”和“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被“亲”被“爱”者必须甘愿做他们的奴仆,做他们的顺民,必须匍匐在他们的脚下,任他们的盘剥、打骂或“恩宠”,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如若谁把“自由”、“尊严”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想在人格、权利等方面与“治人者”讲“平等”,那么对不起,“亲”与“爱”不但要收回,最严厉的惩罚也会接踵而至。
有没有另一种玩法,有没有人人平等的游戏——在这种游戏里,人不再被分为君与臣,主和奴;在这种游戏里,一部分人不再有权支配另一部分人,不再对另一部分人颐指气使随意盘剥打骂欺辱;在这种游戏里,所有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们独立、自尊同时也懂得尊重他人,他们对同类怀有同情同理关爱之心;在这种游戏里,大家遵守同一的规则和法律,无人有权践踏规则,无人有权超越法律的约束——在法律之上另立规章以言代法为所欲为……
以前中国人常讲“天下乌鸦一般黑”,《诗经》上就有“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感叹。现在国门洞开了,我们终于知道另一种游戏是存在的,人与人平等相处的“乐土”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前,沿海地区不断有人冒死偷渡海外,改革开放后,国内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出国潮,这都可看作是国人对这一野蛮游戏的厌恶和唾弃。既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游戏的“荒诞”,这一游戏的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为什么不联合起来,重立游戏规则,废掉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换一种新的玩法新的游戏,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社会框架呢?
这种野蛮的游戏几乎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了“残人”和“萎人”,我们是不是到了彻底改弦易辙重新做人的时候了呢?再继续按这种老旧的方法玩下去,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真是名副其实的野蛮族类了。
我们什么时候结束这野蛮人的游戏?
补白:
写《白鲸》的美国作家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大意是这样的: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残暴的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政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但结果却是,奴隶成了新的主人后,同样暴虐地对待别的奴隶;因为这些新的“统治者”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相处和平等地往来,所以他们也那样做不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实行统治。麦尔维尔写这篇小说的时间大约在150年前。可以想象,他之所以写这样一篇寓言式的小说,说明小说中反映的现象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存在的。斗转星移,150多年后的今天,麦尔维尔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盛开着民主自由的花朵。而那里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巨变”,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人权意识和民主诉求一代比一代清醒和强烈,这种诉求和意识最终导致了旧的游戏旧的规则被彻底禁止和废除了。
我们这里,何时才能发生这样的“历史巨变”呢?
首发2004年《杂文报》
后记:
这篇文章发表后,连同《我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粗浅认识》一并寄给了邵燕祥先生。邵先生看后有个回复,抄录在下面,以致缅怀和纪念:
连晨老弟:你好!
两文拜读,在今之大量报刊杂文中,这是属于思想含量高的一路,难得了。因为这需要相当的功力,认真的学习和思考,需要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当然,不是说,这类文章在形式上也必须正襟危坐。
我在这一个半个月里,记得还看到你一篇文章,是在《南方周末》还是《湘声报》,《同舟共进》,记不清了,当时觉得也不错;但说的是什么,也已记不清。你看,老之已至,忘性日长,不知将伊于胡底也。
你是在山西?你是山西人吗?
再谈,祝夏安
邵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