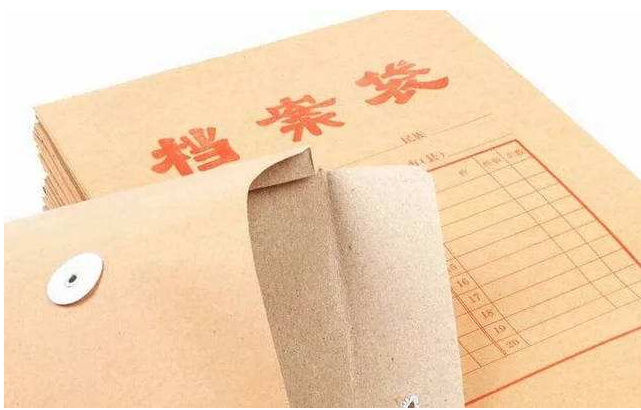中国人大凡从上中学开始,便有一个如影随形的东西伴其一生,这东西就是个人档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档案的意义可能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那些一辈子既不曾“犯事”又不曾做官的人,档案基本是一张“白纸”——可有可无的。
但是一个人要是有一天犯了罪,或是忽然间交了华盖运,要当官了,档案的作用就彰显出来——“犯罪分子”的档案里要是查出曾有“前科”记录,那么这记录将作为他所犯新罪量刑的重要参考(从前这类记录还会作为对“案犯”从重处理的一个依据);要当官的档案里要是有一些诸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记录,那么这类记录则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他迈向仕途闪亮的“绿灯”。
但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事,却叫公众对档案的真实性和作用产生了重重疑虑。
举例来说,有些基层官员劳民伤财作恶多端,在当地早已怨声载道,但却照样官运亨通,挪个地方反而当上了更大的官。这时人们就不得不想:他的那些“劣迹”加“恶迹”,为什么就没有在档案里留上一笔,从而阻止住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再看贪官的情况。从媒体报道我们知道,许多贪官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历史长达3年5年甚至7年8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常有知情人在不停地向上级机关检举揭发他们的犯罪事实。如果这些事实能早一点进入“组织部门”的视野,或贪官们的个人档案,那么他们绝不至于贪到几百万上千万的份上才被“叫停”。这时候“停”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家损失日积月累绝大多数已无可挽回;贪官本人大多也都够上了死罪——想悔也悔之不及了。
要是档案里能如实地记下他们刚“出轨”阶段相对比较小的劣迹,从而使组织上能及时掌握他们的犯罪动向,提前采取行动对他们的犯罪行为给以干预,国家损失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有多少“党的好干部”今天仍可以继续在革命的岗位上为党工作,为国家尽力,而不至于早早步上黄泉路啊!
可是现如今的个人档案似乎已丧失了它应有的功能和严肃性。尤其是那些在仕途上一路走红的腐败分子的档案,我猜测里面是只记成绩不记失误,只记亮点不记污点,更不会有违法乱纪的记录(否则他们一个个何以能边腐败边高升呢?)。这一现象显然让更多心术不正的人钻了空子,也使客观公正地考察干部的一项重要依据丧失了可靠性。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看到的一则紫色幽默:
一名学生刚上大一,就被发现偷东西。该生承认自己从中学就开始偷,而且被学校发现过。但翻阅他的中学档案,没有一个字记录。高校问到他的母校,中学说,档案上写啦,你们没有注意——有一句说“该生手脚比较利索”(见2001年10月9日《中国青年报》5版)。
该报说,这是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忠民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
如此记录一个人的偷盗行为,简直匪夷所思。档案失真,看来已不是个别现象。
贪官们的档案里要是都如上面这个故事里的手法记录他们的“劣迹”,考察干部的人事部门就是个个练就一双金睛火眼,也难识“庐山真面目”了。
按我的理解,个人档案是一个人从上中学开始到走上社会后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历的真实记录,这种记录一要客观真实,二要系统完整,它既不能随随便便被抽掉一些东西,又不能无中生有地硬塞进去一些内容,否则它的真实性便不复存在了,存在价值也要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档案还扮演着历史文献的角色。听说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干部三番五次更改自己的档案,最后竟闹出在出生前一年就参加了革命这样的笑话。中国人的历史如果都这么写,“有办法的人”对自己的档案如果都这样改来改去,将来我们的后代看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比看天书还困难吧?
附记:大贪官王怀忠是2001年4月在副省长的职位上落马的。但多年前他还在阜阳当地(后改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败。新华社记者在一篇文章中说,王怀忠在阜阳的几年,阜阳的干部群众就对他骄奢淫逸、虚报浮夸、腐化堕落等行为非常清楚且反应强烈,群众中甚至流传着一个民谣是专门讽刺王怀忠的(新华社2004年1月18日)。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腐败分子升迁时却一路绿灯,且升迁速度极快,平均两年上一个台阶,直至1999年11月登上了副省长的高位。由此我们不难断定,王怀忠在阜阳当地委书记时的“腐迹”,在他的档案里是找不到的。类似王怀忠的例子还有很多。最近海南省又暴出一宗档案造假丑闻。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局长叶东雄在任不到3年,就接收安排了近200人进工商局,光他的亲属就达20多人,当地群众称其为“叶家军”。经过半年调查,现已查明这是一宗全国最大的档案造假案。万宁市是个仅有50万人口的县级市,按编制市工商局干部职工应在280人左右,但叶东雄硬是将一个县级市工商局扩充至近千人。目前,137个档案造假者已被清理出万宁市工商队伍。(据2004年06月10日12:19 新华网)
首发2005年《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