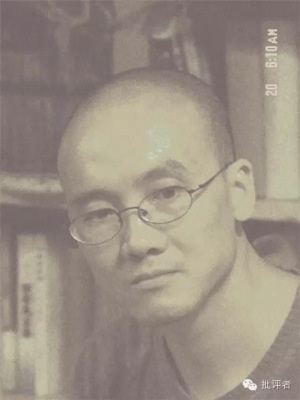2015-07-24
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直接谈论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不必去关注一个诗人。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他由个人成长,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时代命运所共同构成。就诗人王辰龙而论,他父亲在铁西区化工厂上班,母亲在(1990年代破了产的)铸造厂上班,父母皆为普通工人,一家三口生活在铁西区名为工人村的区域。工人村建筑于1952年9月23日,5个建筑群72幢三层砖混楼房,建筑面积99012平方米,属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是当时领先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王辰龙出生于此,对这个地方当然有书写的便利,可是他并不追求这样的书写特权。再则,他要避免用二元论模式所推动的写作,即通过刻意梦幻的、过分透支的过去对现在(即便现在不那么尽如人意)进行否定。他认为,这样非此即彼的写作容易造成文本的自我复制和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语义空转。他的这些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会帮助诗人找准诗歌写作的焦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关注作为诗人的王辰龙,而仅仅只关注他写的诗,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生活的碎片化需要个体写作者去整合公共资源,以形成其作品可供参照的价值共同体。当然,事实上与铁西区相关的诗歌创作也只是王辰龙全部写作的一部分。单就这一部分来讲,他想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消逝,而非言之凿凿的过去。这儿有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诗歌创作更是对现实的重塑。
一种过程的消逝,王辰龙深刻地意识到,其实就是生命的消失。因此,他的写作实质上是基于自救。自救,是他写作《工人村与影子》的私密动机。他说,正是基于自救这一私人目的,我才和铁西区发生了诗歌意义上的关系,而非由于工业区的重要性,反之,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对工业区的重要性有了体悟。因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会担心断绝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成为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成为被此时此刻所困的失忆者。显然,工业区,是指铁西区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是属于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王辰龙以“建筑师般的手温,把每个词都抚摸出石头的质地,以便能够构建一个立体的、可供重返与置身的文学空间。”这与其说是他在诗歌写作上的一种渴望,还不如说是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卓越的实践。
因此,王辰龙以铁西区为生活原型创作的长诗《工人村与影子》,从一开始就不为写什么发愁,而为怎么写焦虑。对此,他在创作谈中自述:“倘若真写出理想中的作品(对我这样一个诗歌学徒而言,它还很遥远),它的光,应源于‘如何写’,而非‘写什么’,我渴望完成的诗,如果仅仅建基于铁西区自身,而非精湛地、准确地对人与事进行诗性的传达,它的诗歌伦理将是缺失的,终究沦为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分行注释。”他谦卑地称自己为“诗歌学徒”,只能说明对于写作他是有备而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自然是令人佩服。除了“如何写”,他还有另外两个意识。一是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即言说过去,但在发生机制上,有不得已而后言。这样的写作,被他描述为,把年龄之雾与时代之霾交结而成的夹角视为写作的现场;这一诗学设想,在现阶段的写作实践中转化成了这样的面貌:当铁西区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空间进入文本,旧日的人与事——注意又是人与事,以幽灵般的行状漂浮其中,通过新旧两种景观的重叠,对一种完整性的重建作出想象。这样的描述,有他的诗歌创作对于现实进行重塑的一个方法论。
2007年,王辰龙19岁,他离开铁西区来到北京。至今,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也许是家乡与首都的局部相似,使得他虽然离开了铁西区,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疏离感。他萌生创作《工人村与影子》也就是这两三年才开始的新事与心事。而对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北京,在一篇访谈里他有过这样的讲述:前不久,我坐1路汽车途径天安门,想起当代诗中“广场”一词的语义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诗人们纷纷以“延安”为蓝图,对再次被加冕为首都的北京展开了新一轮的空间想象,文本中的老城变得肥胖不堪,仿佛被汉语言歌咏的地球上只幸存这一个庞大的空城;它无人,只有革命机器的运转之声。与此同时,它却又极为枯瘦,丰满的细节和感性的赋形都因过剩而非法,只需写下“天安门”或“广场”,再让一轮红太阳升起就足够了。政治抒情诗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这不能说是他对国家诗人的不满,而是他对这样的写作观念保持了一种警醒。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样写作的“无人”状态。他进一步的理解是,所谓“无人”有时是指人群对空间中某种意识形态的盲从,进而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性:千人一面,便是空无一人。无人,无人区,鬼城,可以对应于他记忆中的新区和旧区。他曾经生活过的工业区已经是情感体验深处的无人地带。近年来,工人村相继拆迁,只有几处老民居被保留下来,原来的工人家庭渐渐分流到新兴的商品住宅或回迁房,以陌生人为邻。以前在低矮,四五层楼高,红色砖墙的苏联式民居里,与其他家庭分享公共的走廊、厕所与厨房,这样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从而留下了一些记忆断片。他想起父母和工友们在苏联式的民居里,醉醺醺地高谈阔论,其中有对厂子前途的忧虑、对个人生活的不安,不得已带有佯装成分的乐观,穿插着妙语连珠的段子,大多是荤的,时有影射性的民间意味,以此修复生活压力所造成的空洞。现在的工人村生活馆,用以展览他们消逝的生活。每次从北京回家,工厂旧址上的新楼盘,新的街道,新的商业广场,都以骤然来势更新着他的景观记忆,它们喜气洋洋地覆盖着对于幸福生活的高调许诺。但王辰龙已不在这个生活现场了,视觉上给他的一切,只是遭逢转变后的结果。一种存在的过去愈发空荡,属于他而又远离他,令人心虚与恐惧。所以,他创作长诗《工人村与影子》就是打算为这个消逝的过程留下一些抒情式的记录。同时,通过写作也可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使自己不至于成为故乡的异客。而事实上,他已经是异客,这注定了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是一曲唱给生命流逝的挽歌!
诗人穆旦与昌耀,是王辰龙不时重读的诗人。就像王辰龙在写作工人村时并不是以工业区的重要性为出发点,同样的,他的诗歌写作虽然受到昌耀由书写城市空间取代高原空间的启发,但并不意味着他跟昌耀一样与左翼文学发生过关联。在王辰龙这儿,至少有着难以弥合的时差。这个时差,恰恰是我们这个物欲化的时代,众多文化断裂中一个诗歌小传统的断裂。在个人趣味上,王辰龙表示较少阅读左翼文学。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那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左翼文学运动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加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左翼文学对于王辰龙而言,最不能接受的,恐怕是由于过份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从而忽视了其他文学力量的一些正确观点。但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城市空间里发生过什么,这是王辰龙比较关注的。1920年代,城市赤贫蔓延、犯罪滋生,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堕落、腌臜与空虚,常被用来指控城市。上海的街道,成为整个现代中国遭受死生之痛的象征空间。它无法提供充足的、持续的工作机会,以保障平民与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不断有人在街头暴毙。尤其在冬天,一夜严寒过后,晨晖照亮的街头总会有数以百计的尸体。左翼诗人如何表述他们体验到的都市呢?都市又如何重构诗人的写作主体意识呢?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了,王辰龙作为一个当代的年轻诗人,他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就长诗《工人村与影子》而言,其答案,是充满记忆的空间被新风景遮掩,已成废墟!
王辰龙在评论诗人昌耀时认为,他把城市空间中的人群言说为纪念碑式的存在,把乞丐、盲人、破产农民等边缘者组成的人群,塑造成都市里游动的纪念碑。同样的逻辑,王辰龙在长诗《工人村与影子》里形成了自己的表意系统,他们是童年记忆里的玩具枪、糖果、竹蜻蜓、纸蛙、窜天猴、冰湖、冰锁、浮冰、欢喜佛;是生存环境里的积雪、秋老虎、伪地府、监狱、人造湖、通勤车、抽水泵、工人、游商、小二郎、厌食者、晨泳者、垂钓者、守林人、养蜂人、拾荒人、远人、山野坟墓;是居住环境里的红砖、鬼城、妖、声控灯、灯火等等。这些词语是王辰龙的诗歌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空间,一个记忆里人与事的活动现场。如果说我们并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时代工人村作为工业区的重要性,那么在王辰龙的诗歌表意系统里,他算是真正抓住的一个喻意丰富、意味深长的词语,那就是:钉子。在农民与工人曾经被新的权力允诺为国家的主人时,钉子就是他们的时代象征。当王辰龙见证了革命话语的失败,和物质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挫折之后,他写下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句:
噩梦里,一个钉子
变大变强,它让目的地脱轨
我们必须记住,是噩梦。一个钉子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但它和美好的目的地脱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所召唤的过去,并不意味着过去是完美无缺的世界,而是要去提示某个更好世界的可能。因此,他认为,史学的解释力,或是欲言又止,或是难以道明。当代史正被迫成为秘史,面对此情此景,能否借助诗学来承担记录秘史的职责呢?他写记忆中的体验,结巴而生涩的追忆口吻,旧时的人,旧时的事,与某个往昔时空一起复现。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呈现出了记忆本身与诗意自身之间的界限。界限内外,他捕捉的是心理遗迹和历史细节,用现代汉语实践了一种与消逝对称的抒情。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沈阳铁西区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是屈辱史的起点,这想必与其他有殖民记忆的中国城市类似,追根溯源,父亲所在工厂便是日本人所建。从这一状况,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制后的当代,铁西区确已成为凝固着种种瞬间的历史断片,携带了剧烈而忧郁的漫长本事,可能是社会科学目光中理想的研究对象。”这样,当王辰龙试图在诗中言说过去,工业区的本事就变得极其有重量,构成了压力。这是多么的忧郁,多么巨大的忧郁:晚课、晚归、城市的晚炊。王辰龙作为一个返身无归处的记忆者,通过近景、闪回、重放,远景,就这样,影子在深处渐渐失焦。如果说,工人村是现实,那么影子正是对这个现实的重塑。
2015.5.21
作者简介:
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
附:工人村与影子
王辰龙
序章:重返工人村
1
入冬的、阴糜的晨风,八月新建的站前空地
吹出流汗的气锤,起落之间,回家的工人
留下影子,与人群叠合:依旧背着秋日的
老虎,他们敲稳石板,任由俯蜷的姿势
被旅行箱一次一次洞穿。
这是晨泳者冒然入水,我正走进并未久远的
往事。步出沈阳北站,心脏便紧缩,恍若
夜行人竖起寒冬的衣领。地下岛的入口在何处敞开?
2
先于我,那个影子跃离了地铁二号线,
他等在铁西广场,等误闯旧日的小二郎。
他的哈气散得缓慢,跌宕着升腾
延展成默片的银幕——他看我正骑车
从兴工街拐入建设大路,刹住了
次日的近景;而缺少目击的前夜,闪回,
重放,骤然加速:球锤高高擎起,碾过老区的
春晓,几辆大车开往雪花啤酒厂。远景
终究升起了瓦砾堆,趁第二夜尚未降临,
拾荒人荒墟上垂头往复,他看我正望着他们
以铁在土石中探铁……
影子的深处渐渐失焦,熄灭一支黄金叶,
他寡言的口舌为消逝而发炎。那破声的
只是他此时此地的应答,关于公交站的新址——
这一次,惶惑的方向感从歧义的丛林突围。
3
瞌睡于多盐的梦表。街道翻涌着,
由鱼缸里的海拥上规划失误的柏油沙滩。
缓缓下沉的公交车又在重工南街浮出
一些迹象正逗引可爱的敌舰向它发射
童年的深水炸弹。波浪刮过车窗混着
另一种更远的声响——是雨前风
红砖红砖间走马,工人村褪色的楼群
其中有一个我正掩笑,声称腹部有恙,
把共用的窄门久久紧锁,任你急。
我们各自的母亲在共用的厨房诅咒坏天气。
还未善饮。还未患上皮肤病。还未坐通勤
在机床厂与家庭之间往返。你变小了,虚构着
想骑上俺们不曾近观的海豚,却只是披起影子
佯装食梦兽,吃我吃到我徒留打滑的一觉。
从有人摔倒的旱冰场你伸来左手,轻拍我,
拉我提前五站就下车。“去河边吧!”卷折起
丰雨之年的地图,你的影身,镜子般与我相对。
4
坐一会儿或更久,多么好的地点
你邀我看水看对岸的疏林,继而
搬演出走者,用突然消失的方式
留我向远人重修关于惊叹的晚课:
错把天阴阴望成了洪流漫漫,时间,
水下倒映着被星群推动,轰鸣而来;
可内心的道德法则,那失灵的扁舟
已自横于枯水期的浑河中央……
渐渐听清了此地的两种声响:
水边草,面朝城北降下半旗;
被排出的黑暗,正滚入
提前上灯的污水处理厂。
而倦鸟低飞而过的身子里
你终于再次溢出,收起翅膀
显身于垂钓者收杆的手势——
我一直在寻你,正如你搜我的藏身地。
沿着晚街上起雾的记忆,
你笨拙起舞舞成一团微火
照亮了此起彼伏的影子:
走着回家,在影子的念白中取暖。
影子:迷恋铁轨的人
铁轨。
南北延伸的、狭长的青色海
无数阳光之岛显出轮廓。
这是雪霁后的时光机器发出
寒假的噪响,我们的父母
正在铸造车间的机床前。
而你,潜游着找到了
适于搁浅的滩涂,放好
钉子。
抑或你俯身放下的是一枚角币:
这取决于你想得到的是一把剑
还是一掌盾。
你转过身的表情
就像月熊那优美而无知的腹部。
返回枯草的避风港,你与几处山野坟墓
与地上雪,与我共同等待
大地的震颤。
那么快就消失于平静的下一个小站。
你盯住它的飞起,以及它
平展了整个躯体的新生。猎犬从雪野
叼回银兔。这一次,你将一把小剑
送给了我。骄傲是十二岁的皇帝。
获剑的小夜。
噩梦里,一个钉子
变大变强,它让目的地脱轨,
它放倒了运送化工原料的专列。
影子:吃冰者
最先发现诱惑的他们
带我越过铁轨
来到人造树林的新大陆。
干瘪的小路通向冰湖
和冰湖上的缺口。
而我所无法说出的情节,
或许只是守林人的醉酒夜:
渴望着冬歇的鱼,潜入者
举起尖锐或钝重
一次又一次落下
直到周围的树木惊讶于
水发出的气息……
我开始害怕,湖上的缺口
似乎正在张大,就像资深的妖
伸展出吸纳好人的神器。
他开始打捞深渊中的浮冰
一块,两块,三块,寒假的
局部的天空也被搅乱了三次。
“冰是甜的”,他这样声称,并将
收获分发给我们。咬下去,免费的冷
和恐惧,就在唇齿间脱开紫色的缰绳。
哈出的气也开始颠簸,一同动荡的
还有落脚处偷笑的分裂。
他落水,手中紧握的冰也浸入窒息
我已经忘了,在发愣和乱喊之后
你是怎样被重新拉回流不动的世界
正如我也忘了,吃冰的日子怎样收场。
影子:马铁虎
你痴迷急速上升的事物。他骑车下班,你
仍追赶竹蜻蜓的落点,直到她推开厨房
第二扇门,去阳台探出声音找你,骂你上楼。
南窗也已系上冰锁,年关近了,另一个下午
绕到化工厂小区的北面,一次次点燃窜天猴
灰色的短尾:最高的那只,误撞药厂宿舍的
屋檐,五层楼,我屏住呼吸……是年的五月,
劳动公园筑好鬼城,在伪地府的出口
我听见你体内的火药肾上腺般地呼啸:
不够……还不够。余下碎银两,我们就奔往
凌霄飞车飞过夏秋与寒假,你却抵达他
某夜的切齿:“永别了,工厂。”继而,他竟
向她和你作四年的暂别。“大北监狱,大北,
监狱。”起哄着挤作一团,他们踢沙土,你
紧跟她,不曾怒目不曾打过来,只是消失于
六单元的暗影之中。他终究回家;你一直在
却没再归来。“下来玩呀,马虎!”我听见我
一跑出五单元便喊,略去你名字里散发
黑硬光泽的部分,它像十余年前的流星,
划过此刻京畿突兀的晴夜:有人正在城北
隔着十一月的狭渊为烟火鼓掌。我想起你。
影子:姐
风发出了响动,我们的耳朵是挂铃般的
眼睛稍稍张开,它们透过温暖的幕纱,
摇向一边,看蹑手蹑脚的流动如何平息。
你总先于我,离开午睡的袒护,如竹蜻蜓,
出入于暑假的下午。小身子已滑过了十个
春天,你以柔软去迷恋糖果,你正爱得发痴
却单把糖衣留下,双目纤美如丽人手,将斑斓
喜看,你抚平塑料彩虹的褶皱。而那些炮弹,
都打给了我,我不归地发胖,并将跃向某一种
未来和八月末:被秋老虎紧盯,流汗。你则会
瘦如水果硬糖,一裹上花花裙衫,就去小城探望
改嫁多年的母亲。好时光如今想起都留在夏天了:
呆日头扒着工人村的建筑,五层楼曝露着红砖
从四面围拢花圃,野草正紧。我们无法掘出深坑
用以掩埋他对她说出的狠话、她对他施加的咒骂。
就找一片铁凉亭边的松土,挖妥了小而深的窠臼,
你落稳本周最爱的糖纸,你覆上汽水瓶底或碎窗的
一角。俯身赏玩,回土,踩实……可你不曾在冬天
再找回它们,即便当年的雨季没有过膝。很多次,
你沮丧极了,不甘心,泪水顺雪原的反光飞入
繁星的行列。而我,陪你一起等待,等冷锋过境。
影子:姥
伏天里的厌食者消瘦依旧,她步入腊月,总是
走得太快,却未尝溅动声息,往后也不曾亮起
声控灯,久久封冻楼道的昏暗,直到一把明锁
弹开门后的微光。紧跟她你踅过公用的长走廊
邻人们堆出的旧物又多出几件,它们轮廓上的
手温正退向你有关疼痛的记忆:是独自回家的
坏时辰,走廊愈发狭长,得小心绕过雕花木箱
闪避卸去了后轮的废车,赢取啪叽的那个夏夜
它们碰碎过你的欢喜佛。三楼高的苏联式民居
这惊觉之前的魔方大厦,你终究还是无法把它
扭转为玩具柜台上的六面兽,一个她许诺中的
礼物,它忽暗忽明在停电的冬夜;而卡车碾响
阴着脏雪的后街,擦亮梦魇的余震,你看她正
用点燃波心的手势熄灭磷火,等待他们的晚归
影子:爷
叫卖更近了,如爬山虎,它攀附
工人村新楼的外墙,尖梢漫出
打糕的诱惑,绿得刚刚好,足以
佯狂成一声钟,响彻你的瞌睡。
把左手从往事里探出,你练习醒来
唤我,一边摸索与喜悦对称的零钱。
而我正在模糊的大雪中走不出来:
肇工街,雪,拥挤多时,我五岁
站了起来,惊喜于被棉花接住;妈
扶起摩托,惊讶于我不喊疼,还乐;
往卫工街继续走,走入另一片白色
听你躺卧酒精气味的暖围,笑谈如何
被司命小仙的血栓箭狠狠命中……
跑回三楼卧室,八月的阳光蝉衣
都来不及抖落,就与你咀嚼此刻
我们最大的福。我后悔,我忘了
向那好游商去讨一个回答。星期一
他还会来吗?甜海的潮汐出入南窗……
这是石头流满你右半身的第六年的
某天下午。点了心的你拈起白纸
它缓缓鼓起蛙的姿态,你教我按
它的臀,蛙便跳出半指之远。你
继而依次拈起八张纸,恍若扯动
大小不一的八个扁木偶:前仆后继
它们在瑜伽中折起身子,成为
塔的局部……我真后悔,祖父,我
忘了问你那可以站立的纸塔顶端是否
藏有时光灵骨,能给二十五一剂醍醐?
影子:劳动公园
绕湖再走上几个圈,一片大水才会率先开口?
有时,落下柳叶,掠过未名鸟,就像一场好雨
打在腕表的玻璃脸上。湖中央有阴郁的马达,它
把秒针之手伸向我,沿着人造湖那完美而虚假的圆形。
攥久了的石头开始生气,比我更加腻烦
这被回忆摧毁的下午。我将它甩向湖心
尚未落水,便成为子弹,返身飞回童年
紧握着的玩具枪:在游乐园,我重新瞄准——
却只赢过坚硬的糖果,而一切也开始慢慢变甜:
云变甜,新城区的空气变甜……
以乡愁的速度,你怀念公园南墙下咸味的潮湿。
影子,或尾声:重工南街
1
撬开一点窗子,是否就意味着
能撬动车载电视长久的蓝屏?
颠簸完了色情二人转,喇叭开始
向邓丽君致敬。司机成功戒酒,
通勤车昏昏沉沉。再撬开点窗子
放进些冷空气,是否就有了足够的风暴
能容许你起飞,旋转?你累了,
整个下午和其他人一起,用一个小时
修理抽水泵,用两个小时追捕小蛇,
采集野芹菜。你的双手正衰老,指甲里
小心翼翼地窝藏着硫化物的余味。
而下车时,我看见你分身成为年轻的丈夫
穿过重工南街回家,身姿轻盈
就如此刻整座城市的晚炊。
2
从窗口望出去,你确信(并大声宣布)
都市养蜂人正朝重工南街走来。
邻人们吞吐生长薄翼的词语
纷纷飞向你——“疯子!”
他们都说你疯于是你就真真假假地疯。
从窗口望出去,一刻钟走了一圈年轮
富余下的时间就用来抱怨与恨
你骂不来看你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
你骂供暖不足,你骂冬天真冷。
把狗拴在第一重门的阴影里,你
感到安全。我看见你分身
成为疯婆婆,用年长的手指
久久掂量着你身上的隐形铁链。
3
天暖时,积雪融化,潮湿
渗入租来的墙壁,开出
乌云之花。你忧心屋子里
会下起一场隆冬小雨。
困守于深夜。隔音失败
越过天花板,无数只噪声之手
不时地探伸而下,推搡你走上
偷听者的不归路。你偷听
他们欢爱他们争执女主人
不在的日子里他整夜整夜
移动椅子的位置。困守深夜
倚着家乡的床沿,你眺望
重工南街的灯火。当冷一再
钻入失眠的脾脏,我看见你分身
成为另一个我:暂居此地,读书,写作
维系着微薄的尊严与不沉默。
2014年12月 北京 魏公村
文章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