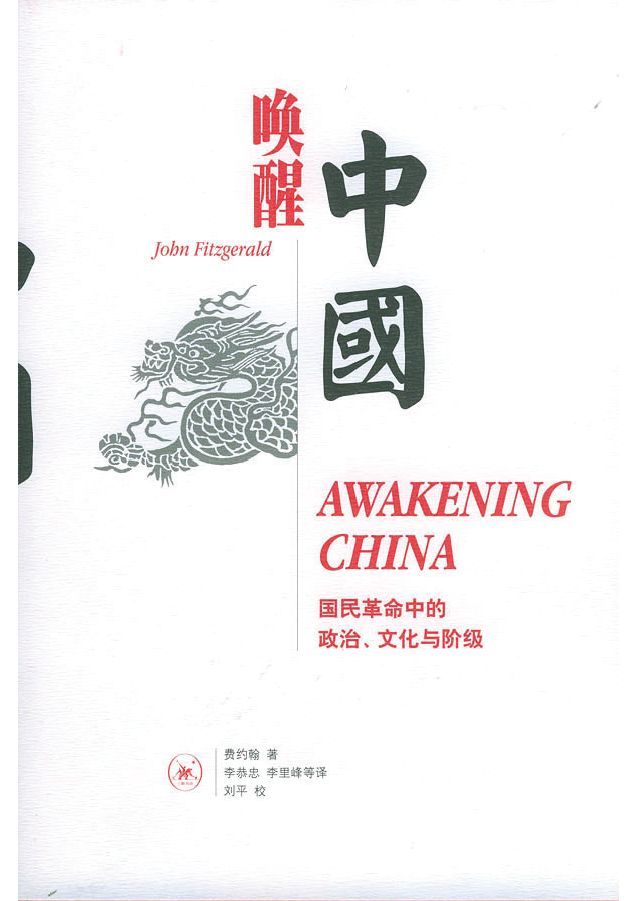——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基都是帝国王朝的独裁主义或专制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基都是帝国王朝的独裁主义或专制主义。
——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
在我的少年时代,似乎没有哪个家庭拥有电视机,我所见到的第一台电视机是父母工作的工厂购买的。每逢周末,就出现了壮观的场景:数百个大人小孩围坐在大饭堂看那台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机。我还记得,看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香港武打片《霍元甲》。一夜之间,《霍元甲》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响彻大街小巷。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著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时,“唤醒”这个词语让我又想起了那首沧桑而昂扬的粤语老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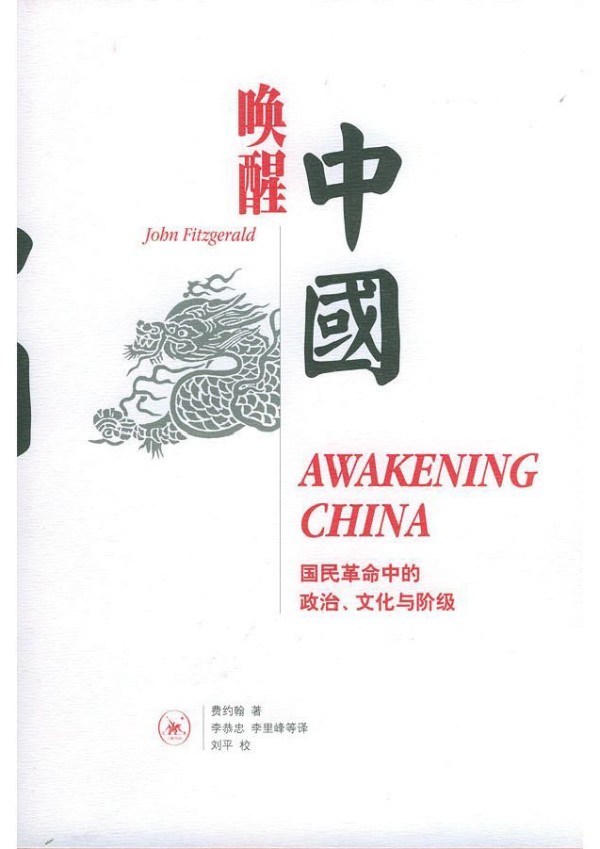 二零零五年,我在墨尔本与费约翰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他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康复。我们一起喝咖啡和聊天,我惊讶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如指掌和洞若观火。《唤醒中国》是一本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历史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影响巨大。作者以“唤醒”这个近代中国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为切入点,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剥去了国共两党的官方史学加诸于国民革命身上的厚重油彩。作者从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中,以火眼金睛般的敏锐梳理出“一个中国、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种声音”的形成过程。人民不是被唤醒,而是被加以更可怕的催眠,人民成为被国共这两个列宁式政党肆意驱使的“丧尸”。
二零零五年,我在墨尔本与费约翰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他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康复。我们一起喝咖啡和聊天,我惊讶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如指掌和洞若观火。《唤醒中国》是一本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历史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影响巨大。作者以“唤醒”这个近代中国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为切入点,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剥去了国共两党的官方史学加诸于国民革命身上的厚重油彩。作者从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中,以火眼金睛般的敏锐梳理出“一个中国、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种声音”的形成过程。人民不是被唤醒,而是被加以更可怕的催眠,人民成为被国共这两个列宁式政党肆意驱使的“丧尸”。
是联邦共和,还是中央集权?
我到台湾访问时,发现所谓的“国父纪念馆”中有中国革命史的展览,在许多历史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叙述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惊人一致:陈炯明被称为“陈逆炯明”和“革命叛徒”。
孙文一生最恨的人,不是慈禧太后、梁启超、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政敌,而是陈炯明。孙文将陈炯明视为门徒,当陈炯明不愿支持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时,他就认为陈炯明是无耻的背叛。而陈炯明仅仅将孙文视为一个暂时合作的地方领袖,对其并无人身依附关系,当他发现孙文并不信仰民主、自由和法治时,立即与之分道扬镳,这样做有错吗?
关于孙文对陈炯明的“背叛”的耿耿于怀,费约翰用幽默又逼真的笔调写道:“只要听到陈炯明这个名字,孙文的表情就会由和善变成愤怒,如果有谁为陈炯明辩护的话,孙文就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有一次,孙文的顾问赖世璜请求孙文对陈的“背叛”示以宽大,孙文愤怒地质问说:你是不是他那一派的人?甚至发疯似的对卫士挥手,下令说:“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为何孙文对陈炯明的愤恨到了情绪失控的地步?费约翰的解释是:“孙文心里积蓄了对陈炯明的强烈愤恨,不是因为他与自己明显不同,而是因为陈炯明以同样无私的精力,去追求一个关于民族统一的不同的梦。”
具体到在广东省施行的政治模式上,一言以蔽之,孙陈之争是“党人治粤”与“粤人治粤”之矛盾,两者的区别在于:是由一个拥有独特的党派追随者的政治派系来治理,还是由一些拥有独特的地方追随者的士绅来治理。而在整个国家的结构上,陈炯明赞同联邦共和,孙文则坚持中央集权。陈炯明主张各省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欣赏高度的区域自治,以及相应的中央政权地位的降低——简言之,一个联邦政府。一九二一年,陈炯明在广东推动县长和县议员通过公共选举来选择和任命,却遭到孙文反对。陈炯明还实施了广州市议员的直接选举,放弃自己作为省长在传统上所拥有的对三分之一市议员的任命权。当时,就连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民国日报》也作出正面评价:“这不仅是广东的突破,而且在中国的民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其实,不仅史无前例,亦后无来者:九十年之后,中国尚且不能迈出乡级选举的步伐,甚至连香港的“双普选”也遥遥无期,香港立法会中所谓“功能组别”的非民选议员恬不知耻地“代表”着市民。历史的停滞与倒退,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二十年代中期,当对联邦主义的支持开始呈现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态势之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紧随孙文其后登上公共论坛,对联邦制口诛笔伐。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优缺点,完全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势力”和新发于硎的“革命力量”尖锐对立的框架之内评估。代表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联邦主义与共和主义,居然被孙文和共产党妖魔化为“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一词被用来解释军阀与联邦主义运动的姦诈关系。对此,费约翰评论说:“对于这个世纪中国的更伟大革命而言,国民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它对待语词的方式。……革命者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到了一九二二年,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学,都不足以像列宁主义那样,能够精致地解释新中国的困境。”
孙文是党国体制的始作俑者
在今天的台湾,孙文像仍然定格在新台币上;而在今天的中国,对孙文的崇拜仅次于毛泽东和“今上”。孙文跟台湾无甚关系,民主化后的台湾,大部分民众对孙文“无感”——甚至连反对他的意愿都不大,他毕竟没有像蒋介石屠杀过那么多的台湾人;而很多海外中国政治流亡人士以及中国年轻一代愤青,却将孙文作为一个对抗共产党统治的符号,作为“光复大陆”之后的中华民国至尊无上的“国父”。对于此种具有讽刺意义的“时光倒流”,本书中文译者在后记中指出:“今天,当人们把孙文视为‘走向共和’的符号时,有没有想到他同时也是‘军政’、‘训政’的始作俑者呢?许多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是决不能用‘一种声音’来发表意见的。”
孙文是中华民国的终结者。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孙文明确提出用“以党建国”取代“以党治国”,颠覆中华民国的企图毫不掩饰。他宣布要建立一个国民政府来取代共和政府,党将复制政府党组织并监督其各级运作。孙文在演讲中指出,党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允许党员自由活动,并使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发展到了超出党本身的程度。所以,所有党员都要将个人自由交给党。这就是隐藏在列宁主义路线指导下党政改组背后的基本原理。
屡败屡战的孙文找到了咸鱼翻身的秘诀:创建列宁式的高度纪律化的党国模式。他致力于将宋教仁时代作为选举型政党的国民党改造成“准布尔什维克党”,尽管终其一生都未能完成。孙文的理想是,在党国体制下,党牢牢掌控每一个领域。费约翰提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党代会结束后的两个月内,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大理院院长赵士北——一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家——的职务,因为他坚持认为党规不能凌驾于法治准则之上。他被指控散布“司法无党”的观点。在关于党与司法的关系上,孙文和他的追随者宣中华、毛泽东都宣告说,“在党规则和党治体系之外,将不会有任何法律”。这様的思路与中共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宣布的“党主法治”何其相似。对习近平而言,党章高于宪法,宪法只是党章的细化。如果孙文前来列席中共的全会,大概会心有戚戚焉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遵从孙文的命令,在一项决议中通过国民党的新党歌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并且“将来定为国歌”。一九二四年八月,孙文下令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从自己控制的华南地区所有机构的旗杆上降下,并升起“青天白日”的党旗。从一九二五年元旦开始,当地公安局长对继续悬挂民国国旗的市民处以罚款。费约翰指出:“旗帜的改变既不标志政府换届,也不表明着国民运动领导层的变化,但它显示了民国历史中的深刻变迁。它预示着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五色旗在中国的公众仪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两种全国性旗帜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种都只认同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党派。”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民国热”中,有多少年轻人知道这幕改旗易帜的场景呢?
在书中,费约翰还分析了孙文“圣像”的确立过程,以及国共两党为什么都供奉这尊“圣像”。无论是中山陵的修建,还是将总理遗训、三民主义等编入中小学课本,国民党不遗余力地将孙文塑造成一个新的偶像。而蒋介石以孙文的学生自居,继承孙文的遗产就如同古代的皇帝子承父业一样。
毛泽东是孙文的好学生
其实,比起蒋介石来,毛泽东才是孙文更称职的好学生。在逃亡台湾之前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成孙文的遗愿——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列宁式政党,将国民政府打造成一个苏联式政权。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毛泽东没有沿用孙文的国号、国歌、国旗以及“三民主义”,却将孙文思想中独裁专制的一面升级换代、发扬光大。
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面向,作者用长达几章的篇幅叙述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代理部长期间的工作情况。“毛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这段经历却对毛影响甚大。
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泽东受命代表汪精卫管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毛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雷厉风行地实现了几名旧文人气十足的前任未能做到的事情:首先,有系统地清查党内出版物,不定期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检举。比如,对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上海的党刊《革命导报》,以及美国总支部在旧金山的资深日报《少年中国晨报》提出控告。其次,让宣传部这个此前被人们视为可有可无的部门蜕变成一个党的核心机关,毛向国民党各部门发出指令,个人和组织在公众场合发布的一切宣传资料,都要送交中央宣传部检查。第三,利用这个机构来清洗来自党内的政治敌人,或者通过群众斗争的方式发现外部的敌人并用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毛泽东是国民党历史上最能干的宣传部长。而这八个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生涯,也赋予毛对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宣传的巨大功用的崭新认识。用费约翰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广泛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验,来设计自己的主义和战略,并在自己领导之下即时地发动了一场纪律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与孙文所设想的目标相同,但却没有了孙文主义的障碍。毛泽东所设计的一套民族革命的战略,它将在策略允许的范围内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以便利用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在一步步地走向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长征”中,毛把宣传工具视为与军队和秘密警察系统同样重要的、“三足鼎立”的利器。只有牢牢掌控此三者,权力才能稳如泰山。与之相比较,党务和政府序列反倒没有那么重要,他可以放手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可以随时收回来。后来,毛悍然发动文革,其实就是一场“宣传革命”,毛不厌其烦地亲自起草和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决非小题大做,因为社论中的一个字就可能剥夺百万条人命。与之相比,孙文与蒋介石确实是“略输文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国民革命的灵魂人物是孙文、蒋介石和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孙、蒋、毛的“三人传”。国民革命是一场战争,更是一场“话语革命”,《唤醒中国》一书中涉及到了与奥威尔式的“新语”系统相对应的诸多领域,如建筑、绘画、时尚、文学、伦理、地理学和人种学等,无不别开生面而发人深省。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发现,孙、蒋、毛都是中国民间传说和好莱坞影视中的“赶尸人”,驱赶着被他们深度催眠的千千万万的丧尸,走进万劫不复的地狱。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