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一生是从苟活通向枉死。
——冉云飞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严,有的国家的公民却如同现代奴隶般不得自由?为什么有些国家轻而易举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国家却不断遭遇挫折甚至被滞留在失败的阴影中?一个人的贫富成败,可能源于若干个体性的、难以复制的因素;而带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繁荣富裕、成功幸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富裕、成功的社会或国家能一直持续下去吗?为什么有的社会或国家的富强宛如昙花一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的富强者却能维持数百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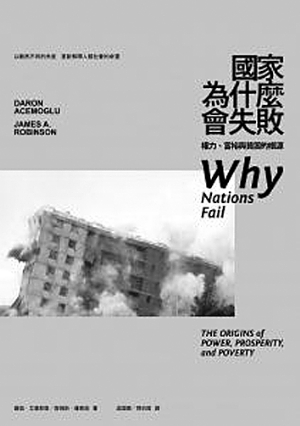 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一书。这两位在各自领域享有顶级地位的学者,宛如黄金搭档,以全球史为素材,运用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与政治学洞见,全面检视欧美亚非等地的历史发展,对“国家何以失败”这个困扰国家治理者和普通大众的问题提出了简洁有力的理论解释。该书被称为“国败论”,与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并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赞扬说:“作者以说服力十足的方式阐明,国家只有在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摆脱贫困,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制度与竞争。更具独创性的是,他们认为当国家拥有开放的多元政治体系,可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同时新政治领袖有机会崛起时,才比较可能发展出适宜的制度。他们重大贡献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紧密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显现在他们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一项重大问题极为有力的研究中。”
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一书。这两位在各自领域享有顶级地位的学者,宛如黄金搭档,以全球史为素材,运用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与政治学洞见,全面检视欧美亚非等地的历史发展,对“国家何以失败”这个困扰国家治理者和普通大众的问题提出了简洁有力的理论解释。该书被称为“国败论”,与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并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赞扬说:“作者以说服力十足的方式阐明,国家只有在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摆脱贫困,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制度与竞争。更具独创性的是,他们认为当国家拥有开放的多元政治体系,可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同时新政治领袖有机会崛起时,才比较可能发展出适宜的制度。他们重大贡献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紧密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显现在他们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一项重大问题极为有力的研究中。”
一个小镇,一堵围墙,两种命运
本书以一个名为诺加雷斯布的小镇的故事作为开头:小镇被一堵墙分成两半,两边的居民一遍宛如生活在天堂,一边宛如生活在地狱。墙这边的居民,享受免费的公立中小学教育,拥有联邦政府的健康保险,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电力、电话、网路及污水处理系统等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他们将这一切视之为理所当然,他们也可以投票选举从总统到镇长的各级公职人员;墙那边的居民,收入只有另一边的三分之一,许多青少年没有完成基础教育,治安混乱,毒品泛滥,虽然有形式上的选举,但人们视贿选为家常便饭,官员们个个都是刮地三尺的贪官,没有人愿意来投资,也就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年轻人。
一个小镇的两边,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就地理环境和居民族裔等外部条件来看,两边相差无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堵墙不是一道普通的围墙,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境线。墙的这边是美国,墙的那边是墨西哥,两边的居民生活在一个由不同制度塑造的不同世界。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但是,人们还要继续往下追问: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的制度优越呢?
作者由此梳理了北美与南美近代以来不同的发展路径,发现两者内在的差异:一个社会若能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广纳型制度”,这样的国家就会迈向繁荣富裕。反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若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即作者所说的“榨取型制度”,则国家必然走向衰败——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整体社会进步。在北美,政治革命成功地为广纳型制度及渐进的制度改革铺路,同是也显著强化了广纳型政治制度。与之相反,在南美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离开后,本土的菁英阶层垄断政治权力,进而垄断经济利益,并建立起一套榨取型的政治经济模式,于是出现了普遍的贫困和社会的衰败。
通过对这个小镇“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两位作者又考察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演变,由此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修正: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中产阶级的出现自然会促进民主体制的发展。然而,这个理论在衡量今天中国这个例子的时候就失败了:中国的经济包括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一个腰包鼓鼓的中产阶级也出现了,但政治民主化仍然遥遥无期。两位作者否定了现代化理论中的“经济至上论”或“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能滥用委託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个人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当年,克林顿与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打赢了海湾战争的老布什却意外落败、未能成功连任。克林顿获胜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用一句话抓住了当时美国人的心思意念:“笨蛋,问题是经济,是经济!”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当头棒喝般地说:“笨蛋,是政治,是政治!”
邓小平为什么能创造“中国奇迹”?
也许有人会向两位作者提出挑战: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的中国,邓小平并未开放政治参与,并未建立广纳型的政治制度,不也创造了长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吗?本书中提及的那些负面案例,如刚果、狮子山共和国、索马里、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海地、柬埔寨、缅甸、北韩等,当然都是世人公认的“失败国家”(大概惟有北韩都人民会深信不疑地认定,“只有我们最幸福”);但是,如果将中国列入“失败国家”的行列,不仅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会强烈反对,许多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中央商务区的国际游客,恐怕也不会认可这一结论吧——哪有如此繁华的“失败国家”?
两位学者并不否认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他们不认为这一切应当归功于共产党政权。他们坚信,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中国给邓小平冠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美名,根本是名不副实。而且,如果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两位学者指出:“中国的成长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另外,中国经济的成长得益于对资本主义理论的吸取,而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过去数十年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性的经济制度,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他们进一步强调说:“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广纳性制度让步,这种成长终将后继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邓小平所做的,无非是羞羞答答地承认部分普世价值而已。如果用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学者陈志武的话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者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在经济层面,邓小平倒是没有辜负毛泽东赠送给他的“走资派”的帽子。
放眼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中国奇迹”绝非独一无二的个案。在极权政治下,经济在一段时期内获得高速发展,增速甚至远远超过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先例。当年,不少学者和作家走访德国和苏联后,赞不绝口,甚至说在那里发现了人类的未来,结果如何呢?本书的两位作者将中国与纳粹德国和苏联放在一起考察,他们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比苏联来得广纳,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国,共产党是万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并不乐观——既得利益集团会拼死反对任何“可能”(其实是“必然”)触动其“奶酪”的变革。他们如此评估中国的未来说:“要想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变成广纳性的政治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
中国走不出“第三条道路”:驳朱云汉的“中国梦”
本书台湾版序言的作者、台大经济系教授林明仁特别重视本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负面评估。他曾出席过艾塞默鲁所作的一场名为《中国经济何处去》的演讲,艾塞默鲁以一九六零年代很多美国经济学家预测苏联经济会在一九八零年超越美国的例子开场,破除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迷思,对所谓中国式的“竞争”领导机制、隔代指派与共产党正确经济政策是造成中国经济成长的说法,一一加以反驳。
吊诡的是,与林明仁同为台大教授的朱云汉,却是台湾岛内关于“中国模式”的最积极鼓吹者——台湾居然滋养出朱云汉、王晓波、林毅夫之流的“中国通”,实在让人莫名惊诧。朱云汉在台大发表过一场题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的演讲,虽然承认“中共的一党专政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又为之辩护说,“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朱云汉甚至认为,共产党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中共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这一体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但是,习近平接班以来一系列集权举措,已然让此一判断成为笑柄。
朱云汉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因此,他认为台湾的应对策略应当是:“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面对中国大陆,要学习以小事大。”所谓“以小事大”,不就是“俯首称臣”吗?那样,中国随便赏赐台湾一点残羹冷炙,台湾都能“吃到饱”。
而林明仁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得到的启发,与朱云汉判若云泥:对于正朝广纳型制度的良性循环迈进的台湾,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榨取型制度的恶性循环中?这才是台湾各界必须面对的挑战。如今,习近平认为“大国崛起”的梦想已触手可及,甚至认为缔造出了颠覆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及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并主张许多低度开发地区唯有制度改革才能达成经济成长。而北京共识则彰显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对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而言,或许更有吸引力,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维持甚至强化所掌握的权力,并合理化横征暴敛。但是,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学习和应用中国模式并取得成功吗?况且,中国自己已然走入死胡同。这两位作者指出,中国目前的榨取式制度极端依赖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在这方面,其精细复杂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国一名评论家扼要地说:“要维持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有三个原则必须把握:党要控制军队;党要控制党员;党要控制新闻。”党对媒体的控制达到空前的地步,媒体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审查”之中,“媒体都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没有自由和人权保障,面包又能存留到几时呢?
中国的体制毫无朱云汉所说的正当、有效、平衡可言,否则,中共当局为什么每年要耗费七千亿人民币的维稳费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民众进入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的行列,但即便是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也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代价——环境毁灭性的破坏,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崩解,以及道德伦理底线的突破,让中国人深陷于忿怒、失败和沮丧感之中。台湾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封面,是一栋破旧的楼宇轰然倒塌的图片,这幅图片立即让我联想到二零一五年八月天津港化工原料大爆炸、不计其数的居民丧生的惨剧。作家冉云飞说,中国人的一生就是从苟活走向枉死,这句话说得如此透骨悲凉,却又无比真切。中国的网络上还有一首名为《中国人墓志铭》的小诗如是说:“我们生在中国,/我们葬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不幸,/只有这么两个!/躺在里面的,/再也不必假装死了;/留在外面的,/还要继续假装活着。”这样的国家,难道还不算是“失败国家”吗?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