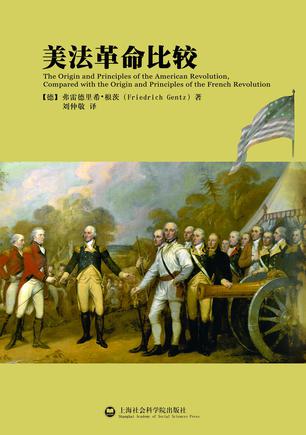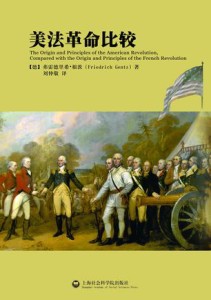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制造了许多奇观:家族反目成雠,路人同仇敌忾。老辉格党俱乐部再也无法同时包容保守派和激进派。老庇特在他的极盛时期,以人民之友和最伟大的下议员著称。小庇特在他临终前,却履行了摩西的使命:为伟大的保守党和全欧洲的反动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目睹胜利的那一天)。请勿误会:即将在威廉和维多利亚王朝诞生的新保守党跟安妮和乔治王朝的托利党鲜有共同之处;后者主要由不忠诚的反对派(斯图亚特正统派和主教制拥护者)组成,更乐于干杯祝愿查理·爱德华国王归来、而非汉诺威的乔治选侯健康。事实上,新保守党的班底(考虑到英格兰贵族政治的家族性质)和政策大体相当于上个世纪(十八世纪)的辉格党。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世风变了。庇特家族也是这样。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制造了许多奇观:家族反目成雠,路人同仇敌忾。老辉格党俱乐部再也无法同时包容保守派和激进派。老庇特在他的极盛时期,以人民之友和最伟大的下议员著称。小庇特在他临终前,却履行了摩西的使命:为伟大的保守党和全欧洲的反动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目睹胜利的那一天)。请勿误会:即将在威廉和维多利亚王朝诞生的新保守党跟安妮和乔治王朝的托利党鲜有共同之处;后者主要由不忠诚的反对派(斯图亚特正统派和主教制拥护者)组成,更乐于干杯祝愿查理·爱德华国王归来、而非汉诺威的乔治选侯健康。事实上,新保守党的班底(考虑到英格兰贵族政治的家族性质)和政策大体相当于上个世纪(十八世纪)的辉格党。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世风变了。庇特家族也是这样。
在大西洋彼岸,亚当斯家族和民主共和党人拷贝了英国辉格党故事、分别演化为美国式保守和激进传统。陈寅恪先生论证中古门第与政治,提出家世门风对政治立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是否可以解释牛李党争,姑且不论;用于封建贵族将亡未亡、大众民主将兴未兴之际,颇有启发性。亚当斯家族对杰斐逊、汉密尔顿对艾伦·伯尔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门风不正”、“浮薄浪荡”的反感。早在1800年大选之际,阿比盖尔夫人就给老亚当斯写信;把丈夫比作寒霜不改劲节的苍松,把杰斐逊比作随风俯仰腰肢的蒲柳。
无疑,这种反感很有“赵老太爷鄙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息;日后注定会引起中西一切开明人士的嘲讽,当时也挽回不了联邦党的败局。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基督徒妇女懿德的化身,从来不出妄语。她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后世宣传性传记读者眼中的堂皇雕像。
这位血肉之躯的行径足以招致任何时代“社会体面人士”的反感。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留下了煽情的斗争言论,以此获得了不小的政治资本;在英军来犯时正好担任州长,却弃城而逃。英军一撤退;他就不顾弗吉尼亚议会的抗议,匆匆辞去原本就只有两年任期的州长职务、将支撑危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他在邦联初期的政治实验期间,为佛蒙特的“人民直接司法”跋鼓齐鸣。这种激进尝试在几年之内就声誉扫地;他又忽然做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赞美杰伊和纽约州制宪的保守主义。他声情并茂地谴责黑奴制度的罪恶,哀叹弗吉尼亚子孙难逃上帝的正义裁决;自己却背弃种植园主的家长责任,(奴隶制正当性的主要论据在于:黑人没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生存,只有在家长式保护下才能安居乐业。)非但出售黑奴、而且使他们母子分离。他跟女黑奴的奸情纵然纯属虚构,在巴黎沾花惹草的行径却是铁证如山——这些情书构成杰斐逊文学天才的最好证明。
这种行径恰好符合保守派心目中的“浮薄文人”刻板印象:言大而夸,缺乏责任感;喜欢滥许无原则的诺言,却不能或不愿履行;一面借口公共利益、嘲笑传统行为准则,一面在自己的私生活当中,为道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开脱;抽象地主张平等、同情弱者,具体地放弃精英责任、享受精英地位。保守派的箴言永远是“责任、荣誉、信仰”;“不妄作承诺,但总是做得比说得多”;“背弃信赖你的人,毋宁死”。他们轻视抽象的理论著述,重视具体的个人操守、尤其是家庭责任感;理论上否认平等、质疑弱者的自身素质,实际上却扶危济困、视之为精英应尽的责任。解放纽约州黑奴的人,是杰斐逊的敌人汉密尔顿。解救黑人奈特的人,是奴隶制的同情者约翰逊博士。罗伯特·李将军对待庄园黑奴的理论与实际,恰好跟杰斐逊相反:解放自己的黑奴,维护南方的特殊地位。
政治上,保守派的责任观主要体现于他们对人民代表的看法:人民选举代表,不是需要应声虫和谄媚者;而是需要品德和判断力高于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民代表应该以人民的忠臣自居,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冒犯人民的感情。人民代表是辛辛那提,不是卡提林;是伯里克利,不是亚西比德;是华盛顿,不是艾伦·伯尔!托克维尔对美国革命的评价最能反映这种价值观。他说:在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人民坚定地选出了最值得他们尊重的人、而不是他们最喜爱的人。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建国关键时刻的舵手恰好是这样一批人(联邦党人);承平日久,美国政治家的素质也退化了。民主制度容易培养一种人民的佞臣,他们对待人民就像路易十四的廷臣对待君主:奉承主人的虚荣、损害主人的利益。
在亚当斯夫妇的历史版本中,杰斐逊就是这种缺乏原则的政治家:为了博取民望;不断修改自己的意见,追赶反覆无常、不负责任的民意。亚当斯恰好相反。他在殖民地群情激愤、暴民滥用私刑之际;挺身为枪杀市民的英军士兵辩护,为他们争取到无罪释放的判决。(根兹在书中提到此事。)英军来犯之际,他的家乡是最早的战场。他在本地组织义勇,并没有抛弃职守、然后远飚海外。亚当斯父子夫妇都是基督教家庭美德的化身。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法国革命的风暴波及美国国内时,幸而有他辅弼华盛顿、抵制人民的一时冲动。否则,如果杰斐逊一伙人如愿以偿:对内破坏社会秩序,对外甘做法国的小兄弟、反对大不列颠及其欧洲盟国;谁敢担保美国的下场会好过巴达维亚共和国、海尔维希亚共和国和美因茨共和国?杰斐逊的私生活本来经不住攻击,但亚当斯在竞选中仍然对事不对人。亚当斯的人品本来没有弱点,杰斐逊手下的小报和竞选干事却不肯投桃报李、甚至攻击亚当斯的体型和夫妻关系。阿比盖尔夫人在信中嘲笑道:这两者只有她说了才算;但亚当斯毕生耿耿于怀。直到两人都已经风烛残年,杰斐逊写信请求和解;亚当斯仍然不能释怀。他相信:杰斐逊肯定事先知道而且默许此事。这不是政见问题,而是人品问题。
精英主义和草根民主的张力贯穿美国历史前半期,并没有随着联邦党的消失而结束。亚当斯家族几乎就是精英主义在北美的道成肉身。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杰克逊短暂而勉强的胜利、持久而彻底的失败,重演了老亚当斯对杰斐逊的剧本。随着辉格党的没落,在北美拷贝英国“绅士俱乐部政治”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亚当斯家族的政治生涯就此告一段落。约翰·昆西的孙子亨利·亚当斯得以名垂青史,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外交使命(外交官和军官显然是绅士传统在民主时代的最后避难所)、而是因为他留下了两部大作:《民主》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前者从欧洲贵族外交官的视角,嘲笑失去原则的美国民主政治日趋腐败。(当然,他所谓的腐败是罗马意义上的腐败:政客罔顾公共和长远的利益,以自私和短期的恩惠收买选票;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腐败相比,行贿者和受贿者恰好交换了位置。)后者哀叹自己在工业和群众的时代越来越丧失方向感,人类也越来越陷入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力感。另一位保守派切斯特顿宣称:偏见是智慧之母,伟大的偏见蕴涵着比事实更深刻的智慧。小亨利·亚当斯的著作就是这一类偏见的结晶。
保守派一向轻视理论著述,重视具体的经验和个人。如果你仅仅通过政治思想史理解历史,就会得出颇为偏颇的结论;因为绝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是保守派心目中的“浮薄文人”,他们统治着“思想的王国”、但也仅此而已。在激进派著作的汪洋大海中,保守派只留下寥寥无几的珊瑚礁。根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座珊瑚礁。约翰·昆西·亚当斯引进此书,主要是为了反驳美国国内“流毒甚广”(本书序言)的谬论:也就是杰斐逊式的激进派历史版本。这种史观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视为同一原则的产物,企图用抽象、不可靠的人类权利取代具体、可靠的盎格鲁传统自由。华盛顿、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最忧心忡忡的,就是这种发展倾向。
不过,我们不能片刻忘记:盎格鲁的保守主义只有在英语世界才是保守主义。它跟欧洲大陆的天主教-正统君主派保守主义鲜有共同语言,跟西欧以外的所谓保守主义就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不顾历史背景、仅仅按照字面意义移植盎格鲁保守主义,产生的后果大概恰恰是保守的反面。亚当斯家族将日耳曼自由主义视为盟友,其实跟杰斐逊将法国激进主义视为盟友差不多:符合当时美国国内政争的理论需要,但不能掩盖双方在思想史脉络上的重大分歧。它们不久就产生了面目迥异的思想后裔。
欧洲保守派的背景不同于盎格鲁新教徒,天主教会和正统绝对君主制为根基。在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当中,新教徒和改信新教的犹太人占据了畸高的比例。盎格鲁世界用于巩固即成体制的教义,在他们手中往往只是一种打击天主教多数派的武器。如果将“自由主义者”改成“普鲁士王国”、将“天主教正统派”改成“哈布斯堡帝国”,以上陈述就可以适用于从哈登堡到俾斯麦时代的普奥关系。日耳曼自由主义与普鲁士的诡异情缘就建立在这种歌德式“选择亲和力”上,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单相思体现了这种关系的最高峰。最后,自由主义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太子的影子内阁一起没落;将德语世界留作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场。这条路径打开了战争和革命的大门,最终毁灭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
在法国革命最初的蜜月期,以下的蓝图似乎并非不可能实现:将霍亨索伦王朝改造为德语世界的奥兰治家族,实现(北德)新教徒与自由主义的英国式合流,让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保守派落到斯图亚特王朝的下场。这种希望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普遍,艾克曼和海涅都对此念兹在兹。他们一再欺骗自己,将普鲁士王国的每一次变法解释为自由主义;但这些改革最终全都演变为强化国家主义的举措。耶拿战败后的改革部分实现了教育世俗化,但主要结果是军事动员体系和文官制度的合理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劝进计划由俾斯麦付诸实施,但前提是毁灭“国会通过财政控制权主宰国家”的英国式路径。1880年代的法律改革起步太晚、先天不合时宜,在民族法学和福利国家的两面夹击之下粉身碎骨。威廉二世登基时,形势已经很明朗:政权属于国家主义,民间属于社会主义。同样,国家主义各党和社会主义各党占据魏玛共和国的大半壁江山,自由主义各党势力还不如天主教和少数民族的党派。希特勒将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怪胎中,结束了这场游戏、证明日耳曼自由主义只有依靠外力才有可能胜利。
弗雷德里克·根兹是法国胡格诺派流亡者的后裔,依靠新教的普鲁士保护。门第背景对政治选择的影响之大,往往超乎当事人和后世史论家愿意承认的程度。根兹虽然在柯尼斯堡上过康德的课,但他的教育底色仍然属于洛可可时代。按塔列朗亲王的经典论述,他属于体验过“生活甜蜜”的最后一代人。他们属于旧制度,游历、交际、寻欢作乐才是他们真正的教育。君子不器。严肃地对待抽象理论和书本知识,那是“布尔乔亚世纪”优等生的做法;暴露了小市民的出身和眼界。绅士即使涉猎群书,也仅仅是为了培养品味、并不尊重学究意义上的知识。他们在精英小圈子内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通过经验理解各邦活的宪制运作、而非纸上的死宪法。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宪制本身。圣西门公爵说:全法兰西都在国王的客厅里,就是这个意思。对他们而言,自由权利就是柏克所谓“欧洲共同的古法”—-封建意义上的自由、各等级共治的传统惯例。
根据这种自由观,法兰西和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侵犯了各等级古老的特权。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并不是通向民主的不彻底革命,而是针对新兴绝对君主制的拨乱反正:恢复各等级共治的混合宪制。大不列颠国王和上下两院完美地体现了混合宪制的平衡。根兹写道:
“在混合宪制内,最高权力或合法主权者总是由几个部分联合组成、由宪法规范。每一部分各有其宪法权利与特权;即使自身更加重要,都不可能比其他部分更为神圣。一旦其中某一部分逾越合法边界,压迫或企图毁灭另一部分;除非宪法只是空洞的名义、后者必定有权抵抗,除非另有幸运的权宜手段、战争无法避免。如果原有的平衡不能恢复,宪制解体就是争执必然、合法的结局。一国最高权力的两个独立组成部分起衅,正如两个邦国开战;不可能存在仲裁法官。不言而喻,这是整个邦国最不幸的情况。毫无疑问,最可怕的处境势必随之而来:在这种争执当中,国民永远不知道应该服从谁、抵抗谁、拥戴谁、反对谁。一切权利和义务都陷于混乱、地位不清。谁在叛乱一方,谁不在叛乱一方;本身就难以确定。这是混合政体不可避免的害处。无论政体多么伟大;出于宪制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例如:不列颠国会两院企图不经国王批准,颁布法律;或是国王未经国会同意,颁布法律。这样,受害的一方无疑会抵抗、积极有力地抵抗。即使这种抵抗以内战和宪制毁灭为结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其合法性毫无瑕纰。
无疑,这是混合政体最大的弱点。不过,幸运的是:政体接近完美状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解体的可能性。宪法权威的一部分由于自身有适当的分量,能够抵抗另一部分的侵凌;可能性更大。某一部分迫于无奈,拿起武器;可能性更小。在这方面,人们有正当理由地断定:英国宪制相对于任何其他曾经存在过、或可能设计出的复合政体,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因此,法兰西如果恢复古老的三级会议、将绝对君主制的武断权力收回等级君主制的有限范围内;无疑值得庆幸。但是,法国第三等级“不到六星期,他们就已经破坏了这三项基本条件。第三等级代表没有获得丝毫授权;就可耻地践踏了其他等级的权利,宣布他们自己单独构成国民议会。”
这不是混合政体的复辟,而是以另一种绝对权力(人民主权)取代原先的绝对权力(朕即国家)。而且两相比较,前者对权利的破坏远远超过后者。
一旦越过这个阶段,根兹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就由康德式同情转为柏克式反对。他第一个(1794年)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翻译成德文。1795年以后,他在柏林出版的《历史研究》月刊可以概括为:根据“老辉格党”史观解读并宣扬英国宪制的奥妙。《美法革命对照论》(1800)就属于《历史研究》系列文章,其主旨在于:美国革命不是法国革命的先驱,而是英国宪法的复辟。(这也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观点。)他的假想敌无疑是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后者愿意依靠法军推翻本国政府。约翰·昆西·亚当斯刻不容缓地将这篇文章介绍到美国,无疑是针对1800年大选的对手: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
在此期间,根兹不仅通过文字宣扬保守自由主义理念、而且直接向普鲁士政府提出改革建议。1797年,他上书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要求保障贸易自由和出版自由。这种出格的举动对他的仕途没有好处,却为他赢得了相当大的公众声望。
1801年,根兹厌倦了定期出版《历史研究》杂志;但他鼓吹英国宪制的热情不减,发表了另一篇公认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的产生和特征》。这些活动不仅为他赢得了收入和声誉,还确定了他在现实政治中的角色。他作为法国革命公开和积极的敌人,难以在中立的普鲁士获致要津、转而投奔英奥联盟。
1802年,根兹受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斯塔迪安伯爵引荐;前往维也纳,就任帝国枢密。他途经伦敦、会晤英国重臣庇特和格兰维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政府意识到他的笔杆子可以为反法联盟做出极大贡献,从此为他支付丰厚的年金。奥地利大败后,根兹撰写了两篇新论文《英格兰和西班牙两强开战前的关系》、《欧洲势力均衡的碎片》(1806)。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以先知式的热情预言:“欧洲通过日耳曼毁灭,也将通过日耳曼复兴。”这时,他极力促成普鲁士放弃中立、加入英奥联盟。拿破仑愤怒地说:“无行文人图财卖身,根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耶拿大败再度粉碎了根兹的希望。
1809年,奥地利再度向法国开战、不旋踵而败。1810年,根兹的政治保护人斯塔迪安伯爵倒台;他联袂辞职。梅特涅亲王继任后,根兹再度出任帝国顾问。莫斯科和滑铁卢似乎实现了根兹的外交理想,他却偏偏在这时向梅特涅建议:维持拿破仑的地位,以法奥联盟保障欧洲均衡。前一项建议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梅特涅和格雷在维也纳和会上奉行的宗旨确实是:避免过分削弱战败国法国、避免过分加强战胜国俄罗斯,在欧洲维持五大国势力均衡、在海外听任英国所向披靡。这一体系给欧洲带来了近代最长久的和平,证明根兹作为外交家确有独到的眼光。
从1812年维也纳会议到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兹一直担任梅特涅的助手、身居欧洲政治的中心。他在毕生事业的顶峰,内心却充满了玩世不恭的绝望情绪、完全丧失了早年先知般的热情和严正的道德感。从他留下的片断纪录看,他似乎经历太多、了解太多,以致于看透了人性和时代;相信身逢叔世、事无可为,唯有延缓断壁残垣的进一步颓坏而已。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上,他接受了塔列朗亲王和卡斯尔雷勋爵馈赠的巨款。在1819年维也纳会议上,他漠然抛弃了自己十几年前不顾利害鼓吹的日耳曼再联合。在《卡尔斯巴德法令》中,他断然否定了自己1797年上书力争的言论自由。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与妻子分居,充满了天主教各国常见、新教各国少见、美国新教徒社会中尤其罕见的风流韵事。
1832年6月,根兹在维也纳去世。这时,他的日记和文稿仍然是堪与柏克媲美的杰作;但约翰·昆西·亚当斯或美国任何党派都不可能将他引为同道了。或许,在没有自由主义历史基础的地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只能是一批自由主义理论鉴赏家。他们是无根的游士、精神上的异邦人;既然有足够的智力理解精微复杂的盎格鲁宪制理论,必然就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自己的地位、利益与自己的爱好、倾向早晚不能相容。这种分裂自然会造就玩世不恭的态度和道德相对主义,鄙视自己、同胞和人类本身。俄罗斯的纳博科夫、卢金,日本的币原重喜郎在这方面与根兹非常相似。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样,无法具备盎格鲁世界作为自由基础的信仰、道德、社会责任感;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他们注定是知识世界的孤星、历史世界的流星、政治世界的装饰品。
流星一批接一批掠过中欧晦暗的天空,一次又一次照亮另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但日耳曼民族浑然不觉,一步步穿过小径分叉的花园、走向自己的命运。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