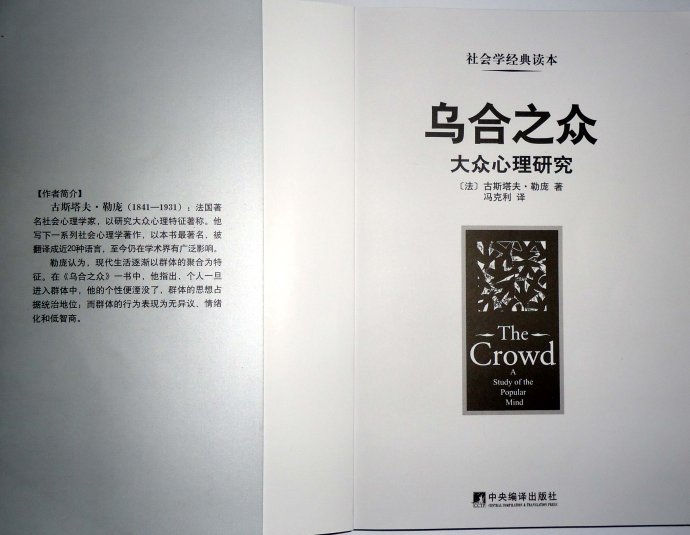——读《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西斯群众心理学》
 这是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是法国人勒邦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另一本是奥地利人威尔海姆·赖希著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前者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分析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中作为主体参与的群众,他们的行为、心理的诸般特征,更多具有现象学意义。后者则以希特勒纳粹时代为背景,兼及苏联斯大林时期,探索极权制度中在谎言和恐惧状态下生存的普通群众性格心理法西斯化过程呈现的非理性性质,并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生物性缘由,更多具有社会哲学价值。两本书各有精义秘笈之处,却又互印连类而学理相通,都具有实证研究之价值。
这是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是法国人勒邦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另一本是奥地利人威尔海姆·赖希著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前者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分析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中作为主体参与的群众,他们的行为、心理的诸般特征,更多具有现象学意义。后者则以希特勒纳粹时代为背景,兼及苏联斯大林时期,探索极权制度中在谎言和恐惧状态下生存的普通群众性格心理法西斯化过程呈现的非理性性质,并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生物性缘由,更多具有社会哲学价值。两本书各有精义秘笈之处,却又互印连类而学理相通,都具有实证研究之价值。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理智与情感、思想与灵魂、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交替纠结在一起,支配着人的行为。现代心理学有一“情商”之说,认为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灵魂等力量大于聪明、才智的“智商”的力量。性格即命运,优劣成败的人生例子,我们不难于现实生活中找到。昆德拉写过一本叫《生活在别处》的有名小说,描述一个抒情浪漫的青年诗人人生追求,最后却沦为向警察告密的告密者。昆德拉思考的是浪漫主义与专制政治隐秘的情感联系。他说道:“抒情状态是人类的境况。”这就是说,不仅是浪漫之情,而且追求的激情、豪情、失败痛苦的悲情,乃至怨恨愤怒之情、七情六欲,都是人类的宿命。它们竟支配人生的始终。
“情商”重于“智商”的现象,不仅于个体,人类群体概莫能外。不管是阅读历史书本,还是从现实生活之经验观察,凡有群体行为发生之处,特别是事关重大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莫不是场面汹汹。激烈的冲动、狂热的感情,有如泛滥的洪水、狂奔的野马,那种情绪压倒理智、盲目冲动代替思考的状态,被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兽性的上层建筑”。对此无理性局面以及造成的恶果,凡经历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小政治运动或“文革”的国人,恐怕莫不有深刻的记忆、切身的体会。
集体无意识,是群体行为发生时的基本心理状态,勒邦在其书中对此有着透辟的论述。他甚至说:“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这里的“无意识”指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勒邦在书中举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论述了群众行为的这种心理特征。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因此,勒邦认为,参与社会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真率、冲动易变、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在人群中迅疾传染蔓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所谓“谋杀无动机”(昆德拉语),就是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
群体行为还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地位,因为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大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群众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中也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还是希特勒的讲演、斯大林的检阅等,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
勒邦在书中说道:“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翻开历史书籍,这种出身江湖、强人领袖成功夺取社稷重器的例子遍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这类群众领袖的高明不仅在于他们擅长谋略权术,还在于擅用巧妙的宣传和演说把自己打扮神化成伟人救星、明主英雄,窃取国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让他们相信为其谋利,相信其幸福与快乐在于崇拜与服从之中,役使他们赴死就义,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群众中有无智者?群众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受欺骗?他们在为人驱使被利用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为什么不知道自身的行为常与其利益相背离?这岂止一句“愚昧”、“糊涂”说得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个体意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这些,两本书的作者都有解读。勒邦认为,群众意识有“趋同一致律”,即在特定事件群众集结、情感亢奋昂扬的场面中,个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灭,会不自觉地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即使平时独处冷静清醒的佼佼者,一旦汇入群体,个人都会被感性所支配,被群体所裹挟,意识趋于群众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受过教育的绅士和伙夫修鞋匠的心理意识并无多大差别。再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的个人会卸去责任感,有一种冲破压抑、胆大包天、罚不责众的快感。这种快感又被英国哲学家罗素解释为权力感。罗素在其《权力论》中说道:“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群众有一种热情和安全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下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集体兴奋是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甚至自我保护很容易被遗忘。这时候,残忍的屠杀和英勇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就是当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处支配地位时,集体无意识力量异常强大,很少有个人能与之抗衡的原因。除此而外,人类群体的盲目趋同现象,犹如原野上生存奔跑的马群或牛群,恐怕还有祖先遗传的动物本能,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心理和行为。
和勒邦从现象层面研究不同,赖希在他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一书里,是从人的性格结构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分三个层次。第一层为表层,表现为含蓄、有礼、有同情心、讲道德、负责任,但多是虚伪的。第二层为中层,表现为残忍、贪婪、好色、嫉妒、虐待狂。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原始生物欲望的派生物,所谓“无意识”正在于此。第三层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善意、勤奋、合作。深层性格是人自然健康的基础,产生“力比多”冲动。但“力比多”经过第二层便扭曲为反常。第一层相对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文明教化、道德理想精神。第二层表现于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精神”。第三层是文化艺术、科学创造的源头。赖希指出,这是人身上的怪物,脱掉修养的外衣,最先显露的便是人这种反常的性格。而小人精神来自人的情感欲望,是一种既渴望威权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就是在许许多多群众运动、造反的过程中,千百万群众个体表现出来的性格。
赖希认为,正是这人身上的怪物、小人精神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内核。而且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素,法西斯主义是普通人性格结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当时为什么得到德国人民普遍拥戴的原因了。
他指出:“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意识、纲领与广大个体的心理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法西斯主义,不能将其看做一个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行为,也不能仅当成德国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它渗透到人类所有民族的有机体中,是被压抑的卑微者既反抗又崇拜强权的一种基本情感态度。赖希于七十年前在他的书中表述的这一观点,不幸被后来发生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小战争、屠杀、暴行所证实。从奥斯威辛的焚尸炉到斯大林时期的清剿运动,从科索沃、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到巴以冲突,直至当今频繁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的事件,这些群体行为大规模的发生,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地理的直接原因外,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寻找一下人类自身的缘由吗﹖对此,一位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家洛伦兹曾经有一精辟论述:“人的行为,尤其是集团、国家、阶级、民族间的争斗行为,绝不单由理念、文化传统或利益所决定,它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那就是动物性法则。”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普遍发生的杀人强奸等侵犯他人的暴力行为,虽属少数人犯罪,但探索其性格的深层因素,一定具有恃强凌弱、侵害他人的兽性心理,满足于随意处置他人的权欲性快感。就是在普通人中,那种崇尚威权,以暴力残酷为壮伟磅礴,并为之叫好的荒谬心理例子也随处可见。远的不说,请看看“基地”组织制造的纽约“9·11”、西班牙“3·11”弥天惨案吧,就可想而知。基地组织屠杀成百上千生灵后,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多国人同胞特别是青年人竟然为恐怖主义的拉登叫好,称其为反美反帝斗士。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欢呼者心里装的是国家至上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无视那些无辜死伤的几千人生命的权利,肆无忌惮的语言暴力则表现出的是一种嗜血的快感和心理。太多的事实告诉人们:法西斯精神普遍深植于人的动物性中。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巧妙的伎俩雄辩演说,来迎合众人浅薄心理,慑服人心为要术,是领袖人物、群众操控者的基本手段。其实他们并非需要掌握什么了不得的理论,只要用一些具有煽动性标语口号或诗一般的语言,开动其控制的宣传机器长久反复的灌输,调动群众的情绪或欲望,便会达到统率思想征服民众的目的。希特勒一再强调,不能靠论证、证据和知识来赢得群众,只能靠感情和信仰。总之,舆论宣传于一切独裁统治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针政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纳粹的歌曲就这样唱道:
我们是党徽的军队
高举着红旗
为了德国的工人
我们铺设通向自由的道路
希特勒讲演时说道:
“……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在旗帜上看到了纲领,看到了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党徽中看到了为雅利安人斗争的使命,同样看到了创造性劳动观念的胜利。这一胜利一直并且永远是反犹太人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可再看看1935年3月19日苏联《真理报》一篇题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文章的摘要:
苏维埃爱国主义——对自己祖国无限的爱无条件的忠诚的炽热感情,对祖国命运最深刻的责任感,在我们心中奔腾。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里,人民的利益和祖国及其政府的利益不可分。苏维埃爱国主义激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苏维埃党的领导下,人民塑造自己的生活。只有现在,我们美丽富饶的祖国才向劳动人民敞开。
别小看这些语无伦次大言不惭的口号、毫无实质性内容的豪言壮语,它虽然和一个人对自己祖国与民族真正自然热爱的感情丝毫无关,但当其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时,会流行传染成一场政治性情感瘟疫,具有“无意识”的巨大力量。这便是宣传造势的秘密。精神分析学中有“自居作用”之说,即一个人感到和另一个人的观念、信仰等一致时,便采取这个人的态度,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赖希先生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大量宣传内容和方式进行考察研究后,揭示出正是这种“自居作用”构成了群众心理的现实基础,即个人越觉得无能、越卑微,就越需要崇拜威权;越感到自身无价值,就越需要移情于集体和大人物,把自身等同于民族的伟大、国家的荣誉,等同于领袖的崇高。当时的德国人民对国家、元首、政府拥戴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我就是国家、民族、权威,甚至每一个德国人在潜意识里都自认为是小希特勒。元首的思想就成为德国人的思想,纳粹党的意志就是德国人的意志。这种心理感觉上的置换,潜意识的移情,效果可谓巨大而显著。“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鲁迅),这种“小人精神”,自卑与自大的非理性情感混合物,正是法西斯民族主义的心理土壤。本来民族情感应该有正常与非正常之分,热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正常的感情;而无限崇奉本民族的一切,导致歇斯底里地排外、扩张却是一种非理性的原始感情。并且它往往是被诱导、操纵的结果。这种非理性的原始情感使人个性泯灭,失去正常思考能力,易沦为野心家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赖希与勒邦在其研究群众心理的书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群众是无意识的,他们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如果一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非理性,也会使群众的性格结构成为非理性状态。这不但被法国、德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独裁国家统治的现实所证实,而且正在被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战争和暴力与恐怖主义行为所印证。独裁与专制、战争与暴力是人类的毒瘤,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非理性行为。被这种情形笼罩下的民众容易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国之邦的蚁民或子民。勒邦与赖希这两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著作,其实际意义就在于唤醒每一个普通人,警惕自身,认识自己,拒绝为野心家和反动势力所利用,保持我们的公民人格,做一个清醒的自由人。
赖希与勒邦在其研究群众心理的书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群众是无意识的,他们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如果一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非理性,也会使群众的性格结构成为非理性状态。这不但被法国、德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独裁国家统治的现实所证实,而且正在被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战争和暴力与恐怖主义行为所印证。独裁与专制、战争与暴力是人类的毒瘤,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非理性行为。被这种情形笼罩下的民众容易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国之邦的蚁民或子民。勒邦与赖希这两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著作,其实际意义就在于唤醒每一个普通人,警惕自身,认识自己,拒绝为野心家和反动势力所利用,保持我们的公民人格,做一个清醒的自由人。
(〔法〕古斯塔夫·勒邦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奥〕威尔海姆·赖希著:《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来源:《书屋》二〇〇四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