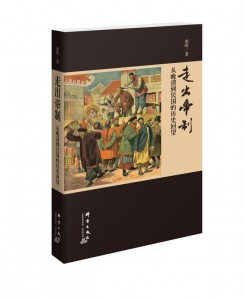个人的成长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秦晖教授《走出帝制》一书的主题即如书名所提示的,是从帝制走向民主共和。根据秦晖的自述,他思考问题的视野是“三千年大变局”:中国历史的三千年中有两个变革的节点,一是从周制(可简单理解为周代制度,重点是周天子乃“虚君”——编者按)走向秦制,一是走出秦制,实现民主共和。书中广泛涉及近代史的一些关键问题:革命与改良、共和与立宪、西化与现代化、救亡与启蒙、儒与法的传统、中学与西学、殖民与独立(站起来)、“日本式自由主义”、西方“正版的自由主义”与“俄国式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现代史的宏大问题,统括在“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名下。从秦晖一贯重视制度因素、强调传统社会的法家影响和秦制特征、批评新文化运动全力批儒而放过法家的失误的论述中,也多少可以窥见他所把握的“近代史脉搏”,就是从帝制(秦制)走向共和这一主线。
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走出秦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我的疑问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是不是可以归结为“走出帝制”?或走出秦制是现代化的主线或基本坐标吗?本书引发我们去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或者背景是什么?怎么来估价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它能否归结为“帝制”(秦制)?或者秦制是否其最关键的特征?以此相应的,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走向目标的途径是什么?走出秦制是否其核心内容?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依次要经过哪些历史阶梯或逻辑环节?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评价标准或坐标系,用以评价近代史上的事件和行为,确定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从比较政治的世界性视野来看,非西方国家走出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虽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途径和模式,但是最基本的逻辑环节是不能跳跃的,而只有把握住现代化进程深处内在的真实脉搏,才能够准确辨析和评价其进程中的各个逻辑的和历史的环节。
人的现代化应为“走出帝制”基本坐标
秦晖是以从秦制走向民主共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坐标的,而我以为,应该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包括:其一,个人意识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个人挣脱传统共同体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其二,独立的个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得到平等的地位、较大的自由空间,获得人的尊严;其三,个人在政治法律领域里获得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保障,成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公共事务;其四,其现代政治人格发育成熟。在现代化进程中,上述各项虽然会有可能交叉重叠,但大体上是如上所列先后顺序展开的。它们构成现代化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环节,由这些环节形成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链条或时序。
这样说来,个人的成长才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真正主线。个人的萌发、成长和成熟,个人从传统的共同体当中独立和解放出来,而后进一步成长为现代的个体,这是衡量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坐标。与此相对应,共同体由不同形式的天然的血缘共同体和各种准天然的或类天然的共同体演变为人为的共同体,即以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为基础的、以契约为纽带的现代共同体。个人的成长推动共同体的变化,不同的共同体又对个人的成长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在变。这是人类进步的主线,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即人的现代化。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逻辑的。
秦晖也注意到了这个线索,在本书的最后三章谈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仅仅是将其作为现代化的一条辅线来处理的。因为主线是从秦制到民主共和,所以,制度变革就成为焦点。这样的认识定下了他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基调:在批儒的同时,更应该批法(家);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日本式的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误区,应该引进西方的针对大共同体(国家)的个人主义,即具有政治法律内涵的自由主义。
由日本式的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走向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这之间没有多大障碍,甚至是水到渠成。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是要走出周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日本式的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而是西方正宗的针对大共同体(国家)的个人主义。出于这样的判断,秦晖甚至把从日本引来的个人主义称为“伪个人主义”,将其与西方的“原版的个人主义”对立起来。
对两种个人主义历史逻辑的误解
秦晖对两种个人主义的区分非常有价值。在我有限的视野里,还没有发现西方学者对这两种个人主义的区分作出过清晰而系统的阐述。包含于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西方个人主义,是针对国家及其权力的。它将个人从国家权力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自由和平等。它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抵御国家权力的侵犯,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西方没有哪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明确地将这种个人主义与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或在西方语境下针对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贡斯当虽然讲过两种自由,但他所说的个人自由仍然是针对国家的。哈耶克批判过德国传统中的“对不同的、有差别的个性的狂热崇拜”的“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是针对社会惯例和习俗的,不是针对国家之外的小共同体的。
秦晖对两种个人主义的区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最初大声疾呼个人解放的思想家,很快便向权力皈依,投入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怀抱;为什么以个性解放为开端的历史进程,合乎逻辑地走向整体主义的轨道。个人主义能够与整体主义实现对接,是因为这种个人主义是针对小共同体的,而整体主义则是针对大共同体的。
不过,秦晖把从日本引进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或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思想家们高扬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视为一个误区,我以为,是对两种个人主义历史逻辑关系的误解。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变”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两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西方的情形和中国有所不同。希腊罗马略去不说,到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是多元的。由于这种多元性,人们对国家家族的依附被削弱了。
中国主要是两极,一极是小共同体家族,一极是大共同体国家。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一个忠,一个孝,对应的就是这两个共同体。但在西欧,与国家并列的还有教会。人们对教会的认同感或依附超过国家。此外,在世俗社会生活领域里,除家庭或家族外,还有庄园(领主)、城市、行会等其他类型的共同体。
抛开基督教因素,可以说,中世纪西欧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情况比较接近。但问题是,正是基督教,赋予西方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关键的特征。教会首先是一个世俗结构,它包揽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控制了在中国属于世俗生活的广阔领域。与此同时,基督教信仰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基督徒精神共同体,每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灵性的存在,成为其独立平等的一员,每个人只依附于上帝。于是,人的个体化在精神领域里得到了实现。这样一种信仰和宗教生活,削弱了西方人对各种世俗共同体——无论大共同体还是小共同体——的依附和认同。
无论西方、中国还是日本,现代人的出现,最初都是从传统的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但却不是从秦晖所讲的大共同体即国家中独立出来。
“娜拉出走”后投入国家怀抱,合乎逻辑
秦晖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错在直接从日本学来了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虽然,它使中国人个人意识萌发,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个人幸福,比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但是,最初觉醒的个人主要针对家庭和家族,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则集中批儒。接下来,这样的觉醒的个体自然会投入到国家的怀抱,走向整体主义。在秦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是秦制,对人的最大压迫也是秦制。日本没有秦制,家族也不如中国发达,所以个人解放主要针对贵族(藩主);而中国没有周制,个人解放应该针对秦制才对。在思想理论领域,应该集中批法家,而不是批儒家。
我以为,秦晖在这里忽略或误解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个体获得独立解放的时序,亦即现代人觉醒和成长的历史逻辑。他认为,个人觉醒一定首先会针对压迫他最严重、危害他最大的那个共同体,在中国即实行秦制的国家。这个判断不符合历史。个人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不是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算计过程。这种判断还忽略了个人觉醒的最初内容是什么。个人萌发、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个性伸展的欲求之后,首先面对的一定是直接束缚他的个性、管制他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最切近的共同体,而国家较为遥远和抽象,初步觉醒的个人开始并不会与它发生普遍而深刻的冲突。个人走向独立最初产生的欲求、情感和态度,无非是想伸展一下个性,在某些生活领域里实现自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欲求主要受到社会习俗的束缚和压制,而小共同体则是社会习俗的守护者。所以,觉醒的个人最初主要与小共同体发生冲突。个人最初为了从天然的小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与其权威相对抗,就要求助和依附于更大的、更遥远的、部分地属于人为的虚拟共同体,就是国家,还可以是民族、人民等等。所以,现代人最初主要与小共同体发生冲突,而从小共同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将其情感投注于作为大共同体象征性代表的国王(西欧)、天皇(日本)和领袖(中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娜拉出走了,摆脱了夫权、父权、族权,却投入国家或领袖的怀抱,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在这个阶段,他还不具有真正独立、成熟的政治人格,他必须寻找一个坚实的依靠。没有秦制,也要创造出一个秦制来。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现代化就处在这个阶段,那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们,表达的正是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解放要求。所以,从日本引来的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并非失误,而是个人解放成长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步,也是思想进步合乎逻辑的一个环节。
其实,西方个人解放的初期也没有秦制。个人迈出第一步时,针对的主要是教会,试图从教会的束缚下获得解放。这就是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时期现代化的主题。与日本和中国一样,最初从教会里面解放出来的个人,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自主的人,也投入到了民族国家和王权的怀抱。当然,如果仔细说来,西方社会个人解放是多元的渠道,比如农奴成了自由农民,摆脱了原来对庄园主、领主的人身依附。城市兴起是另一种渠道,农奴成为市民。不过,西方人从这些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最初结果,也是转而依附于民族国家,依附于王权,因为刚解放出来的个人仍然是软弱的,他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同时他也有一种精神的或心理的需求,要在更大的共同体中找到归宿,获得坚实的依靠。西方人又经过了二三百年,进一步成长起来的个人才开始感受到国家压迫的难以忍受,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才突显出来,人们才开始要求政治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和自由,针对国家的个人主义才开始出现。
那么,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出现了以变革秦制为目标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呢?如秦晖所强调的,早在19世纪,一大批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包括徐继畲、薛福成、张树声、郭嵩焘、洪仁玕、谭嗣同等,就已经表达了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羡慕,呼吁在中国实行国家制度的变革了。到了新文化运动反倒绻缩到个性的解放,不正是受到日本人的误导而走了弯路或出现了倒退吗?不正好证明,从个性自由到政治自由的历史时序不存在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追问,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改革国家制度的要求和行为,是否出于“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引进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主要是出于对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团结、凝聚民心和国力强盛等社会效果的羡慕,或如秦晖所指出的,是被西方制度与古典文献中所谓三代盛世的天下为公、国无苛政、民风纯良的相似性所吸引,于是以古儒传统接引西方制度。他们推崇民主,并非个人产生了平等意识和参与要求,更不是出于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引进民主共和,仍然是少数有国家关怀的精英从社会整体需要出发做出的选择,而并非由于随着个人的成长产生的权利要求与当时的秦制发生了普遍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这种民主共和诉求缺少坚固的根基,民主运动也只能流于表面形式的模仿,缺少来自社会深层和个体内在的动力。这一点,也可以参照美国黑人和西方妇女获得政治权利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是国人“站起来”的第一次努力
这样看来,秦晖这本书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把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觉醒、成长和走向成熟的过程梳理出来,这是走出帝制或走向现代的最扎实的步伐。
秦晖在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贡献。“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讲的是中国人作为整体的独立解放,而不是个体的独立解放。个人的独立、成长和走向成熟,这个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维度,在这里也被秦晖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怎样才算站起来了?他的个性得到解放和充分的伸展,形成独立的成熟的政治人格,他的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作为国家的主人,他有权充分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这样才算站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站起来”的第一次努力——摆脱小共同体站起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重新开始了个人解放的历程,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比起新文化运动,个性的解放无疑更加广泛和深化了。今天的中国,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快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社会已经相当开放,人们也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个人生活不但很现代,甚至有浓浓的后现代意味了。这样的进步花了近百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百年前的国人会理解针对国家的个人主义并与其产生共鸣。
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在西方也没有一种政治哲学来表达。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宗教神学思想当中。它是个人觉醒的第一阶段,也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从小共同体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进一步成长,就会感受到国家对他的束缚、压迫和侵犯,他就要站起来维护他的权利和尊严,对国家权力提出他的要求,也就是走向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秦晖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过程,还需要再对人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一个梳理,从清末到民国,在这个路线上,我们获得了哪些进步,还有什么未竟之业?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28日B03-04,转载授权联系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