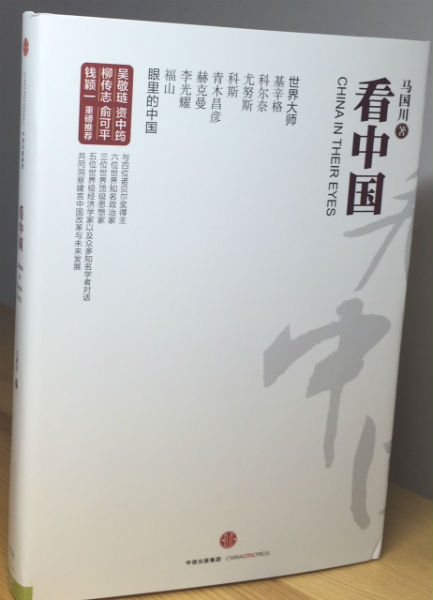摘要
越战期间,一美国男子每晚都点著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一个雨夜,他还是拿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著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他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看中国》后记
【本文刊于《书屋》杂志2016年第2期,此为作者赐稿。】
一
故事发生在波兰。
上个世纪前半叶,腐败弥漫着整个国度,人们陷入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这时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贩卖“穆尔提-丙药丸”的猎鹰人。蒙古哲学家穆尔提-丙发明的这种药丸,能够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人们只要服用了它,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而且认为以前辩论的问题没有意义。他们自认为是健康人,把那些质疑者视为疯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它来自小说《永不满足》的虚构,作者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从西部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红军从东部侵入波兰,同一天这位作家割腕自杀。
十多年后,这部作品触动了另一位波兰作家米沃什。他观察苏联支持下建立的新政权下的社会生态,借用“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人们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喜气洋洋,从此不再开口[1]。
中国作家王小波也讲述过另外一个故事: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个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2]。
如果说花剌子模的主角是君王的话,那么“穆尔提-丙药丸”的主角则是民众。有没有两种奇葩并存的国度呢?清朝末年似乎就是。
作为统治者,晚清的君主头脑僵滞,闭目塞听,拒绝和敌视新生事物。虽然社会上不乏个别“睁眼看世界”的社会精英,但不是被贬官(郭嵩焘),就是被流放(林则徐),不是被通缉(梁启超),就是被杀头(谭嗣同)。绝大多数民众安于现状,万马齐喑。整个王朝就像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一样,上下恬嬉。
虽然能够营造天下太平、盛世辉煌的一时假象,但是闭目塞听的结果,不管是小说里的波兰,古代传说里的花剌子模,还是大清王朝,最后都被消灭或推翻,徒留笑柄。
不过,“穆尔提-丙药丸”会消失吗?未必。
二
2009年底,我和一位朋友发生了争论。
他说,经济高速增长连续三十多年,“中国奇迹”无可怀疑。中国正在开辟一条崭新的现代转型道路,“中国道路”一定会成功。
我的朋友并非投机者,他是被现实说服了。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似乎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盛世论”悄然流行。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凭借海量投资,强力拉动和刺激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中国奇迹”、“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成为流行话题。一些知识分子动摇了。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参与到“盛世”的大合唱中。舆论汹涌,似乎“盛世”真的降临了。
我则对此表示怀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权力腐败、贫富差距也使世人震惊,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吴敬琏先生把这种光明与黑暗并存的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认为“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两条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3]
我和朋友间的争论没有结果。最后,他说,你们这些人只是极少数,改变不了什么。我对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越战期间,一美国男子每晚都点著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一个雨夜,他还是拿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著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他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其实,一些前辈学者一直“拿蜡烛站在那里”。吴敬琏、资中筠、江平等先生直面现实,揭示和讨论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他们虽然遭到质疑和抨击,甚至被造谣和谩骂,却不改初衷,直言无讳。不过,坚持说真话的确实只是极少数。在常识缺乏的时代里,这些先生们的身影显得孤独。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4]可是,现在许多“牛虻”变成了为权力唱赞歌、“百啭度高枝”的“流莺”。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转型,都要经历艰难的过程,中国尤其如此。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前,由于缺乏宗教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无处安放,于是整个社会都处于躁动和焦虑之中。一些人动辄贬斥“西方那一套”,不吝辞藻地赞美“风景这边独好”,卖力地兜售“穆尔提-丙药丸”。显然,“穆尔提-丙药丸”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因为它能够让人们获得安详和幸福,满足于现状。
三
资中筠先生曾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5]
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国家气质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最令人担忧的是,一种自我排斥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氛围逐渐蔓延开来。
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进步,得益于改革开放。其实,“开放”比“改革”更重要,因为只有打开国门,思想解放,才能清楚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开放为改革提供动力,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环境里,改革无从谈起。假如中国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那么改革必然失去动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可能中断。
我特别服膺周有光先生的一句名言,“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确实,只要站在世界看中国,“登高壮观天地间”,就会发现中国并不独特。在世界历史上,在几十年间迅速崛起的国家并非个例。
诚如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所说,“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6]
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难题。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以世界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才能准确认识到中国未来的道路。
因此,2009年以来,我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世界,先后采访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人士,其中有世界级的政治家、大师级的思想家,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著名人士。采访的话题涵盖了中国模式、经济社会转型、未来改革等重大问题。这些人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开阔视野,发人深省。
出版社要将这些采访文字结集出版。一开始我很犹豫,后来在编辑过程中重读旧文,发现话题远未过时,许多观点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在这些文章里获得某些启迪、引起深思。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冀望,就是试图以此引入国际视角“看中国”,破除那些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做法。
文稿编辑完了,已是北京深秋时节。乘兴登上香山之顶,遥望不见北京,雾霾深重。近看满山秋叶,由绿转黄。突然想起一个源自印度的故事——
昔日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7]
2015年10月 于北京

[1] 《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2] 《思维的乐趣》,王小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3] 《重启改革议程》,吴敬琏、马国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
[4] 柏拉图《申辩篇》,转引自《风声·雨声·读书声》,朱学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9月第1版
[5] 《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资中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6] 唐世平《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刊于2015年第3期《南风窗》
6.转引自《人权论集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