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香港民族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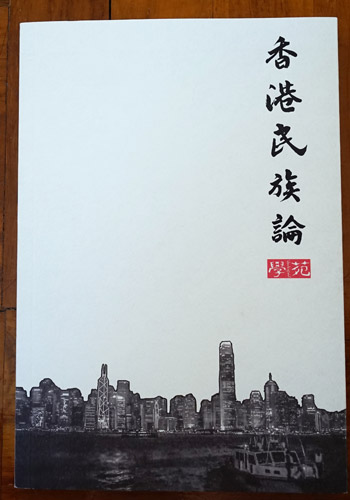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刊《学苑》杂志发表了四篇主题爲“香港民族,命运自决”的文章,一时间宛如“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发种种争议,北京方面自然是恨之入骨,北京的傀儡梁振英更是口诛笔伐。然而,那些让中共及其走卒惊慌失措的思想,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思想。随即,《学苑》的编辑们又约香港、台湾和北美的五位华人学者和评论员撰写同一主题的论文,将九篇重量级的文章结集成《香港民族论》一书出版。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刊《学苑》杂志发表了四篇主题爲“香港民族,命运自决”的文章,一时间宛如“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发种种争议,北京方面自然是恨之入骨,北京的傀儡梁振英更是口诛笔伐。然而,那些让中共及其走卒惊慌失措的思想,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思想。随即,《学苑》的编辑们又约香港、台湾和北美的五位华人学者和评论员撰写同一主题的论文,将九篇重量级的文章结集成《香港民族论》一书出版。
本书撰稿人之一的徐承恩在《香港本土意识简史》一文中,特别提及二零一三年发生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的口号之争。支联会计划以“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作为口号,不料许多年轻人对此不满。他们认为,香港人纪念六四,不是认同大中华的国家观念,而是出于普世关怀而支援邻近国家的民主运动。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支持香港年轻人的观点,却遭到支联会常委徐汉光的辱骂。后来,支联会在舆论压力之下,向丁子霖道歉,并修改了原来的口号。
这一事件爲香港民主运动抹上了一道伤痕,更标识着香港民主运动的接力棒已经由老一辈认同“民主回归”的泛民阵营转移到具有明确的本土意识的年轻一代手上。香港的年轻一代不是不愿关心六四,而是不愿继续被动地“爱国”,他们要站在普世人权价值的高度上关心六四。所以,关心六四与关怀本土是可以兼容的。
任何一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都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压力。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香港,儘管民主特别是选举方面相对滞后,但伦敦基本上按照法治和自由的原则治理这个比英国本土更有活力的东方殖民地。许多港人对英国统治的时代并不感到耻辱,反倒充满眷恋。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民主和自治方面更加进步,不是英国人不想那样做,而是受制于中国的束缚,正如学者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论:“要是换了是在其他地理位置上的话,香港恐怕老早已经自治了,就跟英国别的殖民地差不多,到最后就活脱会是另一个新加坡。”香港没有成为新加坡,罪过不在英国,而在中国。
中国确实成为香港今天一切不幸的根源。当年,清帝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没有徵求居住在香港的华人的意见;而中国以新殖民者的姿态收回香港,同样没有徵求现今的香港人的意见。只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港人对回归的善意想像灰飞烟灭,《学苑》年度总编辑梁继平不无愤怒地数点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种种灾难:“中共及港府一直具策略地去瓦解香港人的身份,包括高举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史观、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在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中文、收编各大传媒及压制本土影视业、推动边境融合与中港同城化、大量输入新移民、放宽大量自由行来港、推动消除基于居民身份的差别待遇之法桉等。”不仅香港人认同的基本价值遭到腐蚀,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搅扰,难怪香港人民怨声载道。
那么,香港人如何与这种宛如灭顶之灾的命运抗争?梁继平认为:“透过建构香港民族论述,我们将重新发掘、诠释并凝练香港的文化内涵、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守卫香港人身份的独特性,免遭受中共同质化。”他也向香港知识界提出恳切的呼吁:“香港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须重新审视、挑选并演绎香港的本土历史与文化内涵,建构出一套具主体意识的民族论述,继而将其成为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香港民族论》就是这样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公民民族主义和宪政民族主义的兴起
香港人能否形成一个民族呢?如果用传统的种族和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概念,香港人很难形成一个独立民族,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广东人,热衷于祖先崇拜的香港人常常去广东寻根。但是,如果用“公民的民族主义”或者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宪政民族主义”的概念论述,则“香港民族”完全可以成立。台湾学者吴叡人指出:“所谓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运、共同政治社会体制、共同心理特徵与共同价值等标凖来界定的,与血缘、种族无关。本质上是开放的,与北京的血缘民族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北京当局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骗局破产后,祭出了爱因斯坦所説的“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即与纳粹近似的“血缘民族论”,中共领导人常常将血浓于水、炎黄子孙等词语挂在嘴边。但是,纳粹当年以现代人类学所确认的雅利安人的概念爲标牓,中共今天却只能用不伦不类的、自相矛盾的“中华民族”的说法来笼络人心。
公民民族主义和宪政民族主义是香港民族论的理论基础。以文明程度而论,香港人有资格宣称自己跟中国人不属于同一个民族。香港人需要反对的,不单单是共产党政权,更是共产党政权的“民意基础”。一般人不敢说出这一真相和真理:反共与反中不可截然分开。共产党不单单是一个“外来邪教”,共产党还将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共产党也不是一群普通的绑匪,若仅仅依靠武力和暴力,共产党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统治中国。当年,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确实得到大部分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衷心支持。而经过共产党漫长而残暴的统治,作为人质的民众早已跟绑匪“精神同构”。对此,苏赓哲指出:“历史事实是,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没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权;没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在六四万人唾骂下发展成目前的贪腐大国。没有这样的人民,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权。”所以,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文化圈中思想被污染的人,都需要一个“刮骨疗伤”的过程。
中国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而香港已经迈入半个公民社会。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网路社交媒体上,连公民社会都成爲“敏感词”。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奴隶变成公民。学者资中筠指出:“中国最需要的是培养理性的、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顺民。实际上,愚民、顺民并不能保证社会安定,没有明确的公民意识,没有法治观念,在某种情况下,顺民很容易变成暴民。建立公民社会是当务之急。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会获罪。如果把最讲理、有良知、有正义感、主张温和渐变、培养公民社会的人都打压下去,一旦有事,顺民无告,变成暴民,那才会无序大乱,是十分危险的。”其实,共产党仇视公民社会的原因很简单:对于共产党来说,暴民造成的动乱是遥远的危险,而共产党担忧的看得见的危险——觉醒的公民的维权运动。
由于共产党的愚民统治,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跟朝廷一样卑贱暴戾。既然官场肆无忌惮地腐败,民间也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线。香港对中国开放自由行,带给香港的收穫,除了少许旅游收入,更多的是秩序的沦丧,以及公民与愚民、暴民的文化冲突。苏赓哲评论説:“土改可以谋财害命,奶粉製造者、食品生产者、玩具製造者为了谋财,当然就不顾人命。他们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不是时代有别,也不一定为了斗争,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在文明程度上他们已经烂掉了,烂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个民族了。”那么,香港人为什麽不能选择不跟这个野蛮的族群做“同一个梦”呢?
如果将公民民族主义和宪政民族主义诉诸于政治实践,就是作为普世价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住民自决”原则。如《学苑》副总编辑王俊杰所説:“自决,归根究底是为了捍卫人生而拥有的价值与尊严。”如果不能“住民自决”,或者如北京宣称的那样,香港七百万人的命运,必须要由中国的十三亿人来决定;那么,无非是在十三亿奴隶中再增加七百万奴隶而已。香港人当中当然也有“奴在心者”,如梁振英、叶刘淑仪、民建联、爱港力;但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愿做奴隶,而要奋力争取公民身份,他们出现在维园烛光晚会中,出现在七一大游行中,出现在鱼蛋革命的巷战中。
香港文化的精粹不是华夏文化,而是英美文化
如果説香港民族的概念可以成立,那么与之配套的就是香港文化——没有独特的文化体系,民族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符号。
那么,如何定义香港文化呢?香港不是某些“北京中心主义者”心目中所蔑视的“文化沙漠”,产生于香港的金庸的武侠小说、粤语歌曲以及港味电影等,一度风靡中国、台湾、东南亚以及整个华语文化圈。本书中收入曹晓诺的《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一文,论证了香港文化的独特性及在沉寂中的出路:香港的文化人不应当忘我地追逐中国的市场、投合中国官方的喜好、进而被中国的文化黑洞所吞噬;反之,应当建构本土文化的岗位、表现香港的独有城市特色。
再进一步发掘,香港文化的根基是什么?香港评论人、有“国师”之称的陈云在其着名的《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须传承华夏正统,在文化上比中国大陆优越。但是,李啓迪质疑这种“以华夏文化反征服中国”的思路是否可行,而且香港文化不能单单以华夏文化的精髓来概括。学富五车的陈云,在常识问题的判断力,甚至不如李啓迪这样一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精准。
在我看来,陈云的“香港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正统”的观点,与海外新儒家以及中国国内的传统文化论者同样荒谬。论证华夏文化的优越性,跟论证中国人人种的优越性一样,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自欺欺人。所谓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并没有让中国人过上自由、民主、有尊严的生活,并没有在中国建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全民普选的政治制度,以及保护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那么,这种文化究竟有多大的保存价值呢?即便保存下来,它早已脱离了其诞生的土壤,又如何存活下去呢?
香港人比中国人提前进入文明状态,不是得益于华夏文化的熏陶——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衡量,最“文明”的不应当是香港,而是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或者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中原大省河南。然而,这两个省份偏偏离文明最远,发生的法西斯暴行也最多:在日光之下,山东的地方政府将东师古村打造成一座囚禁盲人陈光诚的监狱,河南的地方政府则迫使调查艾滋病村真相的高耀洁医生踏上流亡路。作为政府帮凶的,还有无数吃人血馒头的当地底层民众,他们心安理得地帮助政府打工,身兼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而不自知。
必须承认,香港文化中最可珍贵的部分,都来自于英国,用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的话来说,英语文化的范畴“是盎格鲁圈,而不是盎格鲁人”,是用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和信仰来划线,而不以人的肤色和血统来区隔。香港理所当然地属于“盎格鲁圈”,也就是丘吉尔所説的“英语民族”,儘管会讲英文的香港人只是少部分浮在社会上层的精英阶级,但英语文化及价值在香港早已“处处留香”——就连香港的警匪片中,也会出现法官依照普通法判桉的细节。
何谓英语文明?丘吉尔在其巨着《英语民族史》中,如此论述建立在英语之上的文明的特质:“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订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持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丹尼尔•汉南进一步阐释説,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的市场、出版自由、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审制等等,“无论如何也不能説是一个先进社会生而就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借助英语语言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连同这种语言,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源头实际独一无二”。
香港何其幸运——当年割走香港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等“非英语国家”。英国留给香港的制度遗产,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内被中国侵蚀乃至摧毁;但是,英国留给香港的文化遗产,可以让香港的年轻一代跟中共展开一场持久的、坚韧的、必胜的“价值观之战”。
香港不是古旧的城邦,而是新的生命与价值共同体
陈云的《香港城邦论》是以欧洲城邦的历史折射香港未来的走向,如古典时代的雅典、或如近代的日内瓦、但泽等“自由市”。然而,以上这些城邦都是失败的个桉,它们都没有在邻近帝国的压力及内部的矛盾之下长存下来。或许,陈云的城邦之説,只是一种叙事策略,以此掩饰其内心的独立慾望。然而,虽然费尽心思过度包装,陈云仍被“左胶”和“大中华胶”们冠以“港独教父”的帽子,实在是枉费心机。
跟已经有社会地位、瞻前顾后的知识分子们相比,反倒是香港大学《学苑》杂志的这群年轻人,毫无畏惧地喊出港独的口号。十年前,我最后一次去香港访问时,曾经询问过几位被视为香港民主派中最激进的位朋友,港独的想法在香港究竟有多大的支持度?他们都摆手摇头説,主张港独的人在香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殊不知,才短短十年时间,昔日被视为天方夜谭的港独就蔚为大观。若年轻一代继续成长和突围,港独未尝不可能成爲未来十年香港的主流意识。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佈了一份关于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令人惊讶的是,在十八至二十九岁的受访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三的人认为自已是中国人。而在北京举行奥运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顶峰,逾百分之五十一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种中国认同迅速降低、香港认同迅速上升的强烈对比,已然成为一种中共无法掌控、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即便未来中共政权崩溃、中国艰难地向民主的方向转型,这种趋势或许会减缓,但绝对不可能逆转。
清帝国崩溃之后,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竭力继承清帝国的衣鉢,以维持原有的广袤疆域爲荣耀。结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了夹在古老帝国和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四不像”。具有香港背景、任教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孔诰烽指出,近年来的国际局势演变显示,单一制多民族国家已经走入死胡同。在此世界背景之下,“什么是中国人”本身也成了一个让人彷徨的问题。在价值系统紊乱的中国,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説,“国家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又怎么可能让香港人对“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宏大叙事表示效忠呢?
香港本身就能孕育生长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与价值共同体,它将超越古旧的城邦概念而走出一条崭新的希望之路。它将由一次或多次香港的全民公投来确立,它是开放式的而非封闭的。新加坡、科索沃、东帝汶所走过独立建国的道路,香港也可以效彷。香港人的教育水准、民主素养和国际视野,都比以上这些国家的国民更为优秀,“香港国”可以成为东亚的民主、自由、法治、富裕的典范。
过去,香港是一座“逃城”。《学苑》编辑之一的李啓迪认为:“香港的本质是一个逃避战乱中国和共产党统治的难民社会,但经过定居一代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偏安一隅的一块小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和身份认同。”今天的香港人的先辈,大都是躲避历代中国暴政的移民,李啓迪甚至用“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和抗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官兵来类比之:正如“五月花”号带着新教徒来到美洲开天闢地是象徵崇尚自由和反对帝制统治,或英国人打破西班牙无敌舰队和纳尔逊战死特法拉加海战象徵其海上霸权,香港也有自己的“民族神话”。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出现过一轮逃亡潮。但是,如今的香港年轻一代不愿继续逃亡,他们视香港爲家:“香港是我们的主场,凭什麽要我们离开?年轻一代宁愿绝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毙将家园拱手相让。守护香港自治,已无退路。”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