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世界里,一个能够探查存在的荒诞性、人类的盲目性、历史的无理性的小说家,比一个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政治家更为伟大与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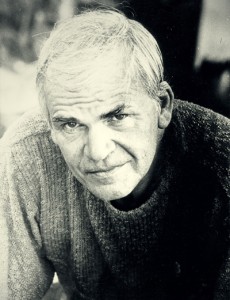 对大多中国读者而言,昆德拉小说在性自由方面的启蒙价值,远远高于政治自由。这是马尔克斯与昆德拉的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所遭遇的共有命运。经历过严酷清教徒性禁忌年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如饥似渴欲死欲仙。而中国艺术家们则在这两位文学导师的指引下,学着如何在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中演练自己的性生活。我有一位作家朋友,谈起昆德拉,很坦诚的说,阅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他才二十来岁。第一遍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但他惊异于男主人公的性生活。一个男人,居然可以既有妻子,又有很多情人,还不以流氓罪被抓捕判刑,真是“共产主义”一般令人羡慕的乌托邦生活。小说里无需男人负责的独立女画家萨宾娜,亦是令他记忆多年的性自由女神,她那巨大无比表演舞台一般的床,她做爱时喜欢玩弄的祖先的黑色礼帽,皆说明她有将性舞台化、戏剧化、享乐化的倾向。萨宾娜对他的影响,比托马斯更为长久。只是自从读过这本小说,他做爱即若到达高潮也不敢闭上眼睛,因为萨宾娜蔑视闭着眼睛做爱的男人。从这个近乎笑话的阅读后遗症中,可以看出昆德拉小说中的性启蒙,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
对大多中国读者而言,昆德拉小说在性自由方面的启蒙价值,远远高于政治自由。这是马尔克斯与昆德拉的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所遭遇的共有命运。经历过严酷清教徒性禁忌年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如饥似渴欲死欲仙。而中国艺术家们则在这两位文学导师的指引下,学着如何在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中演练自己的性生活。我有一位作家朋友,谈起昆德拉,很坦诚的说,阅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他才二十来岁。第一遍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但他惊异于男主人公的性生活。一个男人,居然可以既有妻子,又有很多情人,还不以流氓罪被抓捕判刑,真是“共产主义”一般令人羡慕的乌托邦生活。小说里无需男人负责的独立女画家萨宾娜,亦是令他记忆多年的性自由女神,她那巨大无比表演舞台一般的床,她做爱时喜欢玩弄的祖先的黑色礼帽,皆说明她有将性舞台化、戏剧化、享乐化的倾向。萨宾娜对他的影响,比托马斯更为长久。只是自从读过这本小说,他做爱即若到达高潮也不敢闭上眼睛,因为萨宾娜蔑视闭着眼睛做爱的男人。从这个近乎笑话的阅读后遗症中,可以看出昆德拉小说中的性启蒙,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
中国读者首先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读出性自由,然后才认识到政治自由。身体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所在。极权体制之所以对民众的身体进行大规模的道德规训,亦是因意识到,性自由往往是争夺政治自由的柔性先声。众所周知,整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以捷克的“布拉克之春”作为历史背景。男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位唐璜式的外科医生。他徘徊在“轻”(萨宾娜)与“重”(特蕾莎)之间,对政治生活并不热衷。比起政治生活,他更喜以阳具为手术刀,勘探、找寻隐藏在每一个女人身体中的细微差别与珍宝。托马斯是这样一位唐璜:他既不是美色痴迷患者,也不是女性身体的掠夺者,他只是对女性身体过分好奇的游客。每一个陌生女性的身体,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寻宝式观景。
就这样一位热衷艳遇、旁观历史的知识分子,亦被深深的裹挟进历史事件的漩涡。他不想与政治共渡蜜月,但政治却对他情有独钟–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闲暇言论,成为他忤逆斯大林政权的罪证。他被医院开除,成为给居民们清洗窗户的清洁工,最后与妻子特蕾莎双双流落至一个乡村,过着所谓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托马斯的命运,是“布拉格之春”后颇多捷克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人被巨大的权力机器所挟持,无有任何政治自由可言。
但仅仅因托马斯的遭遇,将昆德拉看作是一位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必然是一种严重的认知错觉。本质上,昆德拉是一位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皆保持着狐狸般警戒的作家。与其说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控诉了极权社会的罪恶,莫如说昆德拉更在乎探讨人类存在的本质。在昆德拉看来,流行于人类社会的种种潮流与主义,无非是一场又一场的荒诞闹剧。自由主义在昆德拉的眼里,亦非完美之物,而是一种社会学“刻奇”。昆德拉对自由主义的反讽与嘲弄,可以在萨宾娜与弗兰茨在法国、美国的生活小细节中凸显而出,并在弗兰茨临死之前的“伟大的进军”中达到颠覆性高潮。我们大多数人,都一直生活在“刻奇”的生活语境里。人类不是在媚雅,便是在媚俗,闲着没事的时候,更会以心理杂耍的方式进行自媚。
至1987年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来,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一直遭到严重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仅来源于读者,更来源于作家与批评界。因韩少功误将“Kitsch”译为“媚俗”,小资们作家忙不迭地将昆德拉的只言片语引用进他们的作品四处炫耀,却不懂他们正是昆德拉的话语之刺所要挑破的脓疮。一些批评家因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读出昆德拉对前苏联的辛辣嘲讽,便认为昆德拉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却不知昆德拉反对一切主义与潮流。倒是国外批评界对昆德拉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英国左翼批评家约翰·伯格,因憎恶昆德拉高蹈于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虚无价值观,在随笔《一坨屎》里如此挖苦昆德拉:“在这屎的世界里,他以为自己是一枝欧芹呢。”是什么使得心智相等的人彼此排斥而后憎恨?伯格是欧洲老左派(信奉共产主义),昆德拉却唯恐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囚禁了他。伯格积极的介入社会运动,昆德拉却远离一切社会运动成为一个旁观者。伯格将自身融入普罗大众,昆德拉却恐惧“刻奇”对大众躲之不及。伯格执念于人类的幸福,昆德拉执着于艺术之美。伯格认为历史是理性的,有其可循的进化规则,昆德拉认为历史是荒诞的,人类一直在迷雾中穿行。这是永远无法相遇的两类人:前者认为政治斗争高于任何艺术之美,后者认为艺术之美高于任何政治斗争。彼此截然相异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两颗美丽心灵只能互相嘲讽,而无任何交流与汇集。
在乌克兰局势日益紧张的2014年,昆德拉出版了新著《庆祝无意义》。这本小说,虽然比起昆德拉在鼎盛时期的小说作品,较为平庸,但在八十岁的高龄,昆德拉仍旧是睿智清醒的:小说中的加里宁格勒,很可能是乌克兰的未来。小说在四个男性主人公会面时,不时的穿插着前苏联笑话–斯大林与24只鹧鸪,斯大林与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在二战前,原本叫柯尼斯堡,是哲学家康德一生从未离开过的城市。康德生于斯,死于斯。二战之后,柯尼斯堡成为前苏联的领土,被斯大林命名为加里宁格勒。在政治风云变化莫测的20世纪,东中欧的很多城市名因为权力的更迭频频改变,唯独加里宁格勒却像斯大林极权政治的权力之徽,永恒的凝固在此,不曾换回它原本拥有的名称。直至如今,它仍旧是俄罗斯的领土,仍旧被称为加里宁格勒。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笑话,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历史笑话,它更像斯大林特意针对哲学家康德所展开的嘲讽–权力对哲学、权力对理念、权力对世界的无情嘲讽。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昆德拉虚构斯大林与加里宁跑至巴黎的卢森堡公园放肆的鸣枪与撒尿,主人公拉蒙亦与他假称罹患癌症的朋友相遇,用艳遇安慰降临在朋友身上的死亡阴影。但极权制度真的罹患癌症了吗?人们真的该庆祝现在拥有的一切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庆祝无意义”。在此,昆德拉的虚无主义立场显影无遗:庆祝毫无意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毫无意义。斯大林或斯大林式的人物,还会卷土重来。无知而懵懂的人们,就如笑话里的那24只鹧鸪,呆呆地站立枝头,等待着被斯大林式的人物再度用猎枪捕获。
仅小说的艺术而言,我不赞同伯格。艺术不是政治课本,并不需要承载过多的意识形态。艺术的世界里,一个能够探查存在的荒诞性、人类的盲目性、历史的无理性的小说家,比一个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政治家更为伟大与重要。在这个屎一样的世界里,让昆德拉这类时代的逆行者与清醒者,更多一些吧,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欧芹,独立不羁,迎风招摇。
来源:凤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