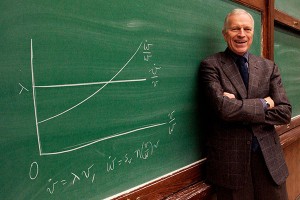【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编者按】
李克强总理近日在上海视察自贸区时强调,政府要给市场让出空间,激发市场活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这也让“大众创业”这个新词进入了大众视野。澎湃新闻发现,“大众创业”这个概念并非看起来那么“草根”,背后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可以溯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那里。菲尔普斯在最新一本中文版著作《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剖析了大众创新等议题,展现了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强调“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西方国家的议题:几个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取得骄人成就,但在20世纪却未能保持辉煌,西方由此变得虚弱和迷茫,不确定能否重现昔日的荣光。这固然是西方的历史,但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
19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某些国家的民众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工资的大幅提高、市场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满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远离了上述美好的场景?从目前来看,似乎所有国家都在与之告别。《大繁荣》的目的就是探究这一罕见的繁荣是如何获得,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试图在《大繁荣》中展现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由于错误的理解或其他目标的干扰,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或削弱,而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并且不能被其他价值观冲淡。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那些不理解繁荣来自何方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严重打击它们的创新活力。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今天的美国取得的创新率和工作满意度已远不能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社会成员有权利使其繁荣前景(约翰•罗尔斯称其为“自我实现”)免遭践踏。在20世纪,各国政府试图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以重现繁荣。如今的任务更为艰巨:让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回繁荣。为此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监管行动与刺激供给或需求无关,要采取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理解经济活力所依赖的机制和精神。这当然是各国政府有能力做到的,有的国家从两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为促进创新铺平道路。以上就是我在酝酿《大繁荣》时涌现的想法,我相信唯一的问题在于人们还远未认识到而已。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另一类问题:对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生活的阻力。支持经济繁荣的价值观与妨碍和贬低繁荣的价值观相互对立。过去的繁荣为此付出了高昂的通行费。我考虑的问题是: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随之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目前,美国出现了一些实现传统目标的呼吁,如加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为国家利益启动公共工程,这些对欧洲国家来说再熟悉不过。有的价值观曾引导许多欧洲国家通过“社团主义的视角”用传统的中世纪的观点看待国家的作用。今天也有人呼吁要更加重视社区和家庭的价值。相反,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生活及其带来的繁荣是多么可贵。美国人和欧洲人已不再熟悉大众的繁荣的感觉。在一个世纪前有过辉煌社会的国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国,或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都已经丢失了广泛的繁荣的鲜活记忆。一个国家的创新过程,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创作、疯狂的发展和创新未能成功时的无奈终结,在今天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痛苦,只有那些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社会为了增加国民收入和国家实力才愿意承受,西方国家的当代人已不再接受。人们不再把创新过程理解为生活的兴盛发达,即变革、挑战以及对原创、发现和不落俗套的毕生追求。
《大繁荣》是我对这些现象的回应: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
首先我将回顾西方国家的繁荣历程:经济繁荣出现在哪里,如何实现,又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所遗失。我们对于现状的理解,有很多来自对过往碎片的拼接。此外,我还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跨国分析。
历史叙述的核心是19世纪爆发的经济繁荣,它点燃了人们的想象力,改造了工作与生活。英国和美国首先出现这样广泛的兴盛景象,人们的工作投入和挑战性大大增强,然后是德国和法国。女性的逐步解放以及美国最终废除奴隶制,进一步扩大了兴盛的群体范围。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发明是这种兴盛活动的一部分,并成为同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进入20世纪后,兴盛的范围逐渐缩小,增长相应减速。
在这一历史叙述中,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所发展出来的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获益。此观点不同于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理论,他们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们竞相实现。而我认为现代经济体不同于老式的商业经济体,它是阳光下的新事物。
对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这种创造性和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现代思想家隐约地观察到,包括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
《大繁荣》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带来的兴盛生活的人生体验。创新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良好运转的现代经济的一种基本品,包括给人精神激励、提出待解决的问题、促进新观察的产生等。我试图描述在现代经济中工作和生活所获得的丰富体验,在思考这一广阔图景时,我兴奋地意识到此前还从未有人描述过对现代经济的感受。
在描述经济活力的现象时,我认识到无数人的经济自由是一项核心要素,我们要感谢西方国家的制度对这种自由的保护。此外还有各种支持制度,它们是应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然而,保持经济的现代性所需的支持不仅仅是对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执行,也不仅仅是各种商业和金融制度。我描述的经济活力并不否认科技进步,但并不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在我的叙述中,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如否定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被其他势力束缚或阻止),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这里所描述的西方国家历史是由一个核心矛盾推动的。这一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例如,欧洲的私人所有权占比在几十年前就提高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或保守价值观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代,再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漫长文化演变史中,产生了各种新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激发了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崛起,在18世纪培育了现代民主制度,19世纪又催生了现代经济,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一文化演变也把现代社会带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的现代化催生了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中新兴的现代经济带来了社会动荡,对传统势力构成了威胁。把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重视保护后进而非鼓励先进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些国家非常强大,因此总体来说,现代经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在现代经济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进展时,往往会被政府机制强行取代(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或者被管制措施束缚(例如在“二战”之后)。
许多学者曾暗示,他们从普遍接受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时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我自己也必须越过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形成的丛林,才能深入探讨现代经济及其创造性和价值观。熊彼特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新熊彼特主义则认为鼓励科研可以促进创新,这两种观点都预先假定现代社会可以离开现代经济体而运转(也难怪熊彼特会认为社会主义时代即将到来)。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们的幸福只来自消费和休闲,因此所有的职业活动都是为此目的服务,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体验。凯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义认为,失败和波动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缺陷,因为导致波动的挑战和冒险对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其后出现并在今天的商学院占主导地位的新–新古典学派则认为,商业活动只是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与人们的抱负、未知、探索和远见无关。还有极端乐天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构成问题,因为社会演化会产生最需要的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文化。假如《大繁荣》的推导更接近真相的话,那么过去产生的所有这些观念就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大繁荣》用了很大篇幅,以崇敬的心态描述现代经济给参与者提供的体验,因为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惊奇之处。这种赞美引发的问题是,现代经济所支持的现代生活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有何优劣之处。在第十一章我将指出,现代经济的精华产物(人们生活的兴盛繁荣)与关于美好生活的古代定义合拍,而对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人们有太多不同的版本。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获得心智的成长(这来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道德的成长(这来自创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领域)。现代经济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美好生活的概念,这是证明优秀的现代经济的合理性的重要一步——它可以支持人们的美好生活。
当然,为现代经济的合理性辩护就必须驳斥批评意见。即使现代经济能够为所有成员提供美好生活的前景,但如果在过程中引起了不公正,或者以不公平的手段实现目的,也不能被认为是具有正义性质的经济。在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出现错误或造成炒作(如20世纪前10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时,弱势群体乃至所有社会成员都将遭受打击,从失去工作的员工到公司倒闭的企业主,到财富大幅缩水的家庭。政府也可能没有妥善处理现代经济的利益分配(这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未能选择对弱势群体最有利的方式。当然这可能源于政府自身的问题,而非现代经济的缺陷。 《大繁荣》的最后一章将简要勾画现代经济的概念,它能够尽可能地为天赋和背景较为弱势的群体提供美好生活。我将指出,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体完全可以根据常见的经济正义的概念进行治理,如关注最弱势群体。如果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生活,那他们将愿意承担伴随这种生活的波动风险。我还将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要优于一个基于传统价值观的、有效运转的传统经济。但如果某些社会成员还是坚持传统价值观,结果又如何呢?在这个入门性质的探索中,我们必须找一个止步的节点,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希望拥有传统价值观,希望有自己的经济生活的人,应该有创建其个人生活的自由。而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也有在现代经济中自由工作的权利,而不能被限制在传统经济中,被剥夺参与变革、挑战、原创和发现的机会。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国家应该支持甚至努力建设现代经济,但这种经济的未来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容易遭受重大失败、波动和伤害,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有漂浮甚至恐惧的感觉,但获得新发现的满足、迎接挑战的兴奋、走自己道路的自豪以及在过程中成长的愉悦(简而言之,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必须付出这些代价。
(注:更多菲尔普斯的观点,可以参阅他的专著《大繁荣》,本文是《大繁荣》的“前言”,澎湃新闻(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希望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借鉴。)

作者: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原作名: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译者: 余江
出版年: 2013-9
页数: 392
来源:澎湃新闻